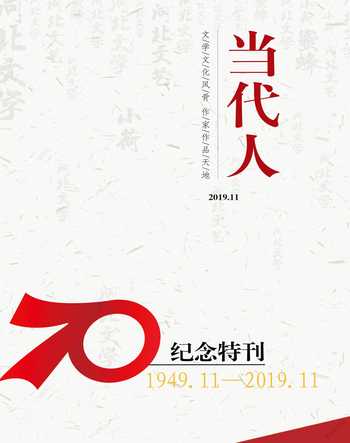八月懷胎,十月分娩
大約是七月的中下旬(一九四九年七月,編者注),冀南文委從駐地威縣郭莊搬家啟程,告別了親如一家的房東,乘汽車北上。南宮“打尖”后,從衡水換乘火車“專列”,繞德州,過天津,次日中午于豐臺站午餐少憩,晚霞滿天的時候,到達了省城保定。
當時聽說省委有規定,兩區合并,對口接待。當時冀中文協住在古蓮池內,冀南文委自然就和他們住在一處了。在兩個單位合并過程中,行政事務較忙,業務部門的同志休整了十來天,領導宣布合并后的機關名稱叫“河北省文聯籌委會”,簡稱文聯(籌),領導成員共四人:胡蘇、趙起揚、申伸、趙卜一。胡蘇任主任,趙起揚、申伸任副主任。各業務部門立即運轉,開始工作了。
會后,趙起揚同志找我談話,說我的工作有個小的變動,要調離創作崗位,去做編輯工作,問我有什么意見。我說:“咱冀南文委創作室的七八個同志,都分到文聯(籌)創作部,怎么單把我一個人調別處,連個伴兒也沒有。”他說:“進城后局面不同了,新建部門的工作也需要有人做,編刊物需要作風細致的同志去擔當,領導上覺得你最合適。”我說:“剛才會上宣布文聯(籌)所屬各業務部門,怎么沒聽到還有個編輯部呀?”他說:“沒有單設編輯部,暫時先建個編輯室,附設在指導部里面。”我又問:“這個編輯室里都有誰呀?”他說:“當下只有兩個人,另一個是冀中文協的王思奇。據胡蘇同志在會上介紹,這個同志人很老實,不愛說話,性格內向,多才多藝,我想你們一定會合得來的,你可以先找他去聊聊。”
突然接受了一個新的工作,感到陌生,心里沒底,為了爭取早些熟悉情況,立馬我就找那個王思奇去了。
聽說他在蓮池東沿的一個小跨院里住,走近才見,院內有幾棵枝葉茂密的古槐,綠蔭遮掩下有一排顯得低矮的北房,看來是個游人足跡不到的幽靜去處。
一踏上小院的臺階,就隱隱約約聽到了三弦琴聲,果然如人們傳說:找王思奇不用問路,循著琴聲就能到他的屋門前。
他住的是這排北房的最里邊的一間,我對著門口招呼了一聲:“思奇同志在屋嗎?”屋里琴聲停了下來,有人答應:“誰呀?請進。”我撩開竹簾進屋,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似乎猜到我是誰,而且完全明白我的來意:“你是葉蓬,對吧?”我說:“你怎么知道的?”他笑著說:“且別說在咱住的蓮池里面,就是在大街上,人們也知道你是剛從冀南來的文藝兵。”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臨近搬家之前,文委和所屬文工團、畫報社的同志們,一人發了一身橄欖綠的制服,上身細長細長,掃地風褲腿一尺多寬,外加一頂八角帽,兵不兵、民不民的,任何單位任何部門都沒見過這種樣式的裝束,他一看能不明白嘛。
我抱著急于了解編輯室情況的目的而來,當然就先發問了:“是說讓咱們一塊編刊物嗎?”他說:“我也是昨天剛聽說。”我又問:“就咱兩個人?”他說:“咱編輯室很快還要來個負責人,他叫遠千里,是《河北日報》社的副刊科長。”我說:“我可沒干過編刊物的工作呀。”他說:“我干過,沒啥。干什么活兒也沒有三天離把。”他的話雖不多,但語氣十分肯定。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況,就這樣簡單又隨便。
果然過了一兩天,遠千里就到任了。他召集我們兩個開了個編輯室第一次全體會。看來他是早成竹在胸,文聯領導對擬議中的機關刊物的要求和設想,辦刊宗旨和編輯方針,他都說得清楚明白。
由于當時的文聯(籌)工作面很寬,對文學、戲劇、美術、音樂、曲藝等各門類全都包括,只有一個機關刊物自然應當辦成綜合性的文藝月刊了。
領導上要求創刊號盡可能在十月份出版,最遲也必須在第一次省文代會之前和讀者見面。時間相當緊迫,只有八、九、十這三個月,滿打滿算,也不過九十來天。八月開始征稿,九月動手編輯,十月三校付印。當時的編輯力量僅有三個人,分工也要一人分擔幾項工作;遠千里這個編輯室主任,除了負責全部稿件的終審之外,還要兼做文藝理論、文藝批評等類稿件的初審和編輯。王思奇除負責劇本、小說、曲藝各欄的主要稿件的編輯之外,還要兼管封面設計和內文版式的編排等編務工作。我負責詩歌、歌曲和通訊報道類稿件的編輯,并負責對外聯系和印刷發行等事宜。
九月二十號將創刊號的全部稿件編審完畢,王思奇開始排版,我覺得這工作新鮮得很,自始至終在旁邊看著。王思奇說:“頭一期,我干,你看;下一期,你干,我看,行不?”我說:“行,只要你在旁邊看著,下期我就敢干。”
第一期刊物的排版,就在他住的那洞府式的房間里,從掌燈開始,直到排完最后一頁,天都快亮了。他從床下一柳條包里提溜出一瓶黑色粗瓷壇裝的茅臺酒,一邊開著瓶塞一邊說:“打開右邊抽屜,那里有個紙包拿出來。”等我打開紙包一看,原來是包花生米。我說:“你屋里有酒有菜,這是早有準備呀!”他笑著說:“不是準備,是常備。”我說:“真沒想到你還是一位斗酒百篇的詩仙啊!”他說:“詩仙可不是,我是‘斗酒不成篇,三弦胡亂彈’,一會兒喝到半醉,穩坐啞言,聽我給你——彈上一曲。”他竟然哼起了西河大鼓的起板腔調來。
這是我生平頭一回喝茅臺酒。那時候的茅臺酒,在大街上商店和酒館里,到處有賣,其價格之低廉,比起今日的二鍋頭來,也貴不了多少。
十月二十五日,創刊號的三校清樣看完,只待簽字付印了。我找思奇商量:“既然咱們刊物的出版日期可以定為十月末,也可以定為十一月初,我傾向于前一種抉擇,讓我們的刊物和我們人民共和國在同一個十月里誕生,那多帶勁!”
思奇也同意這個意見。
遠千里沒有表態,他說:“這是個不大也不小的問題,咱們還是請示一下為妙。”
結果,依照胡蘇同志的意見,創刊號確定為十一月一日出版。
遠千里向我們兩個傳達,說胡蘇在文聯(籌)辦公會上是這樣講的:“關于《河北文藝》創刊號的出版日期問題,我們必須從編輯室只有三個同志的現實出發,他們出色地完成了領導交給的任務,為了按期發稿,他們通宵不眠。如果,將出版日期提前一天,定為十月三十一日,創刊號即為十月份刊物,到年底他們還須再編兩期刊物,吃得消嗎?不如錯后一天,使之成為十一月份刊物,年前再編一期就可以了。我們在座的同志,如果不懂得愛惜群眾的積極性,那就不配擔當一個領導成員。”
因此,盡管《河北文藝》創刊號十月二十八日就印出來了,印在版權頁上的出版日期卻是“1949年11月1日”。
就這樣,我們這個八月懷胎、十月底分娩的寧馨兒,著實招人喜愛,捧在手上翻閱,如同插在水晶瓶里的一束照眼的鮮花,勝似放在金鑲玉盤子里的豐盛碩果。
由于《河北文藝》創刊號的問世,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文聯(籌)領導對自己的機關刊物和編輯工作也就更加重視,文聯(籌)辦公會決定將三人編制的小編輯室從指導部下分出來,升格為編輯部,遠千里也隨之升為編輯部部長。辦公會同時決定調集人才充實編輯力量。冀南新華書店的資深編輯莊進輝同志調來擔任編輯部的副部長。小說作家柳溪從中學語文教師的崗位上調來了,省軍區政治部文化部的李克明調來了,谷峪、呂原、厲聲、王玉西、鐘玲從文聯(籌)本身的創作部調到編輯部來了。戲劇編輯千群、張琪從秦皇島、唐山調來了。編輯部由一個科級小單位一躍而成為文聯(籌)各個部門中的最充實最活躍的單位。此后,一九五〇年冬至五一年春,編輯部還從全省全國范圍的青年業余作者中公開招考擇優錄取了近三十名編輯練習生,從他們中間發現并培養了大批人才。劉紹棠、蓋祝國、韋野、李慶番、劉俊鵬、丁江、樊丁一、苑紀久、張響濤、吳電、馮鋒、田歌、趙棟、王玉文等后來都成為了有成就的作家、編輯和畫家,編輯部達到了它的全盛時期。如果不是趕上壓縮編制,還會有更多的文藝人才涌現。再以后的情況,在這篇重點記述創刊情況的短文中,就不便細說。謹以我為祝賀五十周年刊慶而寫的七絕三首,附于文末,懇請《當代人》的廣大作者、讀者不吝賜教!
十月分娩
半世紀前締造初,荷紅蓮白滿清湖。
仨牛皮匠三雙手,出版如期豈認輸。
辛勤釀蜜
曾憶刊名稱“蜜蜂”,嗡嗡悅耳賽歌聲。
勤勞遍采百花蕊,調理生活甜味濃。
風雅正聲
燕南趙北盡生根,當代誰人不識君?
知命之年方少壯,高山流水有知音。
(原文刊發于2000年4期。有刪節。)
[葉蓬,《當代人》創刊時期(時名《河北文藝》)編輯。]
編輯:安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