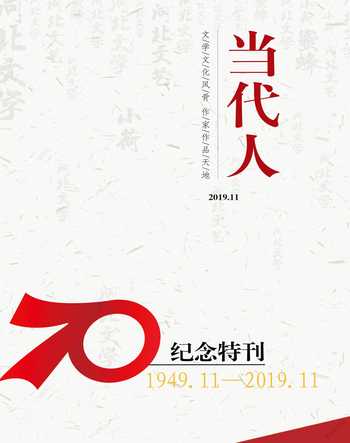“失敗青年”的“情義危機”及其他
有限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張敦的小說是那種即使隱去了作者署名,也可以一眼認出來的作品。強烈的個人化敘述風格,使得他筆下的“失敗青年”形象各個刻有“張敦印制”的防偽標識。就這一點而言,張敦倒是與河北另一位勢頭正盛的青年作家張楚有著幾分相似之處。或者說,他們小說的共同點恰恰在于兩者的差異性。同樣是書寫“失敗者”,兩人的小說總能給讀者帶來別樣的閱讀體驗和審美享受。
要想清晰地闡明這兩位作家筆下的“失敗者”形象,顯然需要一篇更長的評論文章。為了節約筆墨,筆者試著以形象化的語言來加以提煉概括(需要說明的是,下面的文字并無臧否之意,旨在以張楚小說為參照,通過對比來凸顯張敦小說的獨特之處):從風格特征上看,張楚的小說猶如琥珀,硬度低,質地輕,手感柔潤,有寶石般的光澤與晶瑩度;張敦的小說則更像化石,堅硬,沉重,粗糲,具有極強的線條感與紋理度。張楚筆下的人物好像封存琥珀中的昆蟲,纖細入微,毫發畢現,栩栩如生;而張敦筆下的人物則仿佛化石中的遺骸,骨骼鮮明,結構整飭,傳神見性。從敘事調性上看,張楚的小說憂郁傷感又自由疏放,一如爵士和藍調,強調旋律線的轉音和變奏;而張敦的小說則憤怒狂野且赤裸直接,仿佛搖滾和朋克,一群老炮兒的煙熏嗓在重金屬的碰撞與轟鳴中聲嘶力竭地嘶吼與吶喊。從審美感受上看,張楚的小說很像傳統武術,講究一張一弛,剛柔兼濟,威嚴又不失優雅;張敦的小說則更像現代搏擊,追求短平快,干脆利落,靈活多變,拳拳到肉,一擊致命,從不拖泥帶水。在敘事視點上,張楚擅長用第三人稱來講述“他人”的故事,因而小說帶有強烈的戲劇舞臺感;而張敦更喜歡用第一人稱“我”來展開敘述,于是作品帶有鮮明的“自敘傳”特質。一言蔽之,張楚的小說重“情感”,細膩、敏感、微妙、復雜;張敦的小說重“情緒”,頹唐、沮喪、消沉、暴躁。如果要將兩人的小說改編電影的話,張楚筆下的人物,非葛優、蔣雯麗這樣的影帝影后級別的演員不能駕馭;而張敦筆下的人物,最好是讓早期王寶強這樣的非職業演員本色出演,方能保證作品的原汁原味。
以上皆為近年來張敦小說的閱讀印象,下面不妨以其短篇近作《讓父親飛起來》為切入點,走進他的小說內部一探究竟。該小說采用“歸來——逃離”這一經典文學敘事結構,大抵講述了一個底層青年試圖遵循世俗成功學邏輯去實現“衣錦還鄉”的白日夢幻想,并最終宣告失敗的故事。作者張敦從友情、愛情、親情三個維度上全方位地呈現出當代“失敗青年”的“情義危機”,進而將這群鄉村棄兒兼都市零余者精神世界中無歸屬、無希冀、被侮辱、被損害的“失敗實感”和盤托出。
首先,“友情決裂”是故事矛盾沖突的導火索。“我”是一名出身卑微的寒門子弟,孤身一人在城市奮力打拼。一天,發小劉志強來城務工,親眼目睹“我”的窘境后,非但沒有絲毫同情與安慰,返鄉后還以此作為談資添油加醋地講給他爹聽,他爹又不懷好意地告知“我”爹,一直將“我”視作唯一能與志強爹平起平坐資本的老爹自然是萬分沮喪,來電抱怨“我”讓他在村里失了臉面。得知事情始末后,“我”果斷與志強絕交,并在內心深處燃起了強烈的“復仇”火焰。沒過多久,“我”爹再次來電,聲稱志強馬上要結婚了,而“我”卻連個對象都沒有,并再三叮囑“我”不要回來參加婚禮,省得給他丟人。毫無疑問,爹的嫌棄徹底傷害了“我”的自尊,于是一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打擊報復計劃就此展開。于此同時,類似果戈里《欽差大臣》中微服私訪的滑稽橋段亦隨即輪番上演——當“我”開著租來的汽車,攜著有“省公安局領導”女兒身份加持的“假女友”走進自家院落時,不知所措的父親因受寵若驚而洋相百出,向來仗勢欺人的志強爹也瞬間變得畢恭畢敬,就連身居副縣長高位的志強姨夫也主動上前握手寒暄,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向門可羅雀的破舊庭院也變得仿若縣府衙門一樣熱鬧,村民們自動集結起來,爭先恐后地向“我”和女友訴苦鳴冤……荒誕不經、啼笑皆非的情節背后不僅暗含著當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秘密,而且密集地呈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隱疾和暗語,比如城鄉差距、象征資本、拜金主義、權力至上、階層固化、“青天崇拜”等等。
其次,“愛情買賣”是情節發展演進的助推器。王麗是報社一名剛入職的新人,與“我”相比,她的悲慘遭際有過之而無不及。兩顆孤獨的靈魂在陌生、陰冷的都市角落中抱團取暖、相互慰藉,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在一個價值趨于單一化,世俗成功學甚囂塵上的叢林社會,愛情的保質期終究是短暫。由于缺錢,兩人之間的“普通愛情”正在悄無聲息地迅速變質、腐敗。當“我”正在為如何開展“復仇計劃”而苦惱時,王麗也正在為下個月的房租發愁。于是,一場互利共贏的等價交易在心照不宣中就此達成。最終,當“身體”作為最后一件商品明碼標價地進行銷售時,原先的“愛情”已徹底淪為了各取所需的“買賣”。此時,任何貌似公允的道德譴責都是蒼白無力的,正如個體不能把個體的失敗完全歸咎于社會一樣,社會同樣不能把失敗完全歸咎于個體。
最后,“親情危機”是小說的敘事核心以及悲劇性結局的直接誘因。張敦采用黑色幽默的表現手法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既可愛、可憐,又可恨、可悲的“父親”形象。這個“父親”為了“我”,可謂是做出了最大的犧牲,盡到了一個父親最大的義務。然而,親情的付出并不像種莊稼,必然能夠換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豐收;子女也并非父母用來向人展示和炫耀的象征資本。父親賭博一般地將寶壓在“我”能光耀門楣之上,既是對自己一事無成的現實人生的自覺逃避,也是對“我”身體與精神能量的無情消耗與剝削。從這個意義上看,小說題目《讓父親飛起來》就頗值得玩味。筆者認為,“飛”字一語雙關:其一,“飛”字可做“飄”講,意指“我”試圖通過一場“衣錦還鄉”的騙局,來滿足父親渴求已久的虛榮心;其二,“飛”字直取原意,一場意外事故,導致父親被撞飛起來。這里顯然暗藏著“我”潛意識中濃重的“弒父情結”。或者說,對于“本我”而言,讓父親“飛”(飄)起來只是手段,其終極目的在于“讓父親摔下來”,從而實現對父親白日夢幻想的毀滅性打擊。這里的“父親”已經不僅僅指代一個具體的個人,同時隱喻著既定的層級關系、權利結構,乃至基因和血統。如果將題目視作一個語句,那么它很顯然是缺少一個主語的。從文本意義上講,直接肇事者是王麗,而車禍根源在“我”。由此可見,這個無名的主語,指向的是那些像“我”和王麗一樣沉默的“失敗青年”群體,他們所對抗的不是具體可感的某個人、某件事,而是泰山壓頂卻又難以捉摸的“無物之陣”,是森嚴的等級秩序、單向度的價值取向、幾近固化的社會結構,以及如同原罪般與生俱來、如影隨形的劣質“基因”與卑賤“血統”。在這樣實力懸殊的戰斗中,個體的人幾乎只有兩種結局:或是飛蛾撲火,或是魚死網破。于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我”返鄉后會由衷地發出這樣的感慨:“我并非鐵石心腸,對于故鄉的一草一木,可以說一往情深,無比熱愛。我只是厭惡生活在這片熱土上的人。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親。”
近年來,張敦小說中的“失敗青年”形象,一次次讓我想起身邊的同齡人,包括我自己。他們是痛苦的、掙扎的,是頹廢的、虛無的,但更是無時無刻不在焦慮地思考現實、反顧自身的。我們不斷地書寫他們,不斷地在生活中與他們碰面,為的不過是有效地理清自己,在喧囂的現實中尋找可以安放渺小自我的角落。在這個意義上講,任何一種寫作都是值得的。但需要警惕的是,當某種寫作趨向成為一種潮流和時尚,它便極有可能成為一種易于滑入的、不假思索的寫作慣性。文學評論家孟繁華在《寫出人類情感深處的善與愛——關于文學“情義危機”的再思考》一文中尖銳批評:“我們的當代文學曾長久經歷過‘暴力美學’熏染,對‘敵人’充滿了仇恨和誅殺之心;曾受過‘弒父’‘弒母’等現代派文學的深刻影響,青年‘解放’的呼聲響遏行云,‘代溝’兩岸勢不兩立;商業主義欲望無邊,將利益的合理性夸大到沒有邊界的地步等,這些觀念曾如狂風掠過,至今也沒有煙消云散。在文學表達中,其基因逐漸突變為一個時期普遍的無情無義。”張敦的寫作尤其需要對這種敘事慣性和美學意識形態保持足夠的警惕與自省。
(趙振杰,主要從事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學評論文章散見于《文藝報》《文學報》《小說月報》《文藝評論》《青年文學》《中國作家研究》《新文學評論》等,著有文學評論集《螢火微光:文學的散點與聚焦》。曾獲《人民文學》2015年上半年“近作短評”金獎及佳作獎;《人民文學》2015年下半年“近作短評”銀獎;第十三屆河北省文藝振興獎。)
編輯:安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