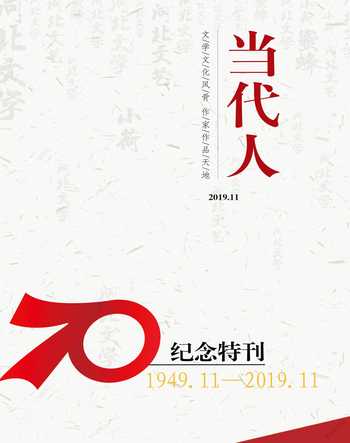去梅潔的家鄉
清晨,從酒店出發,沿解放南路一直向南,行程20分鐘,便來到了漢江邊。漢江是長江最大的支流,李白曾經寫下“橫潰豁中國,崔嵬飛迅湍”的詩句,來形容漢江的波濤洶涌、奔流不息。一千多年后,眼前的漢江比李白描述的要安靜,水波不興。它遼闊、壯觀,極目遠眺,水天相接,陽光平鋪在寬闊的水面,光彩奪目,輝耀成溫柔而抒情的光韻,連綿不斷。
漢江橋頭,面朝大江,一巨形磐石穩如泰山般,端居于此。巨石左半側刻著四個大字:魅力鄖陽。右半側則密密麻麻刻滿了文字,走至近前,細細打量,才識得是作家梅潔的《山蒼蒼,水茫茫》片段,最后一句是“無論天涯海角,只要我一個人獨自望天望云望夜空中的星月,我就望見了我的故鄉——鄖陽”。
是的,這是南水北調的水源地,這是作家梅潔的故鄉。
鄖陽為十堰市的一個區,居秦嶺東部余脈,南望巍巍武當,擁攬滔滔漢江。漢江綿延三千里,在鄖陽成茫茫蒼蒼之勢。在漢江的滋養下,鄖陽山清水秀。于我而言,對于鄖陽的了解,全部來自梅潔有關南水北調工程的系列報告文學及她零星的講述。記得2010年我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學習時,院方曾經請梅潔到高研班給作家們講過一課。至今我仍然記得,她講到自己十幾歲離開家鄉時,與父親話別的情景。家鄉從此離她遠去,但在她的內心,卻從未離開過。家鄉一直是她寫作的一個源泉。梅潔是我的同事,是我尊敬的作家。算起來,她應該是我的前輩作家,再加上她后來長期在北京居住,我們交往并不多,對彼此最多的牽掛大多來自于對方的文字。我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她文字的關注,在同樣對文字充滿著敬畏的我眼里,她是個純粹的寫作者。她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她熱愛的文字之中,尤其近二十多年來,她一直在用她充滿激情與智慧、充滿對故鄉眷戀與熱愛的文字,書寫著故鄉人民為南水北調工程所做出的巨大的犧牲與奉獻,書寫著在我們時代進程中那些默默無聞而又偉大的平凡者。
因為梅潔的緣故,鄖陽,一個陌生的名字,開始在我的腦海中慢慢地熟悉起來。我所在的城市,干燥少雨,每年都從南水北調工程中獲益良多,我曾經在閱讀中,無數次想象過這個漢江,想象過她筆下的故鄉鄖陽。可是身處其中,才真切地感受到,文學對于大地江河的滋養,文學對于一個地域的影響。所到之處,凡是接觸到的人似乎都知道梅潔,都認識梅潔,都對梅潔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她書中的每一個場景,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感人的故事,似乎都深刻地鐫刻在他們的腦海中,那份由現實到書中的榮光與自豪,那份因為犧牲與奉獻而生出的萬千感慨,已經不再只是文字,而成為他們心中跳躍著的疼痛與撫慰,快樂與憂傷,成為他們生命旅程中的一部分。
一直陪同我們的是鄖陽區宣傳部的副部長蘭昌林,他精力充沛,思維活躍,不停地向我講述著梅潔的文章給鄖陽人帶來的精神的撫慰與力量,不停地向我講述著有關鄖陽的歷史,更多的是鄖陽的現在。講到如何發現“鄖陽心”的過程更是滔滔不絕。他說,他繞城徒步行走,驚奇地發現,他走過的路程巧合地正好形成一個大大的心的形狀。在他略有些激動和驕傲的描述中,他親身體驗過的鄖陽是一個內外合一的城市,既擁有一個完美的心的形態,又兼具愛的內心。不管是鄖陽的現在、將來,還有更加厚重的過去,愛心似乎都一直隨著漢江之水,在每個人的內心中涌流。
作家梅潔的城市,因為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因為背靠大江的優勢,似乎注定要經歷痛徹心扉的抉擇與告別。風和日麗,與梅潔一起登上城邊的牛頭山,她無比感傷地用手指著橫跨江面的漢江橋說,我家就在第三個橋礅下面。順著她手指的方向,除了寬闊的水面,早已看不到任何城市的痕跡。隨著時光的遠去,隨著作家無法忘卻的記憶,鄖陽古城早已沉沒到江底。鄖陽城有著輝煌的歷史,府城建于明成化年間,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地理位置顯耀,被稱作“鄂之屏障、豫之門戶、陜之咽喉、蜀之外局”。從流傳下來的舊照片看,鄖陽城生活氣息、商業氣息濃厚,商埠林立,行人如織的石板路,鐘鼓樓、戲樓、商業街,一派繁華景象。在塞外生活工作的梅潔,記憶中的家園仍然是古樸而富有生活情趣的街道、石板路,而31年之后,1991年,她重新回到故鄉時,故鄉已經隨著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修建,沉入江底。記憶隨江水沒入了時間的河流之中。也就是那次回家鄉,作家梅潔才真正地意識到要為家鄉做點什么,要為家鄉的人民做點什么。家鄉人民的犧牲精神常常感動著她。于是她懷著為家鄉人民樹碑立傳的決心,把自己生活的根,創作的根深深地扎在了那里,扎在了她曾經無數次魂牽夢縈的故土。于是我們看到了南水北調移民三部曲,看到了大部頭的《山蒼蒼,水茫茫》《大江北去》《漢水大移民》。
柳坡鎮臥龍崗移民新村的廣場上,映入眼簾的是一組大型雕塑,雕像的序言仍然是引用梅潔《大江北去》的一段話:“我真切地希望,當清澈的漢水給干渴的中原、華北和京津大地帶來一片滋潤時,當人們欣喜地端起從遙遠的鄂西北流來的一杯幽藍時,不要忘記為此而兩度奉獻了家園和土地的庫區人民,不要忘記他們幾代人在半個世紀里經受的磨難和犧牲。”烈日當空,群雕被安置在臺階上,自下而上,依次精心雕刻出移民大搬遷中的一些感人的場景,每一個場景背后都是一段催人淚下的故事。它們被記在梅潔的文字中,也鐫刻在鄖陽人民的心里。最下方是銅質的書籍,梅潔激情四溢的文字便刻在上面。我們碰到了雕像的作者,兩位民間雕刻大師,羅宏和賈蘭玉夫婦。據兩位作者介紹,梅潔的移民三部曲給了他們心靈的震撼,而正是這種來源于文學的力量煥發了他們內心對于再現那段歷史的靈感與沖動。他們樸實無華,滔滔不絕地講述著對于雕像的理解,仿佛他們并不是來自于遙遠的東北的藝術家,而就生活在這里,親身體驗過離別的痛苦與對美好未來的憧憬。
梅潔好像第一次來到雕像面前一樣,對雕像充滿著新鮮感,非常認真地在雕像邊照相。雖然已經是她諳熟于心的情景,雖然他們早已化成她內心涌動的情感,在綿延的文字中流淌,她仍然久久地盯著他們,盯著背負著“彭家崗渡口”的移民,盯著那條有著傳奇色彩的狗。
鄖陽,有那么感傷的故事,卻也有那么多的希冀與期盼。我們從雕像,從文字,從他們的講述中,一同感受著鄖陽的傷痛與犧牲,更憧憬著令人鼓舞的未來。在鄖陽短短幾天,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作家的力量,一部書的影響。一個作家,只有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才能讓靈感長成參天大樹。一個作家,也只有用真誠去面對世間所有的一切,才能找尋到她心中的故鄉。
鄖陽充滿著愛與希冀。蘭昌林部長期望的那個愛的心,一直在他們的腳下,一遍遍地走出來。陽光下,漢水之畔,遠處是正在興建的香菇小鎮搬遷工程,建成后能容納三千七百多戶精準扶貧易地搬遷對象。站在香菇大棚里,我們對架子上圓鼓鼓的菌棒產生了興趣,梅潔不停地詢問著老鄉,她家是哪里的,她一個人能承包多少個大棚,收入多少。老鄉是個三十多歲的婦女,家在偏僻的貧困山區,丈夫在外打工,自己一個人承包著兩個大棚,年收入可觀,滿臉洋溢著滿足和幸福的笑容。一排排香菇大棚整整齊齊,非常壯觀。大棚外擺放著一些成熟的香菇,不僅香味純正,而且體態優美,那是我見到的最漂亮的香菇,體型飽滿、圓潤,花紋優美自然,簡直就是渾然天成的精美的藝術品。小小的香菇,寄托著貧困家庭的生活夢想,那些奔放自如的紋路,猶如鄖陽人對未來的期盼與向往,香菇致富,在鄖陽已經不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正在實現的現實。聽到家鄉的人民已經在脫貧的道路上走在了前面,梅潔很是興奮,她手捧著菌棒,留影拍照。
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故鄉。不管路途有多遠,不管有多少千山萬水阻隔,故鄉始終都在心里,溫暖著記憶,照亮著前行的路。
(劉建東,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河北省文聯副主席,河北省作協副主席,文壇“河北四俠”之一。在《人民文學》《收獲》等發表小說多篇。著有長篇小說《全家福》《女人嗅》《一座塔》,小說集《情感的刀鋒》《午夜狂奔》《我們的愛》《射擊》《羞恥之鄉》《黑眼睛》《丹麥奶糖》等。曾獲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孫犁文學獎、河北省文藝振興獎等。作品多次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小說排行榜。)
編輯:劉亞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