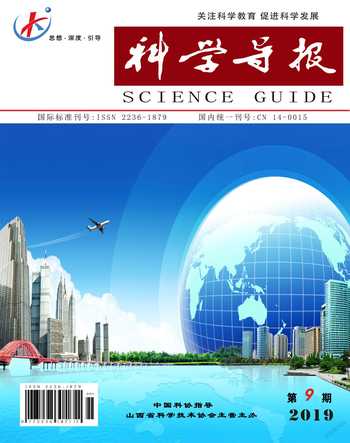論80年代以來軍旅小說中英雄形象塑造的新趨向
趙彥琴
摘 要:軍旅小說是一種以戰爭活動和軍人生活為特征指向的文學形態,英雄形象的塑造是軍旅文學發展史重要的價值追求。20世紀80年代以來,軍旅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相對比較輝煌和繁盛的時期,英雄形象的塑造隨著時代的變遷,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本文分別從英雄性格的人性化、英雄心理的復雜化和英雄命運的悲劇化這三個方面細致地分析了80年代以來英雄形象塑造的新趨向,旨在探尋時代變遷和英雄主義寫作之間的內在聯系。
關鍵詞:英雄形象;人性化;復雜化;悲劇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革”后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南線戰爭”爆發和人們審美取向和精神需求的轉變,軍旅小說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難得的“黃金時代”。它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十七年時期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又在主題和創作方法上進行了突破和創新,特別是對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呈現出了新的寫作趨向。
一、英雄性格的人性化
新時期以來,隨著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等逐漸發展,軍旅作家對十七年時期“高大全”的完美英雄形象進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英雄是人”的創作基調,開始關注英雄性格的人性化,促使英雄走下了神壇,實現了從神性英雄到人性英雄的回歸。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不過是蒼蠅。有沒有缺點并不能成為區別英雄與懦夫的標準,恰恰相反,有缺點,才有差別,才有矛盾,才能使讀者在這種差別與矛盾中看到真實的人性,看到崇高的靈魂。
徐懷中的《西線軼事》以其獨特的英雄塑造和戰爭描寫開了80年代軍旅小說創作的先河,它“單槍匹馬地突破了軍事文學中‘英雄主義寫作’的重重禁區,為后來的軍事文學創作狂飆突起式的集團沖鋒樹起了一面鮮明的旗幟。”[1]劉毛妹是小說中作者塑造的一個“英雄”,他與以往“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相比具有嚴重的缺陷,但恰恰是他與眾不同的性格缺陷和不完美的形象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外表冷酷,作風不嚴謹,軍容不整,嘴里時常叼著煙,組織紀律性差,理想信念似乎也不太堅定。但是隨著故事情節的逐漸推進,我們發現在他身上有著軍人勇敢頑強的優良品質和英雄氣質,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也有著深刻的憂患意識,劉毛妹始終堅守他心中的理想信念,最終壯烈犧牲。作者塑造的劉毛妹這一英雄形象融合了普通人的優點和缺點,更加真實。1982年李存葆發表了《高山下的花環》,塑造了梁三喜、靳開來、趙蒙生等英雄形象,作者按照生活的真實面目刻畫人物,既寫出了他們富于責任感、使命感的英雄本色,也寫出了他們作為普通人的喜怒哀樂。
二、英雄心理的復雜化
縱觀80年代以來軍旅小說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大多都是立體式的人物,那種扁平化類型化的英雄人物已退出了歷史的舞臺。軍旅作家們更加關注英雄人物的復雜心理,挖掘潛藏在內心深處錯綜復雜的情感,使小說具有更豐富的藝術魅力。
《射天狼》是朱蘇進創作的一部中篇小說,他用充滿激情的筆調,刻畫了新一代軍人的光榮與夢想、無奈與痛苦,極富有藝術個性。作品從和平年代里的英雄形象入手,探索英雄復雜矛盾的心理歷程,揭示了人的主觀愿望與客觀環境的嚴重沖突。小說中的英雄典型是袁翰,朱蘇進曾說“從袁翰這個中國當代軍人的典型,我們高興地看到了和平時期的新的開拓和走向成熟。這,或許是我們軍事文學發展的一個新的信息。[2]”主人公袁翰是一名普通的軍人,作為連長,他對戰士要求嚴厲,同時又對他們關懷備至。在家庭中,他扮演著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角色,一方面要承擔普通人的責任,另一方面又要履行軍人的職責,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矛盾。當接到女兒病危的消息時,他本應該回歸家庭,盡一個丈夫和父親的義務,但是,作為一名軍人,他又不能擅自行動。作者形象細膩地刻畫了袁翰痛苦矛盾的心理,展現了當代軍人在事業上、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復雜糾葛,表達了軍人崇高的思想品質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此外,例如《亮劍》中的李云龍和趙剛,《歷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我是太陽》中的關山林,《激情燃燒的歲月》里的石光榮等都具有復雜的心理矛盾,呈現出了一幅在戰爭與和平的環境下所折射的人類豐富多彩的精神畫面。
三、英雄命運的悲劇化
十七年時期的軍旅小說深受政治因素的直接干預和戰爭文化心理的深刻影響,因此,軍旅小說展現出“革命勝利大團圓”的創作模式,小說中塑造的英雄也是戰無不勝的完美形象。例如《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和少劍波不會在戰爭進程中死亡,《苦菜花》中的也必然會目睹整個戰爭的經過,并看到兒女們不斷成長。但是進入80年代以來,由于政治和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戰爭的災難和生活的悲愴激發了人們對英雄這一形象的深層思考,于是,悲劇意識逐漸被引入了小說創作中。縱觀80年代的軍旅小說中的英雄人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人物的悲劇命運都具有崇高性,呈現出“英雄——悲劇——崇高”的創作結構。例如《西線軼事》中的劉毛妹帶著傷痕走上戰場,最終犧牲在被攻取的高地之上,嚴整的軍容和勝利的姿態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高山下的花環》中的靳開來喜歡發牢騷,講怪話,是個“刺頭”,但是在戰斗中他沖鋒在前,吃苦在前,最后為了給戰友們砍甘蔗解渴踏響地雷壯烈犧牲,雖然上級部門不承認他是烈士,不給他發軍功章,但在戰士們心中,他卻是真正的英雄。還有為救戰友不幸中彈的梁三喜……
在和平時期英雄的悲劇命運雖然不如戰爭時代表現得強烈,但絲毫沒有減弱“英雄”這一人物群像命運的崇高性,反而是一種深化。在國家民族命運和個人的利益發生矛盾沖突時,英雄們能高屋建瓴的為大局考慮,這種悲劇命運反映出的無私精神和高貴品格更激發了人們對和平時期英雄的崇敬之情。
英雄主義是軍旅小說永恒的主題,對于英雄人物的塑造既體現了軍旅作家們個人的價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80年代以來的軍旅小說逐漸消解了英雄的神性,還原本真,對英雄狂熱的崇拜轉為客觀冷靜的評價,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現實意義和鮮明的時代特色,為后來軍旅小說英雄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較為合理貼切的參考。
參考文獻:
[1] 唐韻:《英雄主義寫作,或幾個關鍵詞》,《解放軍文藝》2000年11月。
[2] 金輝,韓寶章.當代軍人的愛與恨——朱蘇進論.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1985年,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