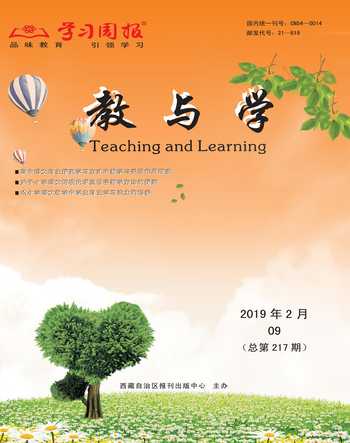論司馬遷與班固商品經濟思想異同的原因
艾新宇
摘 要:司馬遷和班固生活在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的漢王朝,都因是兩漢時期著名的史官為后世尊崇,但二人所反映經濟思想尤其是商品經濟思想上卻有很大的分歧。這又是為何?本文力圖從二人所處時期的商業發展狀況、社會思潮、家學傳統和個人經歷等角度來揭示他們商品經濟思想的異同產生的原因,這對系統地研究司馬遷和班固的經濟思想有很大的幫助。
關鍵詞:司馬遷;班固;商品經濟思想;異同原因
司馬遷與班固商品經濟思想的異同主要反映在《史記·貨殖列傳》《漢書·食貨志》中,司馬遷非常重視經濟的運行。他認為經濟不應該被國家直接管控,工商業的活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認為最好是讓適度自由發展。班固承認商業對農業乃至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這是他和司馬遷的相同點。但班固反對國家放任經濟自由運行,而且歧視和反對經營致富,鄙視工商業的經營者,主張國家實施直接的管理。究竟為何?可以從以下角度來分析:
一、商業發展情況的異同
西漢王朝建立之初,吸取了秦王朝苛政于民、迅速滅亡的教訓,在經濟管理上奉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思想,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實踐證明這一決策在西漢建國初期取得顯著成果,國家經濟迅速從秦末戰亂中恢復并且商業還取得很大的發展成果。
生活在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對建國以來發展起來的商業有著清醒的頭腦,他已經準確認識到多年來對商業的放任自由使得商業過度膨脹,商人勢力對政權的威脅在上升,“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商人恃財驕縱,勾結地方、王國官吏的事情屢屢發生,七國之亂中商人對反叛勢力的幫助是他們叛亂的經濟來源,而漢武帝時期調整對商業的“無為”政策,任用興利大臣桑弘羊等人對重要的鹽、鐵等重要的商業部門實施官營,其對商業的抑制和商人勢力的嚴厲打擊又對當時的商品經濟造成人為的障礙。
商業發展和商人勢力壯大的利弊時刻在提醒著司馬遷謹慎、辯證地看待商品經濟和商人勢力的同時,也潛意識地有助于他對商業、商人有更為公平、公正的看法。
東漢初,經濟同樣凋敝,同樣急需恢復受戰亂破壞的經濟,然而兩漢之際土地兼并愈發嚴重,自耕農大量破產淪為佃農,豪強莊園勢力日益強大,尤其是富商勢力膨脹連國家政權都難以撼動,為控制其進一步壯大,光武帝繼承武帝時期實施的一系列控制和干預經濟的政策,使商品經濟的發展遭到沉重的打擊,堵塞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之路。下詔在全國實施鹽鐵專賣,后兩任皇帝明帝和章帝亦進一步加強抑制商業和商人的力度。
生活在東漢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時期的班固對此有直觀的感受,出于這一實際和他自身的一系列因素,致使他對商業和商人存在明顯的歧視。
二、社會思潮的異同
西漢初年決策者通過道家經濟思想實現了經濟的恢復,但司馬遷生活的年代又是一個法家、農家為漢武帝理財的時代。他們的理論依據基于一部盛行于西漢初期的經濟學著作《管子》,此書核心是“利以生義”,認為衣食足才能知榮辱。與道家經濟思想“無為”不符,與同時期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貴義賤利”等也不符,然而卻為漢武帝時期的開疆拓土提供了最堅實的基礎,成為這一時期西漢經濟發展的最大助力。這種經濟思潮的反差卻指導著西漢經濟不斷向前發展的實際讓司馬遷對他的經濟思想的間接闡述有了一個很廣、較準確的參考。
而班固所處的時期是儒學正統地位日益穩固的時代。統治者當時以儒學為正宗,搞了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講五經異同,尊崇儒學,原本的各家有益于經濟發展的思想已被儒家“貴義賤利”的大趨勢所取代,封建正統思想已占據了他的有限的思考空間。所以他更加注重從當時的社會經濟尤其是農業、商業出現的問題來片面地闡述他的經濟思想。無疑,盡管迎合了政府需要和適應當時局部的經濟實際,但也喪失了辯證、公正地看待商業和商人勢力乃至經濟規律的眼光。
三、個人家學傳統與經歷的異同
司馬遷,字子長,漢左馮翊夏陽人(今陜西韓城縣),班固扶風安陵人(今陜西咸陽),二人的家學傳統與個人經歷對他們的經濟思想影響很大。
他出身史學世家,家境優越,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使其有很高的文化知識與素養。在這點上班固和他是一樣的。
但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崇尚黃老,譏刺漢儒,這對他的熏陶很大。早年他從董仲舒、孔安國那里汲取的儒學養分和二人是都曾向皇帝屢屢上書議事的實踐經歷,養成了司馬遷對國家安危的深刻關懷的愛國情操以及敢于直接觸指社會核心、敏感問題的行為。這是班固感受不深切的。
早年他還游歷天下,奉命至巴蜀、昆明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視察,并多次隨漢武帝巡幸全國名山大川,這些經歷使他對全國大致的經濟有更感性的認識,而班固在成書之前并沒有這么一段經歷使他的著書遜色了不少。
而他中年遭“李陵之禍”后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更是發生了巨大改變,這反而激起司馬遷更強大的自信心客觀公正的記述歷史、記述經濟,尤其是對當時重農抑商大背景下商業經濟和商人的關注。這更是班固所無法感同身受的,也是他的《貨殖列傳》與班固的《食貨志》對商品經濟闡述不同的一大原因。
班固是史學世家的同時也是儒學世家,在父親班彪和伯父班嗣的熏陶下,16歲便進入了當時儒學最高學府——太學潛心苦讀儒家經典,以便進入仕途,在撰寫《漢書》的過程中曾被人告發“私修國史”乃死罪,后經班超的幫助和他所寫的內容符合正統觀念才得以免于一死,這對他的教訓是很深刻的。時代大背景和自身個人經歷都使得班固很難再著書過程中難免有失偏頗。
結語:
通過對司馬遷和班固商品經濟思想產生原因不同角度的闡述與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商業發展情況的異同、社會思潮、個人的家學傳統與經歷以及滲透其中而又不可忽視的國家力量的因素,使得二人在完成對后世影響極大的史學巨著《史記》和《漢書》而被后世人交口稱贊的創作過程中,出現了文章開頭所寫截然不同的對商品經濟的態度。
參考文獻:
[1](西漢)司馬遷.史記[M].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62.
[2](東漢)班固.漢書[M].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2.
[3](東漢)班固.漢書[M].貨殖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2.
[4]張大可.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述論[J].學術月刊,1983,(10).
[5]朱枝富.司馬遷的經濟思想[J].陜西師大學報,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