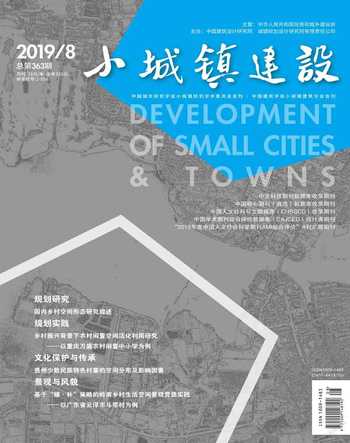基于“縫·補”策略的嶺南鄉村生活空間景觀營造實踐
盧素英 趙則海
摘要:“縫·補”策略是針對鄉村生活空間環境現狀,通過整合現有廢棄地、閑置空間、廢舊資源等發揮其“鄉土、經濟、集約”的特點,實現“本土營造,一村一品”的鄉村風貌。文章以廣東省云浮市云城區斗帶村生活空間的景觀改造實踐為例,系統梳理了斗帶村的環境特征、生活空間現狀及存在的問題,調查分析村莊閑置資源現狀,以及村民生產生活、文化習俗等鄉土特征,提出適用于該村“本土特色景觀”的“縫·補”策略,從空間整合、廢舊資源再利用兩個方面著手,對村落中原本割裂、無序、雜亂的閑置節點進行重構。改造后的斗帶村生活空間景觀考慮了村民記憶中的生活烙印,再現了原汁原味的獨特村莊景觀,保留了濃郁的嶺南鄉村特色。
關鍵詞:景觀重構;“縫·補”策略;生活空間;嶺南鄉村;斗帶村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8.014 中圖分類號:TU982.29
文章編號:1009-1483(2019)08-0094-08 文獻標識碼:A
Practice of Living Spac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Lingnan Rural Areas Based on"Stitching and Supplementing" Strategy: Taking Doudai Village in Yunf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U Suying, ZHAO Zeha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living space and environment, the strategy of "stitching and mending" is to integrate the existing wasteland, idle space and waste resources to give full play its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conomic and intensive" and achieve the rural style of "local construction, one village and one product".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practice of village life space landscape renovation on Doudai Village in Yuncheng District of Yunfu,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condition of living spa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en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idle resources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villagers’ production and living and cultural practices, proposes the "stitching and mending" strategy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of the villag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space integration and reusing discarded resources, the discrete, unordered and messy landscape nodes are refactored. After transforming, the living space landscape of Doudai Village takes into account the brand of life in the villager’s memory, at the same time it reproduces the original unique village landscape and retains the strong r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ingnan.
[Keywords]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stitching and mending" strategy; living space; Lingnan Rural Area; Doudai Village
引言
鄉村生活空間不同于鄉村農業勞作等生產空間和村落外圍生態空間,是村民居住、消費和休閑娛樂的場所,主要由村民住宅建筑集聚圍合而成的場所構成[1-2]。鄉村生活空間的形成與發展往往隨著生產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生存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快速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嚴重影響了傳統鄉村原本的肌理,昔日依山帶水的居住格局逐漸惡化,鄉村生態環境也受到一定的破壞。隨著國家“美麗鄉村”建設思想的提出,除了村民生產、生活等方面的問題外,鄉風文明、村容村貌等問題也開始得到廣泛關注[3]。我國2017年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推動了全國鄉村人居環境景觀建設的快速發展,鄉村生活空間也隨之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本文以廣東省云浮市云城區斗帶村生活空間改造實踐為例,系統梳理了斗帶村的環境特征、生活空間現狀及存在的問題,調查分析村莊閑置資源現狀,以及村民生產生活、文化習俗等鄉土特征,提出結合“縫·補”策略進行空間景觀重構,營造獨特的“斗帶景觀”。
1鄉村景觀營造中“縫·補”思想背景
所謂“縫”,《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作為動詞時“用針線將原來不在一起或開了口兒的東西連上”,《說文解字》中解釋為“縫,以針紩衣也”,《廣雅》中“縫,合也”;所謂“補”,《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添上材料,修理破損的東西;補充、補足、填補等”,《說文解字》“補,完衣也”。
筆者根據縫與補的基本含義將其引申至當前鄉村生活空間環境景觀設計之中。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于2017年8月出臺的《廣東省 2277 個省定貧困村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示范村規劃編制指引》第三章“規劃內容”其中一條是“村容村貌整治”:明確村莊開展“三清理”(清理亂堆亂放、存量垃圾、溝渠池塘等)、“三拆除”(拆除危舊房屋、亂搭亂建、違規廣告招牌等)、“三整治”(整治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水體污染等)。但是在執行“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的過程中,有些相對完好的材料如磚、瓦及石材等被作為“垃圾”而清理,一些閑置的舊建筑、殘墻被認定為“危舊”而拆除,出現嚴重的浪費現象(見圖1、圖2)。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縫·補”的思想策略——針對生活空間雜亂閑置空間、閑置“廢料”、空置舊建筑等資源的處理思路。對雜亂閑置空間進行整合,即為“縫”;對空置舊建筑或“殘墻斷壁”等結合實際情況用閑置“廢料”將其修補,營造具有一定的功能或觀賞價值的構筑物或小品,即為“補”。通過“縫·補”策略達到景觀重構的目的,營造具有濃郁鄉土生活氣息的本土景觀,實現真正的“本土營造,一村一品”的鄉村風貌。
2斗帶村傳統生活空間環境特征和存在的問題

斗帶自然村位于廣東省云浮市云城區安塘街道安塘村,地處安塘街道東南部約5公里,距云浮市區約21公里(見圖3)。斗帶自然村是其所屬的安塘村委會下轄的安塘、斗帶、石頭地、云龍、愛武、石仁背6條自然村之一,自然資源豐富,景觀特色鮮明,低山丘陵、水網密布、叢林深深,共同構成了安塘村獨特的生態環境。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附近缺少特色經濟產業,沒有工業廠房用地,交通不便等原因造成該村經濟發展較為落后,2017年被列入省定貧困村。由于斗帶自然村對創建新農村示范村的配合程度和熱情相對較高,支持村莊景觀改造意愿強烈,生產條件和自然條件優越,因此安塘街道政府選定斗帶自然村(下文簡稱斗帶村)為示范村建設試點。斗帶村當前有43戶,165人,村域面積0.5平方公里,群山環繞,自然環境優美。項目建設之初,設計方對村落傳統生活空間構建、傳統生活空間的消失、當前村民新生活空間的轉移及現狀問題等進行了深入的調研。
2.1斗帶村傳統生活空間環境特征
斗帶村始建于明朝萬歷九年(1581年),由張氏始祖從廣東珠璣巷遷居到此地而形成,屬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式廣府村落。村落坐落在群山環抱的一塊高地上,建筑坐北朝南,依山拾級而上,形成梯狀之勢[4],風水塘呈弧形環繞于村落東、西、南三個方向;平面上是典型的梳式布局。空間交往方面,根據現狀調研及村民口述,村民傳統交往空間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村民結合村落小氣候條件在長期生活實踐中自發形成的,主要環繞于村落外圍,也是人與自然的“自然選擇”結果,具有“因地、因時”制宜的特點,如以風水塘為中心的交往空間、村后小樹林、村口古榕樹下和巷道空間等,為村民交往提供了舒適的小氣候環境;另一種交往空間是根據村民的宗族活動或生活行為等形成的必要性場所,具有“因人制宜”的特點[5],如村民傳統取水、洗衣用途的井臺空間、宗祠前開敞空間、書室空間等。
這兩種空間的形成,一方面是結合村落小氣候條件在長期生活中自發形成的,具有“因地、因時”性,如沿村落外圍的風水塘、林地休閑空間等;另一方面是滿足宗族活動和學習需求的交往空間,如宗祠與書室前的開敞空間(見圖4、圖5)。
2.2斗帶村當前生活空間環境存在的問題
盡管斗帶村的地理位置較為偏僻,但同樣受到快速城市化的影響。筆者通過實地調研、深入訪談及問卷調查等方式了解到斗帶村原有的人地關系、社會關系均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變。如村民大多不再以從事農耕為生,村中90%以上青壯年外出務工①。斗帶村生產方式的改變、生活方式變化大等因素使鄉村活力明顯下降,雖然村中留守老人和小孩仍有生活空間需求,但村落原有的休閑空間年久失修,逐漸破敗。從根源上講,斗帶村生活空間環境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2.2.1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影響生活空間

農業生產的現代化與科學化改變了原有的小農生產方式,如現代農業灌溉方式改變了原有村落中風水塘及周邊河流的用途,原有飲水、灌溉用的河流、水塘變成了無人問津的“臭水塘”,同時也因為鄉村生產結構改變帶來的生活垃圾亂排亂放,農藥、化肥等有害物質的不合理使用,導致目前鄉村人居環境出現不同程度的污染[6-7](見圖6);其次,農業養殖方面,由于“小農戶”對接“大市場”的交易成本高,經營集約化程度低,小農養殖模式日漸蕭條。如原來生活空間中必不可少的豬舍,如今因為生產結構的轉變,大部分已經閑置并破敗不堪[8-9](見圖7);另外受傳統生活模式的改變影響,如鄉村自來水的逐漸普及,以及地下水污染等因素,改變了村民以水井使用為主的傳統空間交往模式。張氏祠堂前的飲用水井已廢棄,原有村民打水、洗衣的生活場所,如今因其功能的消失,其空間交往功能也隨之消失。
2.2.2村落盲目擴張導致資源浪費、村貌喪失、風貌趨同現象
首先是村民隨意自建房屋的行為和無序化擴張切斷了原來呈半圓形環繞于村前的風水塘,還擴張至風水塘以外的耕地、排水渠等,破壞了原本連續的、具有自我修復能力的生態網絡[10],現如今風水塘已被切為幾塊,村口處已被填埋。斗帶村村民的自建房在選址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風水塘以南原有自家田地上沒有在政府引導規劃下營建,另一種是拆除舊泥磚房在原有宅基地上營建。其次是村民自建房外觀風格上受各種文化和觀念的激烈碰撞也存在著盲目跟風模仿城市建設或歐陸風的現象。村落新建區域缺乏村莊規劃,鄰里間的建筑錯綜復雜,不僅整體上破壞了建筑風貌,并且已沒有原有的巷道肌理,致使新建筑區生活空間閉塞、擁擠,無法形成供村民公共交往的空間。在村落舊址上重建的民房因片面追求面積擴張而亂拆亂建現象嚴重,破壞了原有的梳式巷道而變得雜亂無章。
2.2.3廢棄建筑、廢棄雜物占據公共空間
斗帶村廢棄建筑、廢棄雜物占據公共空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廢棄的牲畜飼養房屋或廢棄柴棚等廢棄建筑充斥公共空間;其二是建筑、生活或農用設施等廢料擠占公共空間,如村后原有供村民休閑的小樹林,如今已被多種雜物堆滿。
基于以上現象,結合調研問卷中村民最關心的公共設施增設、公共環境及公共休閑空間改善等問題,渴望有運動、休閑設施及活動空間等,嘗試運用“縫·補”策略將斗帶村生活空間中雜亂空間及廢舊資源有效利用,營造獨特的“斗帶景觀”。

3 “縫·補”策略營造:再現村民記憶交往空間
綜合來看,斗帶村生活空間區域發展過程中,因為缺乏引導和統一規劃,使新建區域生活空間沒有形成供村民交往的公共空間,而傳統的交往空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以村民當前最為關注的幾個休閑空間為對象,采用“縫·補”策略將原有生活空間進行整合,充分利用廢舊資源營造村民記憶中的交往空間環境。
3.1“縫”策略:傳統生活空間的再現
生活空間規劃設計秉持村民日常行為及風俗習慣,對主要休閑空間進行整合。斗帶村整體空間布局上風水塘將新舊村分開,舊村區域保存相對完好,而新村區域因為無序建設而沒有公共空間。根據現狀調研及村民口述,村民日常休閑交往空間主要位于村口、村后背山區域、風水塘、祠堂等處(見圖8)。從平面布局上看這些休閑節點剛好分布于當前村中新建環村路周邊,因此結合當前村民居住分布狀況可考慮將村民日常休閑空間整合串聯環繞于舊村落外圍,一方面以環村道為環狀景觀帶,在景觀帶上營造多個景觀節點形成流動式的休閑空間,另一方面圍合的景觀帶環繞于村落再現傳統山水景觀(見圖9)。主要景觀節點有:入口景觀節點、村后休閑節點空間、以風水塘為中心的街心公園區(包括原有小樹林)及環村道路景觀帶。

入口景觀節點、環村道路和村后的休閑節點均是在前期村莊“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基礎上整理的空間。根據村民需求,入口處設置供村民停車用的空間,為將來村落發展、機動車輛增多預留空間。如前所述,斗帶村屬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村落,人口較少,除了節假日村中車輛較多外,日常車輛較少,因此可結合鄉村實際在入口區域平整后面積約800m2的地塊上營造一處集健身、休閑、納涼、停車于一體的公共空間,即在空間周邊放置運動器材,平時沒有車輛時可供村民休閑用,節假日可作為臨時停車場所(見圖10);環村道建設是根據斗帶村發展需求將原有環村道拓寬便于機動車通行而新建的道路,道路兩旁可增加綠化,靠近民宅一側結合排水渠等基礎設施適當鋪設草坪,較寬敞區域適當種植鄉土遮陰喬木,道路右側因新建汕湛高速公路從村東側通過,公路護坡綠化較為簡單,破壞了原有景觀,需要對坡地進行加固擋土墻和建設草坡以鞏固坡地,同時還起到了隔離噪音的作用(見圖11)。沿環村路向村后方向拐角處結合村民需求新建一處供村民日常交往的休閑空間,同時固化因新建環村道而破壞的后山護坡,避免山體滑坡等災害發生(見圖12)。
以中部風水塘為中心的街心公園位于新舊住宅區之間,景觀區營造考慮了村民交流空間需求,設計方面要體現村民茶余飯后休閑聊天集中之地。首先對風水塘進行疏通清理,使其與村落外圍的魚塘、水田等連通變成有序的活水;其次根據現狀調研、評估及村民實際需求,規劃設計充分利用曬谷場、場所內舊建筑、風水塘周邊空地、原有小樹林等要素,通過整治提升,營造更多舒適的、供村民休閑的空間,并將原有老舊建筑改造成供村民日常休閑和村委會日常辦公的文化室(見圖13)。
3.2“補”策略:“斗帶景觀”的體現

設計團隊進駐斗帶村之初,村里正在進行政府要求的“三清理、三整治、三拆除”工作,大部分廢舊建筑材料等被作為“垃圾”清理出村外,不僅直接危及當地自然生態安全,同時也浪費了大量資源。經過設計團隊深入調研,發現很多廢舊資源、殘墻斷壁均可以作為鄉土景觀素材用于營造村落標識系統、小品、構筑物等景觀。為留住斗帶村特色的“鄉土味道”, 這些鄉土景觀素材一方面為地帶性景觀營造提供了原始素材,另一方面這些素材留住了歷史記憶,為村民生活歷史的延續營造最深刻的記憶。當前斗帶村生活空間的“廢棄資源”主要分為殘墻、廢棄建筑類和建筑殘料磚、瓦、石料等兩類,可以將所謂的磚瓦等廢料與殘墻、廢棄建筑或地面、景觀小品等基礎設施結合,充分利用,營造獨特的“斗帶景觀”。
首先,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形式營造小品、景觀墻、休閑空間硬質鋪裝、坐凳等。所謂“拆東墻補西墻”即將公共空間無用的舊豬舍或被確定為危房等的建筑拆除,將其有用材料補到那些可以通過稍加改造即可作為景觀的實體上。如村后原有小樹林與風水塘之間的殘墻,根據其傳統用途及規劃更新,可將殘墻保留并運用廢舊泥磚將其高度結合需求稍加改善,再在其頂部放置廢瓦片修建成景墻,一方面起到了劃分空間的作用,另一方面保留了村民對場所的記憶(見圖14);又如地面鋪裝可以利用村中廢舊泥磚加入廢舊秸稈做基礎墊層,再用廢舊青磚、石料等鋪設表層,然后再在硬質鋪裝上適當增加鄉土植被營造舒適的休閑空間。這些廢舊材料經過景觀的組合將場地的記憶轉移至景墻、鋪裝等材料語言中,再現了村民記憶中的生活場景[11]。

其次,廢舊建筑改造利用。村落有較多無人居住的舊泥磚房。由于村落的新區與舊區被風水塘隔開,這些舊區泥磚房幾乎沒有受到破壞,大多保存完好。結合村民意見和村莊發展定位,廢舊建筑的利用改造盡量保留原貌的修整,使其再現傳統鄉村建筑風貌,留住鄉愁,為將來發展村落旅游做儲備。對于有部分損壞的泥磚房經過適當改造作為休閑景觀建筑。廢舊建筑改造利用往往涉及農村復雜的產權問題,應深入調研并結合實際情況與村民溝通交流,在充分尊重村民的利益訴求基礎上進行改造。如風水塘旁邊的一處舊泥磚房原為村長舊宅,經設計團隊評估和村長溝通交流,村長非常贊同休閑景觀設計思想,將泥磚房改造為公共建筑(見圖15)。設計師根據現狀及建筑所處位置,將建筑其中一面墻拆除,建筑內部適當整治,營造成三面圍合的公共休閑建筑,為村民提供了遮風避雨的室外交流場所,同時也留住了鄉民的記憶[10]。
4結語
鄉村生活空間中最具特色的景觀就是村民記憶中兒時的老建筑、古樹、舊水井等。這些景觀是家鄉的象征,往往能夠引起人們對童年的回憶和對自然的共鳴。斗帶村結合“縫·補”策略實現了生活空間中破碎休閑節點的空間重構及廢舊資源的有效利用。這些休閑節點猶如圍繞在斗帶村環村道上的珍珠,使村落中原本割裂、無序、雜亂的休閑節點得以完整串聯;其次斗帶村生活空間景觀營造充分整合現有廢棄地及雜物堆放空間,利用廢舊資源,一方面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充分利用舊磚、瓦等廢料結合“殘墻斷壁”營造景觀性和服務性小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舊泥磚房等建筑充當亭、廊之用途營造供村民休閑交往的公共空間,不僅節約了大量資金,還營造了原汁原味的具有本村生活烙印的獨特景觀,使斗帶村傳統文化得以完整的保留和延續。征求村民意見時,項目規劃設計方案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認可,認為是經濟、可行的有效策略。斗帶村實際案例說明,基于“縫·補”策略的生活空間景觀營造方案具有較好的經濟性和可操作性,可為當前鄉村振興背景下改造鄉村人居環境和營造鄉村生活空間景觀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
注:
① 據云浮市云城區建設局提供資料顯示,安塘街道的工業以石材產業為主,是著名的石材產業強鎮。目前全街擁有石材企業1000多家,附近青壯年基本都在石材廠務工。
參考文獻:
[1]龍花樓.論土地整治與鄉村空間重構[J].地理學報, 2013,68(8):1019-1028.
[2]張娟,王茂軍.鄉村紳士化進程中旅游型村落生活空間重塑特征研究——以北京爨底下村為例[J].人文地理,2017(6):137-144.
[3]杜文武,張建林,陶聰.等.彈性理念,鄉村重塑中的風景園林思考[J].中國園林,2014(10):102-106.
[4]田銀生,唐曄,李穎怡.傳統村落的形式和意義——湖南汝城和廣東肇慶的考察[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1:43.
[5]盧素英,袁曉梅.“食·療·景”:嶺南傳統村落生活空間植被特征解析——以肇慶蕉園古村為例[J].風景園林,2017(9):50-56.
[6]趙華勤,江勇.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人居環境改善策略研究[J].小城鎮建設,2019,37(2):9-14.doi:10.3969/j.issn.1009-1483. 2019.02.003.
[7]盧樹彬,翁子添.嶺南鄉村人居環境整治探索——以東莞市石排鎮為例[J].廣東園林,2018(3):4-8.
[8]石好為.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蘇南鄉村生活空間優化研究[D].蘇州:蘇州科技大學,2015.
[9]梁雪.傳統村鎮實體環境設計[M].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10]徐斌,洪泉,唐慧超,等.空間重構視角下的杭州市繞城村鄉村振興實踐[J].中國園林,2018(5):11-18.
[11]盧素英,袁曉梅.蕉園村明清時期棲居環境的“情志”養生特征解析[J].南方建筑,2018(3):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