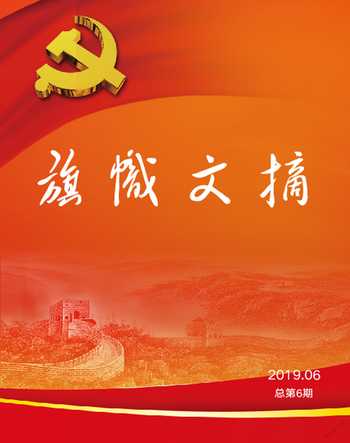《茶館》與《天下第一樓》之悲劇效果比較
李子琳
摘要:《茶館》與《天下第一樓》是當代中國戲劇中具有相似性的兩個作品,這種相似性表現在兩者均沒有按照傳統“三一律”的格式,而是用濃郁的地方語言,以老北京一家茶館和一家烤鴨店為窗口,人物展覽式地描繪時代圖景,道出黑暗時代下的眾生百相和他們的悲劇性命運,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本文將從人物、情節、環境三個角度出發,探究《茶館》和《天下第一樓》這兩部相似作品中的悲劇效果。
關鍵詞:茶館;天下第一樓;悲劇效果;現實主義
魯迅曾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1]文學中的悲劇作品多是表現主角與其他力量(如命運、環境、社會)之間的沖突。西方古典悲劇多體現這種命運觀,即人的抗爭精神在面對命運時的失敗,這種古典悲劇多帶有神話史詩色彩,描寫英雄人物的末路,在悲劇氛圍中體現人生有價值的東西如反抗、斗爭,在命運和神意前的微不足道,“把生的苦惱和死的幻滅通過放大鏡,而后再用極濃的色彩把他們描繪出來”。[2]這類悲劇的高潮與結局往往設置為重要角色的死亡,帶有浪漫主義色彩,悲痛壯烈之感油然而生。
與西方古典悲劇中濃厚的悲劇之感相比,中國古典悲劇多是“散文式”的感傷,不強調人與命運或人與神之間的沖突,多以史實或民間故事為基礎,對其進行藝術渲染,或是描寫才子佳人之間的纏綿悱惻,愛恨糾葛。中國古典的悲劇更像一首哀歌,沒有神話色彩,沒有驚濤駭浪般的沖擊,不會使人產生強烈的命運感,而是感慨歷史的興亡滄桑與人生的愛恨情仇,帶有更多的現實主義氣息。
《茶館》是現代文學家老舍于1956年創作的話劇,《天下第一樓》則是劇作家何冀平于1988年創作,兩部作品同是當代話劇,描寫特定時代下的小人物的悲劇。朱光潛曾在《文藝心理學》中提出“心理距離說”,認為人們對于藝術作品產生的美感源于實際人生與藝術情景之間適當的“距離”。[3]“在成功的悲劇中‘距離’不太遠,因為它所表現的是合于情理的事實;也不太近,因為悲劇的
語言是經過藝術熏陶出來的,它的人物和情節是想象的,不尋常的,于近情理之中卻含有若干不近情理的成分,不至使觀眾誤認戲劇為實際的人生。”[4]
《茶館》與《天下第一樓》中則具有這種適當的“距離”,這兩部作品都以北方方言寫成,描寫平凡的市井生活,富有人間煙火氣,不會使人產生太大的“距離”之感,以現實主義為基調。同時設置三個不同的時代,揭示老北京甚至是整個中國的歷史變遷,描繪歷史環境下小人物的艱辛與無奈,帶有中國古典戲劇作品中“散文式”的悲劇意蘊,給人以凄涼悲愴之感。
黑格爾曾在《美學》中說:“悲劇人物的災禍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須本身具有豐富內容意蘊和美好品質,正如他的遭到破壞的倫理理想的力量使我們感到恐懼一樣,只有真實的內容意蘊才能打動高尚心靈的深處。”[5]我們之所以會對悲劇性人物感到同情,正是因為看到其身上的美好品質在面臨其他力量時的失敗,并為之嘆惋。從同情心的角度出發,《茶館》與《天下第一樓》中的主人公身上都具有抗爭意識,正是這種抗爭意識,讓我們在看到他們的結局時會為之動容。
王利發是《茶館》中貫穿全劇的人物,作為裕泰茶館的掌柜,他深諳為人處世之道,“作了一輩子的順民,見誰都請安、鞠躬、作揖”,精明干練,善于經營,圓滑世故,在老舍極高的語言藝術下,一個伶俐的小商人形象躍然紙上。第一幕中,裕泰茶館掌柜王利發興致勃勃地坐在柜臺上,從他的言語中,我們知道這一人物的基本信息:父親死得早,自己很小的時候便掌管了茶館。“在街面上混飯吃,人緣兒頂要緊。我按著我父親遺留下的老方法,多說好話,多請安,討人人的喜歡,就不會出大岔子。”第二幕,裕泰茶館的生意漸趨衰落,掌柜王利發眼看時局大變,適時地對茶館進行了一次大改良。茶館外兵荒馬亂,茶館內生意慘淡,還時不時遭到巡警特務的敲詐,在這一幕中,王利發雖苦心改良卻無可奈何于現狀,言語中體現出更多的無奈與牢騷。第三幕是話劇的結局,茶館更加破敗,并即將被人霸占。面對暗淡無光的前路,王利發的那一聲聲吶喊,滿滿都是對人世無情的控訴:“我可沒作過缺德的事,傷天害理的事,為什么就不叫我活著呢?我得罪了誰?誰?”王利發最后的自縊行為是他強烈抗爭行為的體現,也使得話劇產生了極大的悲劇效果,王利發這個角色的最大悲劇性也在此,在經歷現實所帶來的打擊后,生命由鮮活走向委頓,只留漫天祭奠自己的紙錢,成為那個動蕩亂世中的犧牲品。他是時代的犧牲者,也是整部作品悲劇效果的直接傳達者。
《茶館》的敘事結構沒有按照傳統的一人一事的格式,而是以“人像展覽式”結構組織人物,與之相比,《天下第一樓》則圍繞主人公盧孟實有一條明顯的主線:從掌管“福聚德”烤鴨店,到將“福聚德”越做越大,再到最終走向失敗,遺憾返鄉。盧孟實這個名字在劇中最早出現是從二掌柜王子西的嘴中,之后盧孟實便出場,從他的談吐中,我們對這個人物形象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不論寫書的司馬遷,畫畫的唐伯虎,還是打馬蹄掌的鐵匠劉,只要有一絕,就是人里頭的尖子”,“船多不礙江,有比著的,才有長進”(第一幕)。從幾句話語中,盧孟實的人物形象初步建立了起來:一個談吐不凡,有見解,精明,深諳處事之道的生意人。到了第二幕,盧孟實成為了“福聚德”的二掌柜,這一幕里,主要講盧孟實如何處理“福聚德”的日常事務,以及與各路人像宮里的人、要債的錢師爺、沒落封建貴族克五以及老掌柜的兩個兒子和“福聚德”其他伙計之間的周旋,這里體現的是盧孟實的處世哲學,講他是如何處理各種復雜的人際關系。在第三幕中,“福聚德”生意達到鼎盛,名噪京師,但盧孟實卻在此時受到老掌柜兩個兒子與克五的陷害,在遺憾中落寞返鄉,離開了自己奮斗多年的“福聚德”。
與王利發等人相比,盧孟實身上具備著更強的主體性意識,“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自由獨立的個體,他意識到自己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需要的東西”。[6]他們同樣身處黑暗中,但盧孟實從始至終不屈服于現實,他在臨危受命之下憑自己高明的為商處世之道將“福聚德”越做越大,并始終為實現自己的抱負奮力抗爭。與之相比,王利發等人更像是被時代洪流推著往下走的人,他們的努力是徒勞掙扎,結局早已經注定。盧孟實雖然最終也面臨失敗,但正因為他更強烈的抗爭精神使得他為戲劇增添了更強的悲劇效果,抗爭愈烈,悲劇效果愈濃。他具有更多的黑格爾所說的“豐富內容意蘊和美好品質”。同是在黑暗中抗爭的人,在人物性格上盧孟實較于王利發更具有悲劇性,而王利發的自縊結局與盧孟實的遺憾返鄉相比更具有戲劇沖擊性。
關于悲劇為何會產生喜感,黑格爾曾在他的《美學》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他著名的“沖突說”:“這里基本的悲劇性就在于這種沖突中對立的雙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辯護理由,而同時每一方拿來作為自己所堅持的那種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內容的卻只能是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或破壞掉。”[7]用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中的話說:“悲劇主角大半象征一種有沖突的片面的理想,他陷于災禍時,在表面看雖似命運造的冤屈,而就宇宙全體來說,實在是‘永恒公理’(eternal justice)的表現。”[8]
《茶館》與《天下第一樓》中具有相似的情節。《茶館》中那些底層的小人物,在黑暗的時代下舉步維艱,他們的求生之道似乎為時代所不容,他們與那個混亂的秩序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雖然《茶館》中沒有一條明顯的主線沖突情節,但能明顯感覺到悲劇就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發生,感覺到人的意志與其他力量之間的對立。那些小人物與造成悲劇的力量之間互相沖突,同時他們自身就是悲劇的一部分,他們又將融入這種力量,在沖突中歸于和諧。在這種矛盾又統一,沖突著同時也將和解的過程里,悲劇就這樣誕生,并且陷入一個又一個的輪回,哭中帶笑,笑中有淚。
而在《天下第一樓》中,這種造成“沖突的力量”更為具象化,落在了劇中的幾個反派人物如老掌柜的兩個兒子和封建沒落貴族克五身上,戲劇將大量的沖突設置在盧孟實與這些角色之間的矛盾上。盧孟實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人物,一輩子想要實現自己“坐轎子”的理想,但作為對立方的唐茂昌和唐茂盛這些人物同樣有自己的利益訴求,這兩種思想無法共存,矛盾由此產生。在一次又一次的沖突中,悲劇緩慢上演,并在最后爆發。同樣是瑣碎的生活,《天下第一樓》中情節上的對立性更加明顯,但這種明顯的對立沖突情節又將悲劇的根源埋藏的更深,盧孟實作為主人公始終體現著對抗精神,這種不屈服的精神稀釋了作品在情節對立中的統一性。
現實主義戲劇的意義絕不在于展示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沖突,而是以戲劇的形式展現日常生活場景,在嬉笑怒罵、冷靜客觀中揭示生活的本質特征,反映現實問題,借以引起人們的思考。《茶館》和《天下第一樓》作為兩部優秀的現實主義題材戲劇,其悲劇內涵不在于表面的戲劇沖突,而是以裕泰茶館和“福聚德”為窗口,再現歷史下的小人物和小人物所處的市井生活。
老舍曾說:“背景的重要不只是寫一些風景和東西,使故事更鮮明確定一點,而是它與人物故事都分不開、好似天然長在一處的。”[9]特定的人物只有放在特定的環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學作品中設置的小環境是時代大環境的縮影,也是大環境中的一部分,了解其中的環境背景我們可以使我們更深地理解作品的真實內涵。而在一部悲劇作品中,無論是人物之間的沖突還是有價值東西的毀滅,時代背景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環境是背后的一雙手,是《寒夜》中汪文宣死去的冬夜,是《駱駝祥子》中祥子永遠買不上屬于自己的車,也是《茶館》與《天下第一樓》中人物悲劇的根源。
《茶館》中設置了三個時間:戊戌變法、軍閥混戰、新中國成立前夕,時間跨度進半個世紀。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各路人物紛紛登上歷史舞臺,你方唱罷我登場。茶館不屬于一個大的歷史中心舞臺,老舍也沒有對人物所處的社會環境進行直接說明,但在這個地方始終能看到社會歷史的影子。
《茶館》第一幕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茶館剛開業的一個上午,三三兩兩的茶客在這里喝茶、看戲、斗蛐蛐。茶館似乎處在一片安靜祥和的氛圍中,但到處貼著的“莫談國事”的紙條又隱隱象征著時局的不安定。常四爺一句“大清國要完”,便被兩個特務抓進了監獄,在茶館表面平和的環境背后,似乎有暗流涌動。第二幕,到了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時期,茶館外兵荒馬亂,“趙打錢,孫打李,趙錢孫李亂打一炮誰都不講理”。抓走常四爺的兩個特務成了軍閥的走狗,并時不時有特務、巡警、兵痞來茶館敲詐勒索,茶館漸漸難以為繼,呈現破敗的趨勢。第三幕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特務和美國兵在北京橫行,“莫談國事”的紙條寫的更多,字也更大,各路小人物的生活更加艱苦。常四爺窮困潦倒,秦仲義工廠被搶,王利發的茶館也將被霸占,三人最終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夕走向生命的終點。不管是主人公還是登場不多的小人物,他們的走向均與時代息息相關,時代是背后操縱的大手,但它又像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審視著我們,每一個人的掙扎與苦難皆看在眼里,但是又一言不發。時代和社會環境是悲劇的根源,這種將小人物的悲劇放置在歷史大環境下的寫法,給悲劇籠罩上了濃厚的歷史氛圍,增添一分悲涼與深重。
同樣,《天下第一樓》中也設置了三個時間:1917、1920和1928年,同是黑暗混亂的時期,《天下第一樓》中的時間跨度沒有《茶館》中的長,但依然能看到時代和社會環境的影子。在第一幕,此時黎元洪退位,皇帝登基,象征清王朝的龍旗再次掛起。“福聚德”里的一個伙計說起自己的辮子:“我是盤上了,革命來了盤上,皇上來了再放下來”,用小人物的言語反映了當時大多數底層人民的心態。到了第二幕1920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皇權再次下臺,克五被抄家,宮里來的執事也對盧孟實無奈地說:“民國了,沒那么多說頭了”。第三幕是1928年,此時是八年后的國民政府時期,體現時局的情節不多,但盧孟實有一句:“皇上都在日本租界當了寓公了,這規矩早該改改了”。最后的尾聲,警察在通知“福聚德”再次掛旗的時候說了一句話:“甭管張三、李四誰當掌柜的,也得烤鴨子,不論皇上、總統、長毛、大帥,誰來也得吃鴨子,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警察的一番話頗有內涵,不管時代如何變幻,人性在古往今來的樣子大抵相同,歷史不管如何推移,大都如這赫赫有名的“天下第一樓”一樣隨時代浮沉,走過人生興衰。《天下第一樓》中關于歷史環境的成分沒有《茶館》中的多,但同樣環境作為悲劇的根源導致了盧孟實的失敗與這“福聚德”的變遷。
苦難若只為了表達苦難,便失去了苦難的價值,文學作品真正探討的,其實還是“人”的問題。《茶館》和《天下第一樓》也是這樣,悲劇絕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展現人性的一種方式。
《茶館》是一部時間跨度長、人物眾多、事件龐雜的藝術成就極高的話劇作品,也是舊社會的一曲葬歌,老舍將歷史的三個片段連在一起,表達了“葬送了三個時代”的主題。[10]在劇中的結尾,王掌柜死后,唱串場詞的傻楊唱起了幾句快板:“小姑娘,別這樣,黑到頭兒天會亮。小姑娘,別發愁,西山的泉水向東流。苦水去,甜水來,誰也不再作奴才。”王利發等人的死去意味著舊時代的滅亡與同時也象征著新時代的來臨,讓我們在黑暗中依稀看到渺茫的希望,為悲劇增添了一點明亮的色彩,就像魯迅小說《藥》中夏衍墓前的花圈,也是沈從文《邊城》里翠翠在憧憬明天中的等待。
而在《天下第一樓》中,除了表達出對歷史興亡的感嘆,更多的是對人生的參悟。“起初是生活,再提高到文化,再從文化升華到治國,后歸結到人生的蒼涼,這個戲的成功就是從底層寫起,一步一步起高樓……”,[11]這部悲劇作品最大的內核是人生的無奈,正如結尾那副對聯所寫:“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只三間老屋,時宜明月時宜風。”生活本是最大的悲劇制造者,平庸和無奈都歸于落寞,繁華與興盛都歸于平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那些歷史舞臺上的大人物或小人物都將隨落幕而留在時間的角落里。大多數人生來平凡,人生向來艱辛,但不妨礙我們在苦難中展望希望的未來。兩部作品均以悲劇結尾,但同時給人以希望,在希望的映襯下使得悲劇更加悲涼,真正達到哭中有笑,笑中有淚。人生是最大的舞臺,人性便是這舞臺上最好的演員。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雜文精選集[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
[2][8]朱光潛,談美 文藝心理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2.
[3]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2.
[4]朱光潛.談美 文藝心理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2.
[5][7]黑格爾.美學 第三卷(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6]魏征徽.從《茶館》到《天下第一樓》——論劇作家的主體精神[J].戲劇叢刊,2014(4).
[9]老舍.作家論創作(上)[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
[10]老舍.答復有關《茶館》的幾個問題[J].劇本,1958(5).
[11]何冀平.我一直帶著微笑去看[J].東方,2001.
(:北方文學 2019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