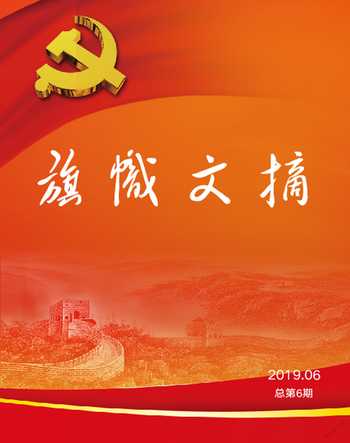遇見,從紫鵲界到翡翠湖
遇見,是生命的期許,是心頭的企盼,不可把控,更無法拿捏。在我旅行攝影行色匆匆的奔波中,極幸運和難忘的遇見,是紫鵲界。在遇見的一瞬,我與紫鵲界彼此都被點燃。
人有各色各樣的矛盾,景點也有。紫鵲界,似乎就面臨文化品位高與知名度略低的矛盾。
大規模的梯田,是最能體現人類智慧的作品之一,已是世界著名旅游景點的云南元陽哈尼梯田,是1000多年前哈尼人的杰作;廣西龍勝梯田,則是650年前的瑤族和壯族人攜手創造的奇跡。而位于湖南省婁底市新化縣水車鎮,屬雪峰山脈的紫鵲界梯田,據考證,起源于先秦,盛于宋、明,已有兩千余年的歷史,無論規模還是形態,都不亞于哈尼梯田和龍勝梯田。
然而,盡管紫鵲界梯田已經擁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國家自然文化雙遺產、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國家水利風景區等一長串不小的名頭,但背后的知名度卻似乎與名頭不很般配。
環顧四周,紫鵲界梯田正處在湖南優秀旅游文化資源的環抱之中,不免有些委屈——不遠的西北側,是因沈從文妙筆生花而聞名遐邇的湘西民俗資源及世界自然遺產武陵源;東北部,則是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之稱的岳陽樓,以及歷史文化名邑長沙;東邊韶山,矗立著千古偉人毛澤東故居;東南邊,矗立著“五岳獨秀”的南岳衡山,無不人文底蘊豐厚,揚名國際國內。群星璀燦,紫鵲界梯田的天然古樸人文光彩,的確不太容易引人注目。
據湖南省政府參事、著名作家弘征 《紫鵲界梯田初墾于秦漢之前考》 ,距今2000多年前,古稱苗瑤的一支南方少數民族為躲避異族欺凌,整體遁入群山環繞的新化縣奉嘎山紫鵲界一帶。大大小小30多座海拔超1000米的山峰,構成了庇佑這支逃生民族的天然屏障。而崇山峻嶺的基巖裂隙中,水資源竟然出人意料地豐富,凡有裂隙處,就有泉水涌流。于是,他們就依山就勢,年復一年,代復一代,挖出了一小塊一小塊梯田,種上單季稻,竟然旱澇保收,足夠族人糊口養命。
后來,由于官府征伐不斷,大部分苗瑤人繼續四散逃亡,其中一支后來逃到廣西龍勝,復制出了后來最早著稱于世的龍勝梯田。
由于紫鵲界梯田依靠森林植被、土壤、田埂綜合形成儲水保水系統,加上神奇獨特的基巖裂隙、孔隙水源,天然形成人類最偉大的水田自流灌溉工程。泉水潺潺,久旱不枯,山洪無澇,水依山勢順序灌溉梯田,旱澇保收。到宋元時期,已經有“天下大亂,此地無憂,天下大旱,此地有收”的美譽。外地漢人開始遷入紫鵲界開墾梯田,到明朝初年,梯田開發進入新的高潮。如此歷經苗瑤族人和漢族人1000多年的持續開發,最終形成了極其罕見的紫鵲界梯田人文奇觀。梯田總面積120平方公里,最高處海拔1585米,層層疊疊的梯田以紫鵲界為中心向四周綿延,在海拔500米至1200米之間,坡度30至50度之間,共500余級,面積8萬余畝。在海拔1600多米的風車巷絕頂,勤奮智慧的古人都修建了供種田人勞作休息的茶亭,足見其燦爛輝煌程度。
本為歷史文化品位極高的旅游產品,卻因思維所囿、宣傳不力,這個苗、瑤、侗、漢等多民族歷代先民共同智慧的結晶,這塊藏在深山人未識的旅游瑰寶,卻沒有達到哈尼梯田和龍勝梯田驕人的知名度。其旅游開發綜合水平,似乎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在紫鵲界,春日水光山色,人們繡花似地整理梯田,除雜草、修田塍,將窄窄的田埂整飭得十分精致、利落,又一鋤一鋤地翻鋤田泥,搗爛、耙平,灌上適量的水,再在燕子的呢喃聲里插上青青的禾秧,經夏日驕陽的烘煉,禾苗在陣陣鳴蟬與山林昆蟲的交響樂中灌漿生長、抽穗揚花。金秋時節,稻浪滾滾,滿山層層金黃。
現代化的打谷機設備等在這里沒有用場。人們把四方禾桶扛到梯田里,雙手揚起一捆捆稻子,重重地砸在禾桶板上,把谷粒從稻稈上震脫下來,再把打下來的谷粒滿滿地裝進籮筐,肩挑,手扶,沿著窄窄的田埂送下山去,一路走,一路歌。
“深山歸月下,曲徑隱云中。”山外歲月千年,山中時光流轉。現今的紫鵲界人們,一如2000年前的先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歲月扛在肩上,把生活拽在手里。恰如我們攝影者用鏡頭耕耘光影,這里的人們用鋤頭和鐮刀守護心田、雕刻時光,承繼先人的財富與榮光。
遇見紫鵲界,仿佛是遇到戲文中羞澀矜持的大家閨秀,水袖一拂,將嬌顏藏在黛色的山巒后。這是我喜歡上攝影后最好的遇見之一。
雨后的紫鵲界,云霧濛朧,恍若人間仙境。山巒仿佛失了根基,漂浮在梯田上方,空中樓閣一般,展露著神秘優美的輪廓。云霧散去,露出一團團俊俏的山巒和線條優美、風韻萬千的萬畝梯田。漸漸地,“亭臺樓閣”顯露真容,如絕色女子摘下面紗,重重綠意,在梯田旁環繞。
她是“長空寥廓,云霧逶迤”,她是“千里煙波,霧靄沉沉”,她是“粗服亂頭,不掩國色”,她是“一朝成名,誰人不知”。
在我癡迷攝影、喜歡遠足的數年光陰中,紫鵲界的朦朧詩意與我所見佛國緬甸的禪意,一度讓我欲罷不能。
緬甸與中國毗鄰,同樣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
緬甸的佛教雖然沒有印度佛教歷史悠長,但也有一千多年,佛教被緬甸尊崇為國教。緬甸最具禪意的景點是烏本橋、蒲甘和茵萊湖。
地處曼德勒的烏本橋建于1851年,長1200米,全橋完全由柚木鉚合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長的柚木結構橋。傍晚,古樸的木橋倒映在悠悠江水中,一輪紅日緩緩落下,橋上行人來來往往,唯美的剪影,使這片金紅色的世界更添幾份禪意。
蒲甘是一座坐落于伊洛瓦底江畔的古城,盡管占地僅40多平方公里,但在歷史上卻擁有數以萬計的佛塔廟宇,與柬埔寨的吳哥窟、印度尼西亞日惹的婆羅浮屠并稱為“東南亞三大奇跡”。據考古學家證實,蒲甘曾經至少屹立著1.3萬多座佛塔,而在當地民間傳說中,佛塔的數量更是多達448.6萬座之多。在斗轉星移之間,蒲甘佛塔歷經劫難,大多被歷史的塵土湮滅,僅2000余座留存至今。蒲甘佛塔建筑精美,氣勢恢弘,在緬甸佛教建筑中堪稱翹楚。
茵萊湖位于緬甸北部撣邦高原的良瑞盆地,為緬甸第二大湖,緬甸著名的游覽避暑勝地。湖面海拔970多米,南北長14.5千米,東西寬6.44千米,三面環山,來自東、北、西三面的溪流注入湖中,向南匯入薩爾溫江。湖水清澈,陽光直射湖底。茵萊湖的漁夫個個身懷絕技——一只腳站立船頭,另一只腳劃槳控船,一只手撒網或用竹籠打魚,另一只手握著魚叉,穩如泰山。
異國他鄉,遇見這種在窄窄的漁船上的生活舞蹈,讓我陡然想起那些挑著稻谷穩穩地走在紫鵲界梯田窄窄田埂上的人們。不同的場景,相似的生命張力,在我的鏡頭間彌漫。勞作,原本是天下最美、最青春的贊歌。
說到茵萊湖,我不得不提青海的大美鹽湖。青海鹽湖多,最為有名、人們最容易想到的是大柴旦鹽湖和茫崖鹽湖。
地處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內的大柴旦湖,是一些形態迥異、深淺不一的鹽池,它們宛如一塊塊晶瑩剔透的翡翠,因此,人們更樂意稱其為“翡翠湖”,原本的名稱反而讓人覺得陌生了。
這原本是一個采礦區的遺存。因為礦物元素的原因,使得湖水在陽光下呈現出翡翠的青翠色。當我們站在湖邊,鏡面般的湖面倒映著高天上的藍天白云和遠處的皚皚雪峰,讓人恍若置身仙境一般。
陽光下的茫崖翡翠湖,更是猶如附帶濾鏡的鏡片,鑲嵌在祁漫塔格山下,煥發著祖母綠似的寶石光,讓人驚艷。尤其在無風的時候,水面波紋不驚,綢緞鏡湖般散布在四處的湖面,純美剔透,淡青、翠綠、深綠顏色的湖水,如同遺落人間戈壁的翠玉。
這里幾乎稱得上是新的“天空之鏡”。如果說,大柴旦湖,是嬌小玲瓏的小家碧玉,那茫崖翡翠湖,就是大氣端莊的大家閨秀。
從紫鵲界到茵萊湖;從紫鵲界到翡翠湖,文明不分地界,文明跨越國界。所有的遇見,都不期而遇;所有的遇見,都是震顫心靈的歷史瑰寶,都是攝影者常駐心頭的綿長思念。
我于1963年出生,畢業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地空導彈學院 (現空軍工程大學)。我遇見紫鵲界實屬偶然,正如我極其偶然地喜歡上攝影一般。
2016年5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帶著放在家里多年的一部佳能50D相機隨一幫攝影愛好者去霞浦玩。
在霞浦,我遇見了被譽為中國最美的灘涂,海岸線長達404千米,春去秋來,寒來暑往,每一個季節,大自然都賜予它千變萬化的景致。隨著潮漲潮落、風吹浪打的洗禮,泥沙沖擊的海灘變成了歲月的漣漪。霞浦的灘涂,有時猶如濃墨重彩的油畫,有時又如輕描淡寫的水墨丹青。看著這如夢如幻的美景,我不知所措,無所適從,只能用相機自動檔拍些旅游“打卡”照。盡管如此,心里仍然美滋滋的,因為我感受到了攝影的無窮魅力和樂趣。
不經意的旅行遇見,讓我萌生了鉆研攝影的念頭,并毫不猶豫地踏入了這條令我至今仍如癡如醉、為之瘋狂的風光攝影之路。
一晃三年過去。幾乎所有的假期和業余時間,我都用在了攝影學習上。不是在旅途的路上,就是在創作的現場;不是在網上學習,就是在電腦前修圖。功夫不負有心人,三年的努力,讓我逐漸掌握了風光攝影前后期的基本技巧,個人藝術修養和審美能力也得以大幅度地提高。因為攝影,我過去多年形成的一些不良生活習慣,也在不知不覺中消燼,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亞當斯說過:“我們不只是用相機拍照。我們帶到攝影中去的是所有我們讀過的書、看過的電影、聽過的音樂、愛過的人。”從部隊到地方,從年少青澀到斑首滄桑,透過鏡頭,才發覺當今的世界和原來的世界、現實的世界與理想的世界,何其迥異,卻同樣多彩。三年攝影歷程,無論是定格風景還是牽手邂逅的友人,得到的是從身體到靈魂的真正自由,那才是屬于我自己的快樂!
在年過半百、生命走向末途之際,我遇見了風光攝影。通過攝影,又遇見了紫鵲界等人間絕景。生命因不期而期的遇見而再煥光彩、重返歸途。
鄧文佐:網名雪狼,男,1963年生,畢業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地空導彈學院( 現空軍工程大學) ,轉業軍人、中國財政攝影協會會員、香港中國旅游出版社資深簽約攝影師、視覺中國簽約攝影師、圖蟲認證資深風光攝影師。
(:中國周刊 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