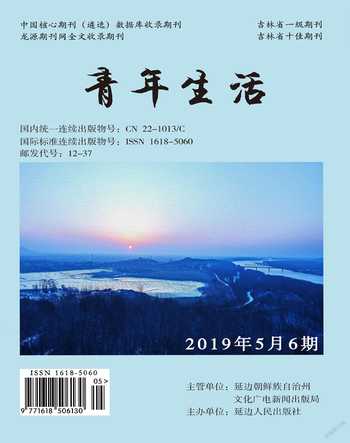“一帶一路”背景下“南方絲綢之路”發展的新機遇
岳崇磊
摘 要:“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已經開展了多年,這條極具時代里程碑意義的發展之路為古老的“絲綢之路”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在“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兩大戰略的背景下,“南方絲綢之路”再次煥發生機,四川作為西南交通上不可或缺的銜接點,也將在這兩大戰略的扶持下發揮其極大的作用。
關鍵詞:一帶一路;南方絲綢之路;新機遇
一、引言
“絲綢之路”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概念,隨著時間、空間的不斷變化,其內涵意義也在不斷的發生著改變。我們“一般認為,德國的地質地理學家費迪南德·馮·李希霍芬(1833-1905)在1877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國親歷旅行記》(簡稱中國)中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一命名的”,但他所指的是我們最為熟悉的由西安經敦煌,出云門關進西域的這樣一條著名的由張騫打通的道路。但是在中國對外交通史上中國的對外交流道路并不僅限于此。這里筆者所提及的“南方絲綢之路”也被稱為“西南絲綢之路”,這條道路不僅僅是漢武帝為統治西南夷而命張騫開鑿,它還是西南夷對外交流溝通的重要通道,西南夷的活動軌跡與漢王朝的統治恰好形成了相互補充的態勢,共同促成了這條對外交通道路的形成。
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發展潮流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本著“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則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發展,發掘各地區的發展潛力,促進各地區與世界市場更好的交流與融合。四川憑借這又一重大機遇,將會在傳統的交通線上發揮其更大的地理區位優勢與文化經濟優勢,如何打好這張牌,如何把握好歷史的機遇將四川打造成內陸開放經濟高地之一就顯得至關重要。
二、“南方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
“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西南地區連接南亞、東南亞等國家的主要交通線路,所以又被稱為“西南絲綢之路”。相對于費迪南德·馮·李希霍芬所提出的“絲綢之路”的概念而言,“南方絲綢之路”更加具體化,但它是一個屬于廣義范圍下的名稱,這也是根據學者林梅村所歸納出的六條溝通中西的交通線路即“除了沙漠之路這條干線外,絲綢之路還有許多重要的分支線路,他們是1、草原之路;2、海上交通;3、唐蕃古道;4、中印緬路;5、交趾道”的出的結論,其中唐蕃古道、交趾道、中印緬路都屬于南方絲綢之路的范疇。關于四川與南方絲綢之路的關系,根據相關學者考證“早在舊石器時代,印度北部、中國、東南亞的舊石器就具有某種共同特征,即所謂砍砸器之盛行。”這也從考古學的角度說明了中國與印度北部、東南亞等國在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了某些文化上的相似性,同時這也表明,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溝通交流在這一時期就已經開始了。
其次,我們根據司馬遷《史記》所記載的“西漢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在出使大夏時見到了從身毒國(古印度)轉運出去的蜀布、邛竹杖”,《史記》中所記載的“身毒”即現在的印度,我們可以看到蜀布以及邛竹已經從四川被輸送到了印度,再由印度到達中亞地區。四川古有蠶從王,號為蜀國,“蠶”“蜀”皆與絲織業有關,再者成都舊有錦官城之稱,更是說明這里盛產錦、布等織物,因此才會有大量的蜀布流傳到印度。這些物品正是通過中印緬路、交趾道等南方絲綢之路到達的國外。
由成都出發的這條貿易通道“其主干道分東西二路,西路(即古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雅安、西昌,渡金沙江入滇,經大姚到大理;東路亦從成都出發,沿岷江而下,經樂山、宜賓,沿秦修五尺道南行,入滇后經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到達大理,東西二線在大理匯合后,經保山、騰沖到達緬甸,再西行至印度。”正是通過這樣的一條交通線路,使得四川這樣一個西南內陸城市能夠與東南亞、南亞各國聯系起來,同時絲路的對外交流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不僅是蜀地將這里的物產輸送到國外,所以“早在戰國時代,就有印度、緬甸等地的商人,通過‘絲綢南路’把貝幣帶到云南”原產于印度洋的齒貝被作為一般等價物大量的出現在云南、四川等地的考古現場,是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堅忍不拔的意志力,佩服他們的敢于開拓的勇氣。“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這是李白寫下的千古名句,但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古人依舊能夠開辟出這樣偉大的對外貿易之路,將我們古老的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相銜接、溝通、交流,這是偉大的創舉,因此就有學者指出“幾條絲綢之路里面,最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西南絲綢之路”。但是,相比較于我國北方的絲綢之路而言,這條西南通道則被國內學者重視不夠,但是它的歷史地位以及歷史意義卻容不得我們輕視。
三、“南方絲綢之路”的當代意義
歷史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在歷史的長河中,交通線路更是如此,也是經過不斷的優化選擇才被保留了下來,這條線路從它初現端倪開始其大致方向就不會再發生大的改變。在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背景下,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順勢而生,這是一條以古絲綢之路為基礎,結合現代綜合立體交通通道展開的以城市帶動區域發展,以域內貿易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優化配置為動力,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和社會共同發展的開放型區域一體化發展與合作網絡。“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南絲路’沿線各國發揮地緣優勢,進一步鞏固政治互信、深化投資貿易、促進互聯互通和加強人文交流顯得更為重要。”在這個新的歷史節點,“南方絲綢之路”再次迎來的時代的復興。
四川作為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有著獨特的區位優勢。近代以來,四川的交通條件得到的很大的改善,抗日戰爭時期成為眾多難民避難的理想場所,大量人口的流入為這里帶來新的勞動力以及生產技術,特別是在國家積極提倡大力發展三線建設時期,這里的工業得到了跨越式的發展,為如今憑借“一帶一路”東風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同時,四川處于長江經濟帶的上游地區,是連接長江下游與西南內陸的重要樞紐中心。同時四川還緊鄰關中天水經濟帶,與西北內陸也有著密切的經濟聯系。所以四川其經濟地位以及交通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一帶一路”的發展起源于古代貿易,同時又是各地區、各國之間文化交流的大通道,這不僅僅是一條商業貿易之路,同時也是一條文明交流之路、文化共生之路,加強四川文化的對外交流是提升四川對外交流、開放中地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因此,加強教育、人才領域的合作,積極開展對外教育和人才培養合作,加強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交流,提升人才培養水平,積極吸收更多的高素質、高學歷、高技術人才則顯得極為迫切。加快四川與東南亞、南亞各國的高等教育合作,積極促進與東南亞、南亞各國的國家職業認證以及學歷認證,推動中國學生赴外留學以及吸引留學生來中國交流學習,都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交流活動平臺。其次,以旅游促進文化交流。四川是一個比較突出的旅游大省,具有極其龐大的旅游資源,每年吸引眾多國內外游客前來觀光旅游,極大的推動了四川的對外交流發展。根據統計顯示,四川在發生了多次自然災害旅游受到嚴重的2018年依舊能夠實現全年旅游收入10%以上的增長幅度。所以繼續堅持“旅游+”的經濟發展模式將進一步推動四川地區脫貧攻堅工作的開展,這也將帶動四川眾多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
四、小結
從歷史長河來看,絲綢之路不是一個具有固定線路的空間現象,而是一個文化符號,其內涵是“和平、友誼、交往、繁榮”。四川將借助“一帶一路”的東風,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憑借“南方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底蘊,積極融入到“一帶一路”的建設發展中,把握時機,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合作,服務于國家需要,致力于國家戰略的實施,以開放、包容、和諧的態度迎接更大的國際市場,在古絲路的基礎上,發揮現代交通優勢以及科技優勢,以點帶線,以線帶面,以面帶區促進貿易、文化、科技等資源的優化合理配置,將最終實現區域經濟與社會共同發展的開放合作新格局。
參看文獻:
[1]王健.“近代絲綢之路”:從“絲綢之路”到“一帶一路”歷史跨越的重要節點[J].南京社會科學,2017(3):144.
[2]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4.
[3]段渝.中國西南早期對外交通——先秦兩漢的南方絲綢之路[J].歷史研究,2009(1):12.
[4]司馬遷.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M].北京:中華書局,1963:999-2996.
[5]李俊.西南絲綢之路與云南貝幣的流通[J].云南文物,1994(38).
[6]熊勇忠.云南古代用貝試探[J].云南文物,1986(20).
[7]李學勤.三星堆文化與西南絲綢之路[A].巴蜀文化研究集刊·南方絲綢之路論集[C].成都:巴蜀書社,2012:11.
[8]范建華,齊驥.論云南在國家向西開放戰略中的地位與作用——開放大西南重振南絲路的戰略構思[J].學術探索,2014(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