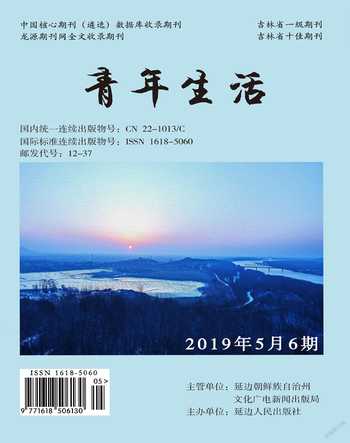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困境及完善路徑研究
苑權菲
摘 要:我國于2010年重新修訂《國家賠償法》時,正式確立了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這突出表現了我國公權力機關對人權的充分保護與尊重,這在一定程度上雖然體現了我國國家賠償制度的一大進步,但與域外國家相比,依舊存在著些許不足之處。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國家侵權賠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新時代要確保廣大人民能夠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必須進一步完善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尤其是賠償范圍和數額標準。
關鍵詞:國家侵權賠償;精神損害賠償問題;改進路徑
一、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內涵及構成要件
(一)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內涵
精神損害主要指人的心靈或感情上因侵權行為所導致的痛苦和創傷,這種傷害是一種非財產上的損害,無法用經濟價值進行衡量。我國現有的民事法律規范所指的精神損害賠償指的是自然人在人身權或者是某些財產權利受到不法侵害,致使其人身利益或者財產利益受到損害并遭到精神痛苦時,受害人本人、本人死亡后其近親屬有權要求侵權人給予損害賠償的民事法律制度。而在國家侵權賠償領域,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可以界定為: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而給被侵權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并產生嚴重后果,賠償義務機關對被侵權人的精神損失所做出的賠償。
(二)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意見》,在第3條中明確指出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家侵權行為。從當前的法條可以看出,我國現在的國家侵權行為主要是以作為的方式實施。但是應當注意的是,依據以往法院所作出的判例,此處的侵權行為還應當包括那些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履行其應履行的職責而導致的相對人合法權益被侵害的情形。
第二,致人精神損害。此處的致人精神損害是指實際發生的損害結果,否則,不會產生賠償責任。可以看出,精神損害發生的實際結果是國家侵權責任產生的前提和基礎。我國當前在國家精神賠償領域只針對被侵權人的直接的精神損失進行賠償,而不包括其因精神損害而進一步衍生出來的間接的財產性利益損失。
第三,因果關系。國家賠償法中的因果關系指國家侵權行為與受害人精神損害結果發生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系。也就是說,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非法行使職權的行為和受害人客體的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只有這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國家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否則國家就沒有賠償責任。因此,“因果關系是聯結侵權主體與損害的紐帶,是侵權主體對相對方的損害承擔法律責任的基礎和前提。”如果兩者之間缺乏這種因果關系,受害者就無權申請國家賠償。
二、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困境
在我國,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經歷了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如今新的《國家賠償法》雖明確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的內容,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國家侵權賠償制度,但該制度依舊存在不足之處。
(一)性質定位失真
對于精神損害賠償的性質界定,學界一般認為有三種,即:撫慰性、補償性、懲罰性。撫慰性賠償是指國家侵權賠償義務機構對在一定侵權范圍內對受害人造成的損害提供適當賠償,以緩解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補償性賠償是指國家侵權賠償義務機關對受害人的賠償可以在金錢上等價填平其精神損失。懲罰性賠償指國家侵權機關不僅要在金錢上等價填平受害人的精神損失,同時還要承擔額外的懲罰性責任。由此可見,賠償性質的定位不同,決定了對被侵權人的損失救濟程度也大不相同,同時給國家財政帶來的負擔也有較大差距。
我國無論在法律規定還是在司法解釋中都體現了“撫慰”的性質,可見我國的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金依舊是撫慰性賠償。而相比之下,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則體現出補償的性質。相對私權利而言,公權力的侵權行為對被侵權人所造成的精神傷害往往比民事侵權行為更加嚴重,傷害程度也更大,因此國家侵權精神損害本應當獲得更高的賠償金,然而在實際的立法中卻恰好相反,這極其容易導致被侵權人對制度不滿意。當前,我國已經步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的經濟實力也有了顯著提升,我國的社會基本矛盾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繼續把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定位為撫慰性的,顯然是不利于實現補償被侵權人精神損害的立法目的,也不利于實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國家賠償法》需要適時轉變精神損害賠償的性質定位。
(二)精神損害賠償范圍狹窄
我國《國家賠償法》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相關適用范圍只局限在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和生命健康權這樣的部分情形之中,其所保護的權利客體相對而言還是太過單一。公民在實際生活中遭受精神損害的情形其實遠大于這兩種情況,只是說侵犯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相對而言更為直接,其實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施的侵犯公民財產性權利同樣會對公民造成巨大的精神損害。例如在強制拆遷房屋和強制征收征用土地等案件中,尤其是拆遷房屋,這是公民賴以生存的場所,有的甚至是幾代人生存的地方,每個人經過了長期居住之后會產生極其強烈的歸屬感和依賴感,部分案件在強拆中還涉及一個家族中的祠堂、祖屋等,這無疑會給他們帶來極其沉重的精神損害,而且這種損害還不只局限于一個人。
同樣與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相比,則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要比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所保護的權利客體要廣泛得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就將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權之外的其他人格權也納入了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還包括一些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由此可見,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要遠大于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狹窄會導致被侵權人的部分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適時擴大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是極其必要之舉。
(三)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細化標準缺失
目前,雖然《國家賠償法》及其司法解釋已對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作出了相關規定,但由于精神損害難以量化并具有無形性,導致了精神損害賠償標準的確定是非常困難,這一問題在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中同樣存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意見》在第7條第2款中就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分別作了上、下限規定,此規定依舊比較籠統,并沒有對具體情形進行分級,同時考慮到各地的具體情況可能百分之三十五的上限對受害人的精神損害根本起不到撫慰效果,更談不上補償作用。
在相關的法律或司法解釋中沒有將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進行標準細化,將造成在賠償過程中的賠償數額缺乏量化,由此而造成一些負面影響。為了避免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結果,非常有必要在法律或司法解釋中將具體的精神損害賠償標準進行分級量化。如果法官對于賠償數額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就會導致賠償數額過低或過高的后果,也不利于樹立司法權威;倘若數額過低,則對于被侵權人難以起到抹平其傷痛的效果,而數額過高又不利于裁判之公正,還大幅增加國家財政負擔。由此可見,一個公正合理、操作性強的精神損害賠償標準是合理計算侵權賠償數額的基礎,同時也是維護法院和法官司法權威的有力保障。
三、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制度的改進路徑
(一)從撫慰性賠償轉向補償性賠償
《國家賠償法》將精神損害賠償定位為撫慰性賠償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已不足以體現立法功能,應當及時轉變這一性質定位,由撫慰性賠償轉為補償性賠償。至于懲罰性賠償,就我國目前的國情而言還不太適合,這是因為它主要是針對主觀惡性極其嚴重的侵權主體所做出的行為,同時其賠償額度極高,導致國家的財政負擔過重。
將撫慰性賠償定位轉變為補償性賠償定位,可以充分體現對公民權利的救濟理念,而不再僅僅是撫慰功能。這一轉變的意義有以下幾點:第一,補償性賠償的基本原則就是“損害多少補償多少”,在立法中采用這樣的補償標準能夠更好地彌補被侵權人在精神方面的損害,充分緩解公私權力之間的緊張局面,有利于社會局面的和諧安定。而當前的撫慰性標準只對被侵權人的傷害給予適當補償,難以對公民的精神權益起到保障作用。第二,補償性賠償可以提高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辦事的積極性,同時也有利于提高行政執法、司法水平,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第三,我國當前已經步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人民開始日益追求其幸福美好生活,補償性賠償是對公民精神性權利的充分保障,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保障公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另外,就財政負擔來講,我國目前的經濟實力已經有了顯著提升,強大的經濟基礎可以為保障公民精神權益可供充分的物質基礎。
(二)適當擴大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
目前,《國家賠償法》關于適用范圍的規定主要是采用列舉式,這樣雖然更加方便法律的明確適用,但同時也導致了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狹窄。而《侵權責任法》則將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界定為侵犯人身權益所造成的嚴重精神損害,這種結果歸責的立法方式在判定精神損害之時,便不需要談論侵權行為,只要結果造成了嚴重精神損害就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因此,為了充分實現《國家賠償法》中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目的,應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精神損害賠償對象的范圍,應當采用“概括+列舉”的形式。
相對而言,我國民法上規定對一些特定的人格意義的紀念物品的損壞,如私人信函、珍貴照片、愛人遺物等,可以要求損壞人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這些物品一旦損毀將永遠不復存在,也不可恢復,此時該物品已經具有一定的人格利益。此時如果因為國家征收、征用或者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非法行使職權而造成物品損壞,對被侵權人造成物質損失倒是次要的,但卻深深地傷害了其情感支持,給其造成嚴重的精神損失。針對現代愈演愈烈的暴力拆遷、城市規劃中任意毀損民房等現象,很多情況下嚴重損害了公民的財產權,甚至有些是祖輩遺留下來的,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公民的精神痛苦。因此,將具有特定人格意義的物品納入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是當前形勢之所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進一步細化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等級并酌情提高賠償數額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意見》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采用“最高限額 + 最低限額補償法”的客觀基準不夠明確細化,致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依舊較大,同時考慮到各地的具體經濟發展情況各不相同,對于部分省份此上限確實相對較低,甚至難以發揮撫慰效果。
近年來,各地在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實踐中紛紛嘗試引入客觀基準,結合當地的實際生活水平具體劃定現行精神撫慰金的區間,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廣東省公安廳聯合發布的《關于在國家賠償工作中適用精神損害撫慰金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第9條將國家侵權精神損害撫慰金額根據限制人身自由的時間長短劃分出八個層次,國家侵權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根據限制人身自由的時間長短在這八個層次中確定。再如浙江省高院在《會議紀要》中指出,國家侵權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以人身自由權、生命健康權等損害的國家賠償總額的50%為基準,再按照案件具體情況酌情增減,但最高不得超過其總額的100%,在這一范圍內確定具體賠償數額。
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之下,最高人民法院應該在司法解釋中進一步細化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具體等級,可以依據被侵權人被羈押的天數和受侵害的程度來劃分賠償等級,并應當指出部分案件可以依據案情以及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適當提高最高額的上限。就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完全可以在有條件的地區突破35%的上限,而且在實踐中,也確實有案件已突破了35%法人上限,如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等。由此而知,最高人民法院應該將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標準進一步做細化規定,明確在何種特殊情況下可以突破35%限額,并應當限定即使在特殊情況下其最高的限額也以100%為上限。同時為了防止法官在此空間內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可以適時發布一些指導性案例,為法官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馬懷德.國家賠償問題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6.
[2]劉麗芝.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賠償系列案例評析[D].湖南師范大學,2017.
[3]金麗.論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D].中南民族大學,2012.
[4]謝曉彬.行政賠償中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D].西南政法大學,2016.
[5]高云.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撫慰金數額的裁量[J].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13,28(02).
[6]李玉潔.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撫慰金數額的確定——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為視角[J].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