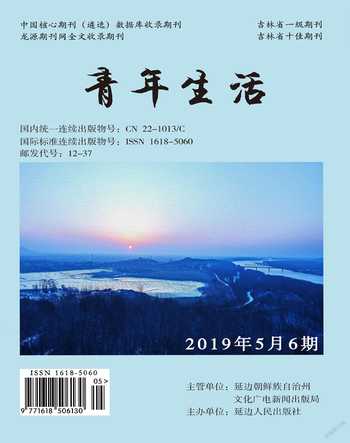淺析由《邊城》的田園牧歌到《長河》的暗流涌動
豆國慶 鐘嘉怡
摘 要:沈從文的兩篇代表作《邊城》與《長河》均講述了純凈和諧的湘西世界中湘西兒女的悲歡離合的生活常態,是相似相近的姊妹篇,但兩者又各所側重點:《邊城》以浪漫的筆調為讀者展現和諧穩定的湘西生活,《長河》以現實關照的態度表現美好寧靜日常中的暗流涌動。而這一轉變,也從側面反映出時代的風起云涌和作者本人精神歷程的演變。
關鍵詞:田園牧歌;暗流涌動;湘西世界;精神歷程
沈從文在《邊城》中的題記中曾道:“我并不即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里,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沖的農民……”從這段話里,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長河》就是那個“另外一個作品”,是《邊城》的后續,而且與《邊城》中的“原始淳樸的文化認知與生活方式”相比,《長河》更強調“平靜背后的喧囂與躁動”。
一、邊城牧歌中的浪漫哀婉
《邊城》中把湘西世界聚焦在茶峒這一地方,沈從文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描繪茶峒的秀麗風光:依山傍水的環境,清澈透明的小溪、白色的山塔,這些構成了一幅如畫的風景。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按照大自然的規律從事生產勞動,同秀麗風光一起成為了精巧的風景。春日里的沽酒桃花,夏日里的紫花布衣袴,秋冬時的黃墻黑瓦,均讓人神往傾心。由此可見,湘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自然溫馨般田園牧歌世界的物質
在這種未受或較少受到外界文明沖擊的自然與文化環境下,人們擁有著親密自然的人際關系,保持著較為原始色彩的價值觀念。正如沈從文所說,他只希望打造一個希臘小廟,而《邊城》是沈從文建筑“人性”神廟這一文學理想的最高成就。其中湘西世界中那古老淳樸而又生機勃勃的自然狀態下的人性依舊流光溢彩——端午、中秋的傳統習俗依舊繼續,男女整夜互唱情歌的故事仍然上演。為人天真活潑的翠翠,古道熱腸的祖父,慷慨熱心的順順,豪放豁達的天保與儺送,甚至是做事渾厚的妓女身上保留著湘西世界中的文化心理結構,一種超脫凡俗、自在自為的人性精神。
但當然,邊城牧歌式的生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邊城》中沈從文總能在有意無意間表現出湘西世界悄然間的變化。商人落腳的飯店,坐鎮不動的理發店,雜貨鋪,油行,花布莊,這些帶有現代商業文明標記的事物裝點著城外小小河街。王總團女兒因為經濟地位能夠在觀看劃船時占據最好的位置,一些人對以碾坊為嫁妝的驚嘆不已,這些也能夠體現出城市文化對湘西人們認知觀的侵襲。這似有若無的改變也正恰當地解釋了《邊城》中哀婉的情調。
二、智慧長河中的暗流涌動
在第一章《人與地》里,作者便以濃縮的筆墨介紹了呂家坪這地方三十年間人事的浮沉,讓讀者在極短的時間里便領悟到《長河》中那條表面風平浪靜的長河,實則早已是波濤洶涌。現代都市的文化價值理念似狂風般席卷了呂家坪這一條靜靜的長河,沖擊著人們千百年所認可的傳統文化思想。考入省師范學堂的兒子自以為受了新教育,便在家中趾高氣揚,使古老中國的父親天經地義的“權威”一下子喪失了,“一家大小必對之充滿敬畏之忱”。年輕的女學生回家之后,向父母談判,需要離婚,更有堅持“報獨身主義”的人物。女學生“新”的裝束、“新”的行為顛覆了傳統文化中人們對女人的認知,特立獨行的人生準則解構了女兒在家中勤勞溫柔的定義。
“新生活”一詞在書中出現了五十多次,呂家坪中的“變”也因這個詞而更加浮出水面。在《長河》的字里行間中處處涌動著一股神秘的力量,這力量沖刷著人們多年以來積淀的道德理念。小說中人物數量不多,故事情節也較為松散,但亦形成了“傳統”與“現代”雙方對壘的局面。保安隊長對夭夭的百般挑逗,人們在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對保安隊長的羨慕,三黑子對仗勢凌人小官的憎恨與厭惡,都說明呂家坪這地方在內部也逐漸出現裂痕,發生著細微的變化。
此外,《長河》中不僅僅反映呂家坪的風吹草動都和外界息息相關,同時也保留著作者對人性的贊美。夭夭身上依舊有著翠翠的天真無邪,卻更加機靈勇敢;老水手同祖父一般勤勞善良,卻洞悉世事;呂家坪依舊是重義輕利的人際關系,卻已出現仗勢欺人的現象。靜中有變是《長河》的跳動的節奏,此時的湘西就像小說中的那條長河,平靜中蘊藏力量,奔騰著流向不可知的遠方。
三、轉變之原因
沈從文創作《邊城》與《長河》的相差時間也只不過是短短幾年,但在其筆下的湘西世界卻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前者充滿詩意的理想王國到后者充滿變動的社會現實,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探討的。
沈從文放棄將湘西世界建構為自己的心靈家園,關注湘西社會現實,并借此來表現自己的未來湘西走向的憂慮,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便是當時的社會環境。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流亡途中,沈從文在沅陵大哥家住了幾個月,直至1938年春天到昆明。在這期間,他的住處恰當水路要沖,耳聞目見處在戰爭中湘西的種種變遷與社會政治問題,繼而明白“‘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自己的理想王國正逐漸崩塌,并業已成為同中國政治軍事局面的動蕩,同經濟緊密聯系的中國的一部分。
同時由于抗日戰爭所帶來的民族矛盾和本已存在的政治矛盾激起了沈從文作為知識分子的擔當和民族憂患意識。他開始理性關照湘西,意識到湘西農民的貧困與愚昧,為湘西的未來感到迷惘,故在《長河》題記中寫道,“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的內在肌理……”因此,《長河》相較《邊城》便顯得浪漫主義色彩已消退,現實主義成分突出,歷史感更為厚重,湘西亦變成了一個暗流涌動、危機四伏的現實世界。
《邊城》、《長河》這兩篇沈從文鄉土小說的代表作,它們共同展現了作者對干凈明澈、優美自然的湘西世界的歌頌以及對其前途的憂慮。從浪漫書寫到理性關照,從心靈家園到寫實再現,這不僅僅是理想與現實的碰撞,更展現出沈從文作為一個在城市生活的鄉下人對城市文明與鄉土文化此消彼長的態度及思考。
參考文獻:
[1]沈從文.長河[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
[2]吳偉.理想與現實的流轉——從《邊城》到《長河》看沈從文的“蛻變”[J].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5(4)
[3]胡曉波.守常中的變異——解讀沈從文的《邊城》與《長河》守常中的變異[J].新余高專學報,2006(6)
[4]張婷閆士委.從《邊城》到《長河》——比較閱讀中簡析沈從文思想的變化[J].文學評論,2011(6)
[5]孫雪梅.浪漫的消解與理想家園的凋敝——從《邊城》到《長河》[J].麗水學院學報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