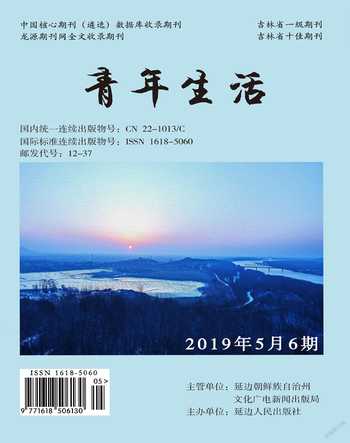從“逍遙游”看莊子的生存智慧
劉倩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大變革時期。而莊子正生活于這一時期。面對道德失范、政治失序的社會環境,莊子卻能看破功利,坦然面對福禍。莊子獨特的處世觀不僅對春秋戰國中人們的為人處世帶來很大影響,還一直延續至今,對中國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下面就《逍遙游》文末的三個故事,對莊子處世觀中的生存智慧進行詳細的分析。
一、功名之辯
第一個是許由讓賢的故事。古代著名賢君堯準備讓王位給許由。他甚至還不惜放低自己,抬高許由:“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堯在這里將自己比作“爝火”、河水,而將許由比作“日月”“時雨”要是一般人,此時一定會手足無措、欣喜若狂。然而,許由聽了這一番話后卻十分冷靜,還不以為然地說道“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對于天子給予的虛名,許由不屑一顧。“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只用一根樹枝,“鷦鷯”便可以安心在深林中中筑巢。只要一定的水量,就能夠使偃鼠填飽肚子。人也是一樣,不用過度地追求外物,也可以生活得很好。許由的不求虛名的態度即是一種人生智慧。
第二個故事敘述了肩吾與連叔的對話。主要講述了一位居住在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神人自然不同于一般凡人,他乘風駕龍,不吃人間的五谷雜糧,而是吸收天地日月之精華,遨游四方。顯然,神人擺脫了世間萬物的束縛,進入了無所待的逍遙境界。“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疵癘”亦作疵厲,指災害疫病。這一句話是講神人精神專注,能夠使世間萬物不生災害疾病,年年五谷豐登。可以看出,神人不依賴萬物的施予,而能夠幫助萬物的生長繁盛。這種不計較功利的處事態度正是神人的智慧。
二、有用無用之辯
第三個故事講述了莊子與惠子的辯論。惠子列舉了“大瓠”“大樗”兩個例子。在惠子看來,“瓠”因為太大,既不能盛水,又不能作瓢,只能無用而“掊之”。而“大樗”則臃腫盤結不合繩墨,枝蔓卷曲不中規矩。因其不材也只能被匠人拋棄。借這兩個例子,惠子闡述了“大而無用”的觀點。而莊子則進行了有力的反駁。他接下來講了“貍狌”和“斄牛”的故事,“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莊子在這里用生動的語言細致地刻畫了了“貍狌”費盡心機捕獵食物的過程。它“卑身而伏”,縮著身子等待獵物,上竄下跳,使盡渾身解數,“中于機辟,死于罔罟”最后卻死于獵人的機關之中。而體型龐大的“斄牛”雖然“不能執鼠”卻憑借看似笨重無用的身軀而逃脫危險,從而頤養天年。“小而有用”的死了,“大而無用”的反而活了下來。莊子在這里借“斄牛”闡述了無用保身的智慧。
就像大而無用的“斄牛”一樣,“大瓠”正因為無用,而逍遙自在“浮于江湖”,而無用的“大樗”則是“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無何有”,指虛無。“莫”,即漠,廣漠,“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仿徨”徜徉也,“逍遙”即自由自在。喻指一種怡然自得,逍遙自在的心境。這一句話表達了身處在虛無廣漠之野的大樗的逍遙的心境。“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因為物無所用,故不矢折于斧斤也。“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雖然無所可用,卻沒有困擾和痛苦。個體以對于社會的無用,換取了自我生命的保全。這正是險惡環境下,無用存身的人生智慧。
總的說來,莊子通過以上三則故事試圖告訴我們不求名,不貪功,無用存身的生活智慧,即身之游的內容。而要深入體會“身之游”的內涵和價值,則需要結合莊子生活的時代背景。
三、“無用存身”的智慧
莊子生活于戰國時期。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云:“春秋之后,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大變革時期。隨著周王朝勢利的進一步減退,各諸侯國為了富國強兵,爭王爭霸而紛紛招攬謀士。到了戰國中期,更是興起了一股養士之風,而當時的達官顯貴也都以善養士而聞名。
相應地,這一時期的士也具有極強的用世意識。所以,當時的大部分士人不是已經入仕,就是急切盼望著入仕。而已經身居廟堂之上的官宦子弟,則為了追求功名利祿,對待同輩不惜相互排擠傾軋,勾心斗角,對待上級則曲意逢迎,刻意巴結。余英時先生也說:“以孤獨而微不足道的個人面對著巨大而有組織的權勢,孟子所擔心的‘枉道以從勢’的情況是很容易發生的,而且事實上也常常發生。”為描述這一現象,莊子還特意創作了一則“舔痔得車”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曹商,通過自己對君主巴結謅媚,為其“舔痔”而得到了賞車百乘的厚祿。曹商為了功名富貴,而不惜為人“甜痔”。他的內心和人格已經完全被世俗的名利之心扭曲異化。
莊子的這則故事雖然夸張,然而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許多士人汲汲于追求富貴顯達的心態。在對功名利祿的你爭我奪之中,人們放棄了個人的人格和尊嚴,內心世也界變得狹隘、庸俗、卑瑣不堪。在此背景之下,莊子所提出的“不貪名”“不圖利”思想真可謂是實實在在的大智慧。因為唯有拋棄名與利的枷鎖,人們才能夠從黑暗污濁的世俗社會中真正解脫出來,不為物所累,實現人生自由的更高價值。
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之中,士人不僅人格和心靈會被扭曲,肉體生命也容易受到損害。伴君如伴虎。在莊子看來,哪怕士人自己做到了德性純厚,卻會因為一味地向君主高陳仁義之道,而被君主誤認為他是故意夸耀自己的品德,揭露他人的過錯,以至于被冷落甚至“必死于暴人之前矣”。而這樣的慘痛例子在歷史上屢屢出現:
《人間世篇》: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
《外物篇》: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事實上,“禮賢下士”僅僅是諸侯卿大夫為了利用謀士而編造的幌子。相對于有錢有勢的諸侯卿大夫,士人居于被動的被給予地位,士人僅僅只是人君爭王爭霸的工具而已。如果君主不再需要士人,或者不再信任士人時,士人就會遭遇冷落甚至性命危險。莊子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無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于是乎,他站在士人的立場上,給出了自己深刻而沉重的建議:當處于黑暗險惡的社會環境中時,個人應當把趨利避害、遠禍保身當做生活的主要目的,而不應該貪功求名,要隱才匿志,以一種于世無用的心態來保全肉體生命和人格精神的完整和自由。我們可以說“無用存身”的處世之道正是莊子基于嚴酷的社會現實,針對士人的避禍免害,韜光養晦而設計的。
無論是不貪功還是不求名,都是為了達到于世俗無所用,從而遠離災禍,實現自我生命的保全。所以,“不貪功”、“不求名”的思想實際上是隸屬于“無用存身”思想的,莊子處世觀中的生存智慧實際上就是“無用存身”的智慧。
參考文獻:
[1][戰國]莊周,《莊子》,方勇譯注[M],中華書局2010
[2]班固,《漢書》,顏師古注[M],中華書局1962
[3]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