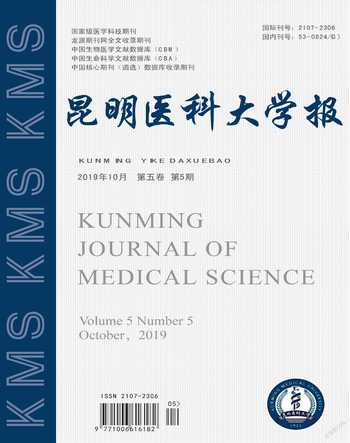葉天士治療血分證與血證特色初探
陳曉宇 盧晨 余金犇 鈕志鋮
摘要:目的:探求葉天士在血證與血分證上治療特色,指導臨床用藥。方法:從《臨證指南醫案》出發,有機結合臨床實際。結果:血分證是屬于溫病衛氣營血辨證中,溫邪侵犯人體達到血液的階段,血證是氣血津液體系中,血液及血液運行異常歸納匯總的一類疾病。結論:葉氏于血分證,見證便行涼血散血方,而于血證則循病因而立法、處方,兩者方藥雖有所重疊,立法卻截然不同。
關鍵詞:葉天士;血證;血分證
【中圖分類號】R-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107-2306(2019)05-181-02
葉天士,名桂,號香巖,祖籍安徽歙縣,行醫于江蘇。其父,曾祖父均為當地名醫,葉氏幼時勤奮好學,尚修進士科,其父去世后專心習醫,后行醫活人無數,醫德高尚,終成一代臨床大家。后世弟子整理編輯其學術思想、臨床案例著有《溫熱論》、《幼科要略》、《臨證指南醫案》[1]等作。葉天士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原是用于溫病階段的劃分,但葉天士所指血分證的范圍遠超出溫病范疇。血證是各種原因引起火熱熏灼或氣虛不攝,致使血液不循常道而出的一類出血性疾病,在葉氏留有眾多治療吐血,衄血醫案,其治療思想與血分證大相徑庭。因此筆者通過對比葉氏血分證和血證臨證中的遣方用藥及治療思想,歸納總結出葉氏治療血分與血證的特色,現總結如下:
一、血分證與血證的范圍
血分證以出血、紫斑、高熱等為主要臨床表現,出血是血分證的最常見的臨床表現,熱盛動血會出現血上逆之吐血、衄血或血下泄之便血、尿血;血熱互相搏結,則會出現瘀斑,瘀血內阻。葉天士遵《黃帝內經》《傷寒論》之旨,并結合自身臨床實踐,在后世醫家關于血及血分的論述啟發下,依據溫邪襲表,由淺入深的過程,將其分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2]。血分證為溫病重癥,溫熱病邪已深陷血分,而致傷陰或出血的特殊階段。
“血證”一詞首見于明·虞摶所撰的《醫學正傳》,該書引《黃帝內經》“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以及“怒則氣逆,甚則吐血”等諸多以出血為主要癥狀的條文論述血證概念。現代《中醫內科學》教材則以此為基礎,運用氣血津液辨證將臨床出血病證歸為血證[3],將其定義為各種原因引起的,血液不循常道,或上溢于口鼻諸竅,或下泄于前后二陰,或滲出于肌膚所形成的一類出血性疾患,出血也是血證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二、血分證與血證的異同
“血分證”是葉天士所創溫病衛氣營血辨證中溫邪內侵的一個階段,與衛,氣,營共同作為劃分,溫病發展的尺度,四者常見兼證,各有特點卻不完全獨立。葉氏將溫邪侵襲人體,而出現高熱,出血,斑疹之時的病理階段稱為血分證,它以血液運行異常為主要表現,兼有外感溫病癥狀,但以血行異常最為危重。而血證是氣血津液體系中一大類血液運行疾病,所屬范圍與血分證大相徑庭,且血證雖有出血,但是間雜其他癥狀亦為危重,如脾虛血脫中,氣虛納差同屬主癥。
高熱譫語為血分證的主要臨床表現,盡管溫病后期的血分證與熱盛迫血型血證均會出現熱盛和出血等癥狀,以及發斑等類似的臨床表現。但血分證發病急驟,屬溫病危重時期,血分證的出血為多臟腑、多竅道的急性出血,可見鼻衄、齒衄、便血、尿血等癥狀,且常伴有高熱煩躁、頭痛如劈、昏狂譫語、有時抽搐的臨床表現,其傳變迅速、病情險惡。而熱盛迫血型血證常有反復發作的慢性病史,出血量少于血分證出血,一般無舌質紅絳等熱盛傷津的表現,也無溫病傳變迅速這一特點,更沒有閉竅、動風等兼證。從臨床表現來看,盡管二者均有出血癥狀,但血的臨床表現,而血證并無高熱癥狀,雖然血虛、血瘀會出現發熱,但其嚴重程度遠不及血分證之高熱。綜上所述,血分證屬于溫病范疇,而血證屬內科范疇,二者說理工具不同[4]。
血分證中熱入營血重要的標志之一為紫斑,而血證中也有紫斑病癥,所用方藥同為犀角地黃湯。對于斑疹,葉天士的辨證多從溫病著手分析,考慮溫邪入血分,迫血外出,留表生斑。同內科血證中,火熱之邪迫血妄行,外溢成斑[5]。二者分析雖然不同,但是皆是有熱入血之證,故選涼血清熱之藥,在紫斑一病上血分證與血證殊途同歸,更說明兩者各為獨立體系的,但有相互交叉的部分。
三、自成一體,血分從血治
血分是用于區分溫病的階段,有別于衛氣營分,血分證為溫病衛氣營血傳變過程中最危重的階段,葉天士認為,“入血”是辨治血分證的關鍵,《溫熱論》載:“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臨證指南醫案·卷五·癍痧疹瘰》中有“濕溫雜受,身發斑疹……又,舌邊赤,昏聵,早輕夜重,斑疹隱約,是溫濕已入血絡。”此濕溫久作,深入血分,故“議清疏血分輕劑以透疹……”葉天士用犀角、金汁此類大寒之藥,直降血分之熱勢,涼血以除溫邪[6]。同理,又有《臨證指南醫案·吐血》葉天士治一失血病人:“失血,口碎舌泡。乃情懷郁勃,內因營衛不和,寒熱再熾,病郁延久為勞,所喜經水尚至。議手厥陰血分主治。”藥用犀角、金銀花、鮮生地、玄參、連翹心、郁金。葉天士從血分辨治,患者因情志郁而化火,熱入血分,以犀角地黃湯加減,銀花、連翹清氣分郁熱,犀角、生地、玄參清血分熾熱,郁金活血化瘀解郁。《未刻本葉氏醫案》載一“鼻衄”醫案:“頭脹,鼻衄,犀角地黃湯加白茅花、側柏葉。”此案雖與前案用藥略有不同,但治法與前述溫邪入血分案相同,亦是清熱涼血散瘀法[7]。總而言之,葉天士在治療上謹守“諸熱瞀瘛,皆屬于火”之病機,以犀角地黃湯為基本方加減,其對血分證和血證的治療思路可見一斑。
四、從因而治,血證不治血
血證是指各種原因引起的血液運行異常,葉氏治療血證多從“多種原因”下手,對因治療。如心脾兩虛虛導致的血行無力,脾不攝血。如《臨證指南醫案·便血》載:“上年夏季,絡傷下血,是操持損營。治在心脾。”藥方為歸脾飴糖丸,該案中患者因前一年夏季勞傷心血,心在時合夏,故而心營不足而致營血虧虛。葉天士對于出血,并不急于使用治血之藥而是從病因治療,用歸脾丸加飴糖,在歸脾丸益氣健脾、養血安神的基礎上加飴糖一味藥,助脾生血,助心行血,營養周身以治療血不循脈之證。又有《臨證指南醫案·肝火》中多處可見因肝氣不疏而導致的肝木克土、肝胃不合而致腸紅的病案,葉氏亦多從疏肝理脾、調和肝胃立法,如診治一患者:“郁怒,腸紅復來,木火乘腑絡,腹中微痛,議與和陰。冬桑葉、丹皮、生白芍、黑山梔、廣皮、干荷葉邊、生谷芽”。此案中患者因肝氣不疏致肝木犯脾,“郁怒,腸紅復來”,提示為近血,法當養陰清熱、健脾理氣。以牡丹皮、梔子清肝熱,桑葉、白芍養肝陰,陳皮、荷葉疏肝理脾,而加一味生谷芽,足以體現葉氏用藥獨到之處,不僅疏理肝氣,亦可健脾開胃,而不是針對血證用藥。
五、小結
總而言之,血分證是各種原因導致的“溫邪”侵入血分,出現斑疹,出血等癥狀的疾病,而血證則是多種原因引起的血液運行異常。二者治療用藥上有重合之處,而論治療思想則大相徑庭。血分證是溫邪進入血分而從血分輪治,血證則針對血液運行失常的病因施治,兩者雖有交叉,但始終屬于不同體系。葉氏對于血分證和血證分別治療,使用不同思路,遣方用藥各成體系,為臨床診治提供更清晰的思路,分門別類,治療才能效如桴鼓。
參考文獻
[1]清·葉天士《明清名醫全書大成--葉天士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9.
[2]屠燕捷,方肇勤,楊愛東,郭永潔.葉天士衛氣營血辨證標準與理法方藥[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6,31(03):788-793.
[3]王蜀嘉.以唐容川《血證論》為基礎探討中醫血證的診斷學特色[D].北京中醫藥大學,2016.
[4]張佳樂,洪靖,牛淑平.血分證與血證異同辨析[J].安徽中醫藥大學學報,2017,36(04):3-4.
[5]蔣文明,陳大舜.葉天士涼血散血法治療內傷血證的基本方劑結構[J].中醫雜志,2000(03):187-188.
[6]翁逸群,張翔,錢俊華.葉天士醫案治血特色探析[J].浙江中西醫結合雜志,2017,27(05):430-432.
[7]錢月慧.《未刻本葉氏醫案》血證治療特色及用藥規律探尋[J].遼寧中醫雜志,2013,40(01):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