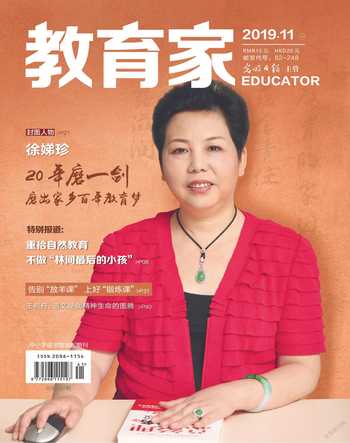當教育遠離自然,孩子缺失了什么
王夢茜


“她當時剛學完一篇有關燕子的課文,跑來問我哪里能找到燕子,她說她太想看一看燕子是什么樣的。”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創始人王愉回憶起女兒“找燕子”的故事時說,“后來我開車帶她去郊外,在車上她終于看到了燕子飛過的身影。”兒時常見的動物,十多年后卻需要特地到郊外才能看到,王愉感受到,當下兒童親近自然的空間與渠道似乎越來越窄。
“他們更喜歡在屋里玩,因為屋里有電源插座”
“他們不知道什么是螢火蟲,分不清樹的種類,認不得蟲,沒碰過草地,也沒有看過銀河系。那他們的童年在忙什么呢?忙做功課、忙擠校車、忙補習,僅有的一點空閑,看看電視和漫畫書也就不夠用了。”作家三毛稱這些孩子為“塑料兒童”。
我們身邊也存在這樣的孩子:除去在學校的時間,他們大多數時候都宅在家里,和電子游戲或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為伴,他們對外界的自然不具備應有的好奇心,對身邊的自然事物缺乏最基本的興趣。他們知道課外書上亞馬遜雨林里的稀有物種,卻不知道家里餐桌上的蔬菜名稱,他們看過電視電影里的麥田、菜園,卻沒有親身體驗過下田、撫摸過一株禾苗……他們更喜歡在屋里玩,因為那是有電源插座的地方。這些現象,被美國記者兼兒童權益倡導者理查德·洛夫稱為“自然缺失癥”。
“生活在高度重復的城市環境中,人的感知能力越來越弱,由此會引發很多問題,比如感覺綜合失調。打個比方,有個杯子在你面前,你去拿它,卻沒拿住,是因為你對它的位置判斷不正確,你的視覺和觸覺無法協調起來。”植物私塾創始人張新宇表示在自然教育的實踐中,他接觸過許多感覺綜合失調的孩子。
2019年10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全球首份《世界視力報告》顯示,中國城市青少年近視發病率高達67%,他們推測這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變、城市化和學校教育系統等原因造成的。
鄉村也并非“自然缺失癥”的空心地帶。2019年8月20日,中國兒童中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中國兒童發展報告(2019)——兒童校外生活狀況》。報告顯示,周末,鄉鎮農村兒童的電子產品的使用時間(108.18分鐘)明顯高于城市兒童(88.40分鐘)。
“除了近視,農村‘小胖墩’也越來越多。”“U然”自然教育聯合創始人郭海巖告訴記者,據成都市疾控中心調查數據顯示,近年來,成都農村地區兒童肥胖率不斷上升,其中,在部分年齡段甚至超過了城市兒童肥胖率。2015年,在8歲兒童年齡段,城市女生肥胖率為8%,而農村女生肥胖率則為9.7%。
“自然缺失癥”并不是一個醫學術語,它概括了一種社會趨勢,讓人們得以從這個視角去思考自然對于兒童成長的影響。理查德·洛夫指出,兒童與自然的疏離會導致身心健康的多重損害,造成感官逐漸退化、肥胖率增加、注意力紊亂和抑郁等病態,間接地損害兒童的道德、審美和智力成長。同時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直接接觸自然對于注意力缺失、多動癥、兒童抑郁癥、壓力管理都有治療的功能,對認知能力也有改善。
蓋婭自然學校校長張赫赫在活動中曾遇到一些孩子,他們往往有控制情緒的困難,容易發怒。但隨著到大自然中,與伙伴們一起進行一些活動,他們的情緒往往會逐漸平穩,與他人相處也會變得容易起來。“在家庭或學校環境中,由于長期被單一尺度度量,一些孩子可能會處在焦慮、恐懼等不適情緒中,因此別人無心的一句話就會把他們的情緒點燃,甚至會以暴力的方式來對待別人。而大自然里的活動,往往不設定唯一的評判標準,大家更容易放下彼此,接納包容。”
恐懼、對抗與不知所措
“孩子對于自然的喜愛是天性,全都烙刻在基因里,但前提是你要給他一個機會,讓他接觸到自然。”臺灣大學植物學博士、林奈實驗室創始人劉芝龍說。
2012年,廈門學生張欣窈研究的課題《“自然缺失癥”現象調查與對策研究》,獲得第27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其中有一個問題——“有一項關于‘我們身邊的生物’的調查,你到哪里完成這項作業?”對此,88%的同學回答“上網找”。他們對自然的了解大多數來源于網絡、電視等信息媒介。
當孩子與自然的空間距離增大時,心理上的距離隨之拉開,他們對于自然的態度、認知也可能產生偏差。久而久之,自然逐漸成為一個抽象的概念。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和科技委員會聯合舉辦的“云南植物考察學生科普夏令營”,每年都會送50余名澳門中學生來云南參觀。曾為該夏令營活動做講解的海螺發現,面對園內多樣有趣的植物種類,這些中學生興致很低,“參觀期間他們一直在聊天、抱怨,要求休息和早點離開。注意力難以集中、對周圍變化顯得漠然是這些學生留給我們的整體印象”。
“當孩子們重新回到大自然系統中,大多數人還是有好奇心的,但是他們往往不知所措,并不知道該怎么跟自然打交道。”張赫赫以電影《阿凡達》打了個比方——當雙腿癱瘓的前海軍陸戰隊員,進入阿凡達的軀殼中,他走路跌跌撞撞,十分莽撞,“這些重新回到自然中的孩子,就跟那個角色一樣,顯得笨手笨腳,不知道如何與自然相處”。
“他們覺得泥土是臟的,看到任何昆蟲都會害怕,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蟲子會不會咬我’……”在桃花源生態保護基金會自然教育總監王西敏看來,現在的孩子,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對大自然的恐懼十分明顯。一次夏令營活動,他帶孩子們穿越一片樹林,在一個池塘邊看見一條鐵線蟲,孩子們并不認識這種蟲子卻紛紛表示要打死它。“那天晚上我們在反思這個問題,為什么孩子想把它打死,可能是害怕不認識的動物傷害他們,也可能是覺得這個動物比我弱小,或者就是單純的不喜歡,這種看待自然的心態是應該去改變的。”
“他們和自然的距離越來越遠,到后面可能已經沒有辦法去適應和親近自然了。”王愉認為,從表象來看,孩子與自然的不親近表現為,孩子在自然中會沒有安全感、很難放松、不知道如何觀察、不知道怎么去玩。她曾目睹一個孩子看見蜻蜓時的場景——哇哇大叫,十分驚恐,“我當時很驚訝,因為不管是飛行的姿態還是身體的結構,蜻蜓都屬于自然中特別美的一種昆蟲,很難讓人產生恐懼感”。
當“自然缺失癥”兒童長大之后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師劉悅來,在景觀設計專業的教學中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景觀設計是一門與自然關系非常密切的學科,但學生們對自然卻并不敏感。“認識自然是景觀設計的基礎。做設計時,我們首先要分辨哪些東西是能夠設計的,哪些東西是不能設計的,如果連這些都不了解的話,你的作品反而會讓更多的人成為受害者。現在有很多園林景觀,把一些本來很自然、質樸的地方,變成很‘奢侈’的設計,最后產出一個個‘綠色荒漠’。”
“我接觸過許多生態學方向的研究生,有些人采集動植物標本時一點都不手軟,見到植物就采,見到蝴蝶就抓,采集的標本也許對他們的科研并沒有多大作用。”王西敏口中的這些年輕人雖然具備自然科學知識,學習工作也與自然息息相關,但他們對自然缺乏情感、對生命缺少尊重。
理查德·洛夫指出,兒童需要對大地擁有強烈的依戀,這不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健康,更是為了讓他們成年后擁有保護自然的責任感。而童年缺乏自然經歷的人,對環境往往會更加冷漠,很難培養出良好的環境態度和行為。
提到“自然缺失癥”的后果,王西敏從環保主義者的角度對此表示擔憂:“如果我們從小沒有在孩子們心目中種下對于大自然的情感,那么以后希望他們關注自然、保護自然,難度就很大。”自然保護不能只依賴于自然保護機構,更取決于年輕人和自然的關系,取決于他們是否熱愛自然、怎樣熱愛自然。
在上海從事環保工作的過程中,王西敏常與當地年輕人交流,發現相當多的人持一種觀點——“上海是人生活的地方,不應該讓野生動物生存”。在他看來,這與從小缺乏與自然接觸密不可分,他們不認為人與大自然可以和諧共處。“如果年輕人心中都是這樣的想法,那未來的自然保護將會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