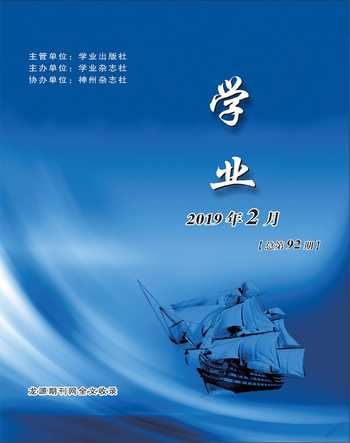試論作為“物”的藝術(shù)作品和物性
馮浩源
摘要:藝術(shù)作品作為我們生活中的審美對象,學(xué)界對此討論不斷,而藝術(shù)作品其載體“物”的屬性,對藝術(shù)作品的物的屬性的辨析,是正確認(rèn)識和藝術(shù)審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從藝術(shù)作品質(zhì)料、媒介、體現(xiàn)形式等方面對藝術(shù)作品的物性進(jìn)行了討論。
關(guān)鍵詞:物性;藝術(shù)作品;質(zhì)料;媒介
藝術(shù)作品是一個物質(zhì)實(shí)體。誰能懷疑藝術(shù)作品就是一“物”?這一承認(rèn)就意味著,一切藝術(shù)作品首先以其物質(zhì)屬性成為我們所關(guān)注的對象,質(zhì)料才是藝術(shù)作品的“基質(zhì)”。這就是說,石頭之于雕塑,畫布與顏料之于繪畫,語言之于文學(xué),顯然,前者是后者的基礎(chǔ),而后者僅僅作為前者的規(guī)定性而存在。
在其肯定性中,質(zhì)料的屬性作為藝術(shù)作品的規(guī)定性,或者說作為對藝術(shù)作品的規(guī)定性的承載而出現(xiàn),它是對藝術(shù)作品的規(guī)定性的規(guī)定,對一件雕塑或者繪畫作品的規(guī)定與要求,首先要看這些作品是以什么質(zhì)料為基質(zhì)的。藝術(shù)作品的質(zhì)料決定著它的形式。這里所說的決定包含著兩層含義:一層是對質(zhì)料的克服程度;一層是對質(zhì)料的服從程度。
首先來說對于質(zhì)料的服從。服從就意味著質(zhì)料的性質(zhì)決定著作品的形式。我們把云崗石窟的石雕與榆林窟的泥塑作一個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單單是質(zhì)料問題,而是由于它們所使用的質(zhì)料的不同所引起的審美特質(zhì)的不同。石窟的高大靜穆與泥塑的小巧生動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審美風(fēng)格上的差異,就是泥土與石頭之間的差異。石頭的硬度、延展性、質(zhì)量決定著雕塑的力學(xué)結(jié)構(gòu)與形式),決定著石質(zhì)雕塑的有機(jī)結(jié)構(gòu)。石頭的硬度與細(xì)密程度決定著雕塑的細(xì)節(jié)刻畫程度。而泥的可塑性和硬度決定了泥塑必須有所依托,它的可塑性決定了它比石像有更大的形式選擇范圍,一尊泥塑臥佛塑多大取決于塑像者的投入和喜好,而石雕除了兩者之外,還要取決于有多少和多大的石頭。
這就意味著。我們對藝術(shù)作品進(jìn)行審美的時候,必須關(guān)注它的質(zhì)料。比如我們對刺繡的欣賞,除了作品的繪畫性質(zhì)以外,還必須認(rèn)識到它是用針與線完成的繪畫,在這種審美之中,包含者著費(fèi)吸,沒有這種贊嘆,對它的審美就是表面的。那么就作品的質(zhì)料對其規(guī)定而言,這種規(guī)定作為一種潛規(guī)則而存在,是游戲與游戲規(guī)則之間的關(guān)系,服從并且在服從中達(dá)到自由,這是藝術(shù)作品的內(nèi)在沖突,是質(zhì)料與形式之間的么沖突。這種沖突,是藝術(shù)美的根基,也是藝術(shù)門類之間的界限,是這個界限,就是質(zhì)料對形式的規(guī)定。有規(guī)則,才有自由,藝術(shù)創(chuàng)造術(shù)的秘密就在于它總是能夠在對規(guī)則的服從中達(dá)到自由,在這種自作由中質(zhì)料對形式的規(guī)定反而被忘卻,魚水相忘則“藝”成。
在這個意義上藝術(shù)作品與其質(zhì)料之間的規(guī)定與否定是證統(tǒng)一的,并且只有在達(dá)到這種統(tǒng)一之后,藝術(shù)美才被顯現(xiàn)出來。在這個同題上,克羅齊犯了錯誤,他荒謬地認(rèn)為藝術(shù)乃是人的心靈活動的表現(xiàn),它在人們內(nèi)心就完成了,并不需要外在媒介的傳達(dá)。用他的話來說,“審美的事實(shí)在對諸印象作表現(xiàn)的加工之中就已完成了。我們在心中作成了文章,明確地構(gòu)思了一個形狀或雕像,或是找到一個樂曲的時候,表現(xiàn)品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而且完成了,此外并不需要什么”。在他看來,所謂文字、聲音、顏色、線條等物質(zhì)因素只是“備忘的工具”或“幫助藝術(shù)再造的工具”而已,因?yàn)樾撵`的活動如果不用備忘的工具將其保存起來,就會被遺忘掉,因此這些備忘的工具只是幫助藝術(shù)家回想起自己的審美經(jīng)驗(yàn),以及供讀者以后可以反復(fù)欣賞作品的物理刺激物而已。無論克羅齊提出這種觀點(diǎn)是為了強(qiáng)調(diào)什么,顯然它忘記了藝術(shù)作品首先是一“物”,而這一物的“物性”沒有被他納人藝術(shù)作品的作品性中。
質(zhì)料決定藝術(shù)作品的形式,這僅僅是質(zhì)料與形式之間的否定性關(guān)系的表現(xiàn),在兩者間還存在一種肯定性的關(guān)系。這種肯定表現(xiàn)在,質(zhì)料的形式就是作品的形式,作品的形式不構(gòu)成對質(zhì)料的否定而是凸顯出質(zhì)料自身的形式。這在一些民間藝術(shù)與原始藝術(shù)中有充分的表現(xiàn),,比如英國著名的雕塑家利·摩爾的口號一“忠于材料”。他認(rèn)為每一種材料都有自身的特性,只有當(dāng)?shù)袼芗抑苯舆M(jìn)行創(chuàng)作,只有在他與他的材料之間形成一種主動的關(guān)系時,這種材料才能在形成某種觀念的過程中發(fā)生作用。這就帶來了是一個矛盾:石塊本身是堅(jiān)硬的,那么使用石塊做雕塑應(yīng)不應(yīng)該制造術(shù)像肌膚那樣柔軟的感覺?還是保持它那堅(jiān)實(shí)的石頭本性?質(zhì)料對形式的規(guī)定本身就是由肯定與否定兩個的方面構(gòu)成的,對于雕塑來說,既要尊重石頭的堅(jiān)硬,又要克服它,藝本術(shù)決不是征服,更不是服從,它就存在于兩者間的小天地中。
由于藝術(shù)作品的物質(zhì)屬性,我們說藝術(shù)作品作為一個物質(zhì)實(shí)體而存在,這個判斷沒有錯。如果我們把文學(xué)作品與音樂這些在存在論上具有兩重性的藝術(shù)作品也考慮進(jìn)去,只要承認(rèn)文學(xué)是語言的質(zhì)量問題和音樂是聲音的質(zhì)量問題,那么這個判斷就是有效的。這揭示了藝術(shù)作品的本體論性質(zhì),藝術(shù)作品所包含的感性因素在藝術(shù)作品中具有一種規(guī)定性的意義,這是藝術(shù)作品與其他非藝術(shù)作品的器具之間的區(qū)別之一。社夫海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通過藝術(shù),感性不再是自身可有可無的符號,而是一個目的。它成為對象本身或者至少同它表示的對象是分不開的。”質(zhì)料乃是構(gòu)成藝術(shù)作品的基礎(chǔ),甚至就是藝術(shù)作品自身的一部分。正如杜夫海納所說的:“音樂的材料是聲音,不是作為發(fā)聲手段的樂器;同樣,詩歌的材料是詞語這種特殊的聲音,而不是講出這些詞語的喉嚨或戲院中用全身講出這些詞語的演員。"這是事實(shí),也是認(rèn)識藝術(shù)的正確途徑。杜夫海納強(qiáng)調(diào),物質(zhì)手段在構(gòu)成藝術(shù)作品的過程中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得到了充分的顯現(xiàn):“物質(zhì)手段是通過顯示自己而不是使自己消失,即通過展開自己的全部豐富感性,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審美化的。”承認(rèn)藝術(shù)作品首先是一物,這不是在強(qiáng)調(diào)一個事實(shí),而是思考這一事實(shí)和藝術(shù)作品作為審美的事實(shí)之間的關(guān)系。這個事實(shí)應(yīng)當(dāng)被尊重,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關(guān)系是如何發(fā)生的。
藝術(shù)家對物質(zhì)材料的選擇直接關(guān)系到作品的審美特征。比如維納斯的雕像,如果不用大理石而用鋼鐵來完成、那么用石頭表現(xiàn)出的肌肉的質(zhì)感將被鋼鐵的冰冷與不可塑性所取代,從而成為另種關(guān)于維納斯或者別的什么觀念的隱喻,這將會成為另一件藝本作品。中國傳統(tǒng)的潑墨山水,如果不是用宣紙而用別的紙張、就不可能造成那種暢淋滴的藝術(shù)效果,即使同是使用宣紙,還有生宣熟宣之分。清代畫論家戴熙指出:“古人書畫多用熟紙。今人以用生紙為能,失合古意矣。”
質(zhì)料本身的性質(zhì)參與著藝術(shù)作品的美感的生成,誠如桑塔耶納所說:“感性的美不是效果的最大或最主要的因素,但卻是最原始最基本而且最普遍的因素。沒有一種形式效果是材料效果所不能加強(qiáng)的,況且材料效果是形式效果之基礎(chǔ),它把形式效果的力量提得更高了,給予事物的美以某種強(qiáng)烈性、徹底性、無限性,否則它就缺乏這些效果。假如雅典娜的神殿巴特農(nóng)不是大理石筑成,王冠不是黃金制造,星星沒有火光,它們將是平淡無力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首先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是一“物”,因?yàn)椤拔铩钡奈镄詮?qiáng)有力地決定著藝術(shù)作品的存在狀態(tài),也強(qiáng)有力地決定著藝術(shù)么作品的存在。但是,人們往往輕易放過了藝術(shù)作品是一“物”這一簡術(shù)單事實(shí),或者,人們在考慮藝術(shù)作品的形式特征時注意到了質(zhì)料對作形式的影響,而沒有深入到以質(zhì)料對形式的規(guī)定與對內(nèi)容的規(guī)定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特別是,藝術(shù)所使用的質(zhì)料作為人類實(shí)踐的結(jié)果與實(shí)踐的對象,本身處在一個歷史性的流變之中,我們有按勞動工體具,特別是勞動工具所使用的質(zhì)料作為人類文明狀態(tài)與社會發(fā)展?fàn)顟B(tài)分期的標(biāo)志,可是為什么卻沒有以藝術(shù)作品的質(zhì)料作為藝術(shù)作品之存在與本質(zhì)的分類標(biāo)志呢?
這需要媒介理論的成熟并且進(jìn)入美學(xué)之中。藝術(shù)的質(zhì)料與藝術(shù)的媒介是同一層面上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文學(xué)領(lǐng)域中最能體現(xiàn)出藝術(shù)作品作為一“物”的性質(zhì)對藝術(shù)本身的意義與影響。必須提一下現(xiàn)代傳媒學(xué)的奠基人麥克盧漢的研究,他向我們表明了,藝術(shù)的質(zhì)料與藝術(shù)的媒介對于藝術(shù)而言,本身具有時代規(guī)定性。
要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就不得不追間一下什么是媒介它對于文化意味著什么?首先切人這個問題的思想先驅(qū)是加拿大天オ的思想家一一麥克盧漢。他研究最為基礎(chǔ)的問題:感性生活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我們的感知能力、認(rèn)知模式的影響。這是麥克盧漢思想的根本出發(fā)點(diǎn),他的核心概念一一“媒介”,正是從感性生活的角度提出的。麥克盧漢認(rèn)為媒介就是人的延伸,而他所謂的“延伸”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對象化”,他所謂的媒介實(shí)際上就是“本質(zhì)力量”的“物化”,麥克盧漢將一切機(jī)械媒介視為人體個別器官的延伸,將電子媒介視為人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伸延。麥克盧漢的這一思想在上個世紀(jì)是令人欣慰和振奮的,因?yàn)樗坪醪⒉淮蛩銓@種“延伸”作出否定性的評判,他并沒有把這種延伸和“異化”聯(lián)系在一起,相反,他把這種延伸視做一種積極的力量,從而把延伸的結(jié)果一媒介視為推動人類和社會進(jìn)步的力量,視為“使事物所以然的動因”。在麥克盧漢看來,“媒介”作為一種認(rèn)知能力塑造了一切文化現(xiàn)象因?yàn)椤凹夹g(shù)使人的一種感官延伸時,隨著新技術(shù)的內(nèi)化,文化的新型轉(zhuǎn)換也就迅速發(fā)生”。在此,文化和媒介之間就畫上了等號因而麥克盧漢得出結(jié)論:“媒介就是人的感性生活的總和。”
麥克盧漢對“媒介”的這個定義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如果麥克盧漢是對的,那就是說,在我們的文化與文學(xué)和我們的社會生活之間,有“媒介”這樣一個中介環(huán)節(jié),我們的文化與文藝活動是通過媒介這一感性活動的總和實(shí)現(xiàn)的。麥克盧漢認(rèn)為他為人類社會的進(jìn)步找到了一種真正本源性的力量,他盡其所能地大聲頌揚(yáng)“媒介是社會的先鋒”,“新媒介對我們感知生活的影響和新詩的差不多。它們不是改變我們的思維而是改變我們世界的結(jié)構(gòu)”。
以麥克盧漢的思考為出發(fā)點(diǎn)、我們對文學(xué)這門藝術(shù)與媒介之間的關(guān)系作一個歷史的回顧。
文學(xué)的最初樣態(tài)是民歌,而民歌是口耳相傳的,它不需要也沒什有什么物質(zhì)媒介,文學(xué)在這個階段是完全民間的,是人民性的,文么學(xué)的任務(wù)也是單純的,勞者歌其事,饑者歌其食,文學(xué)是人民的情是感與要求的最直接流露。
文學(xué)的第二種樣態(tài)是由官方收集并改編過的民歌,以及一些冒品作方文件,這時文學(xué)的媒介是竹簡和帛,還有青銅器。這一時期的文的學(xué)依賴于物質(zhì)媒介,載體的物質(zhì)有限性會造成文本審美特性的傾向本性。所謂載體的物質(zhì)有限性,是指作為載體的物質(zhì)因其固有的特性體而對它所承載的信息的束縛。這些具體物質(zhì)材料作為一種有限存在所受到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以及這種限制對文學(xué)傳播和創(chuàng)作的影響;這些物質(zhì)材料對閱讀方式的束縛;這些物質(zhì)材料所能承載的信息量的局限對文學(xué)傳承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式的可能性的束縛。
文學(xué)的第三種樣是由專業(yè)人員創(chuàng)作的詩、文和史傳,紙成為文學(xué)的主要媒介。這一時期最顯著的特點(diǎn)是專業(yè)的文學(xué)創(chuàng)造者也就是所謂的文學(xué)家的出現(xiàn)。從漢代的辭家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xiàn)了一批專業(yè)的創(chuàng)作群體,他們借鑒并且改造民歌的形式,把民歌藝術(shù)化、精致化從而使文學(xué)獲得了獨(dú)立的地位、也造成了一種為立,一種有媒介的以官方的審美情趣為主導(dǎo)的文學(xué)與無物質(zhì)媒介的以民間審美情趣為主導(dǎo)的文學(xué)的對立。就這種對立的物質(zhì)形態(tài)而言,我們可以稱其為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之間的對立。
文學(xué)的第四種樣態(tài)的主體是小說,特別是白話長篇小說。小說發(fā)展和普及的前提是紙的普及和印刷術(shù)的發(fā)展。紙作為一種市民社會的日常用品,決定了小說必然以市民社會的審美情趣為主導(dǎo)。在文學(xué)樣態(tài)的變遷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文學(xué)自身的發(fā)展和它的物質(zhì)媒介之間存在著一種內(nèi)在聯(lián)系,簡單地說,在竹簡為主的時代不可能出現(xiàn)小說,文學(xué)的物質(zhì)媒介制約著文學(xué)自身的發(fā)展,而物質(zhì)媒介本身的性質(zhì)及其階級屬性,也就是這種物質(zhì)媒介主要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決定著文學(xué)的時代性的審美追求。
這種現(xiàn)象對于藝術(shù)作品的存在來說,是具有普適性的,藝術(shù)總是作為一物的藝術(shù)作品而存在,物的所有權(quán)決定著藝術(shù)作品的所有權(quán),在物的所有權(quán)和建立在這一物基礎(chǔ)上的藝術(shù)作品的審美特性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lián)系,這是與藝術(shù)生產(chǎn)相關(guān)的問題,對此我們在討論藝術(shù)作品作為產(chǎn)品的性質(zhì)時再加以討論。
藝術(shù)作品與物質(zhì)媒介之間的關(guān)系無疑說明,藝術(shù)作品作為物面存在,使得“物”的實(shí)踐性質(zhì),也就是在人類實(shí)踐活動中我們所能使用的物質(zhì)所包含的“實(shí)踐性”成為藝術(shù)作品的本有之性,因?yàn)槿祟愂褂檬裁礃拥奈镔|(zhì)材料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造,這是一個實(shí)踐問題,面物質(zhì)材料之被使用的程度和被加工的程度,這也是一個實(shí)踐問題。藝術(shù)作品本質(zhì)上的”物性”、要求我們在面對整個藝術(shù)生產(chǎn)活動時,關(guān)注它的原材料,關(guān)注對原材料進(jìn)行加工與應(yīng)用的手段,關(guān)注對材料自身的認(rèn)識,關(guān)注這一“材料”的歷史變化。
在這里我們所強(qiáng)調(diào)的是,藝術(shù)首先是作為感性契機(jī)而存在的,藝術(shù)不是一團(tuán)精神,它就在那里,它占有空間,它呈現(xiàn)形式,它占有時間,它是一物,認(rèn)識與欣賞藝術(shù)的過程,就是與這一“物”打交道么的過程。藝術(shù)作品是一個事實(shí),是一件實(shí)體,藝術(shù)作品是以現(xiàn)實(shí)的是藝與具體的感性契機(jī)為基礎(chǔ)的。我們使用了“契機(jī)”這一詞,我們想術(shù)用這一詞掩蓋的問題是,由于“物性”在藝術(shù)作品中的這種基礎(chǔ)性作作用,我們是不是可以判斷說它就是藝術(shù)作品的“實(shí)體”?說藝術(shù)的作品是一物這沒錯,但說藝術(shù)作品的實(shí)體是這一物的“質(zhì)料”,就會被唾罵,因?yàn)檎l都明白一尊石雕與一塊石頭之間的關(guān)系。顯然體我們沒有理由說藝術(shù)作品的物性是它的實(shí)體,因此我們只能說它是一種“契機(jī)”,而實(shí)際上我們在上文所作的分析,就是在探討藝術(shù)作品中感性契機(jī)如何進(jìn)入藝術(shù)作品的實(shí)體,或者說,規(guī)定著“實(shí)體”。這本身是一個具有矛盾性的分析,因?yàn)閷?shí)體只規(guī)定而不被規(guī)定,我們怎么能說感性契機(jī)規(guī)定著實(shí)體呢?這就有一個裂隙出現(xiàn)了。如果藝術(shù)作品是一具體之物,但這一物之物性并不構(gòu)成它的實(shí)體,那么我們只能得出結(jié)論,這一“實(shí)體”不在這一“物”之中。這和我們在前面得到的結(jié)論一一質(zhì)料的性質(zhì)規(guī)定著藝術(shù)作品之間存在著一個裂隙:藝術(shù)作品的實(shí)體在物之外與藝術(shù)作品的實(shí)體在物之中。兩個結(jié)論之間存在著對立,但兩者都有效,這意味著,藝術(shù)作品作為一物,它的質(zhì)料性質(zhì)既是又不是它的實(shí)體。在兩者既聯(lián)系又對立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張力,而質(zhì)料就是在這張力的撕扯下,既介人而又被推出實(shí)體。這就是我們使用“契機(jī)”這個詞的用意:它僅僅是一個契機(jī)而不是實(shí)體;它并非與實(shí)體無關(guān),它引導(dǎo)與規(guī)定著實(shí)體。藝術(shù)作品既是而又不是自為存在。
參考文獻(xiàn):
[1]杜夫海納.審美經(jīng)驗(yàn)現(xiàn)象學(xué).韓樹站譯.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2.115
[2]克羅齊.美學(xué)原理·美學(xué)綱要.朱光潛譯.外國文學(xué)出版社,1983.59
[3]柳宗悅.工藝文化.徐藝乙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署,2006.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