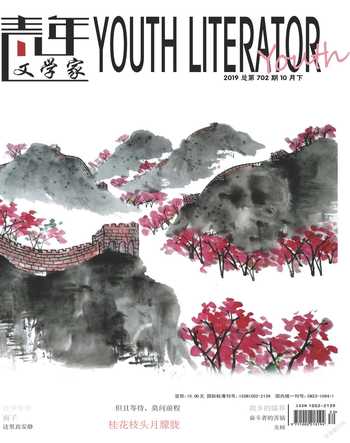奮斗者的苦惱
作者簡介:趙健(1986.11-),男,河南延津人,碩士研究生,工程師,研究方向:數據分析與挖掘、信息安全。
近期,看到一篇文章《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作者是唐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她還在“得到APP”學習平臺開設了《香帥的北大金融學課》,有22萬多人訂閱學習。
唐老師在這篇文章中說:“我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在中國最大的城市擁有房子,車子,我擁有一份不錯的職業,還能在自己熱愛和擅長的領域追求夢想……我似乎擁有一切,可是為什么我卻常常感到惶恐和疲憊?夜深人靜的時候,為什么我常常會感到一無所有?”寫這篇文章時,她41歲。
兩年后,唐涯結了婚,懷了孕,生孩子前夕,她用手機給學生們請假:“我們開學的時候,我已經懷孕5個月了,雖然做了很多課程的準備工作,但是最近身體還是出了一些狀況,寶寶估計是太想提前跟我們見面了,讓我有點措手不及。懇切地希望你能理解我第一次做媽媽的心情,也希望在我為小生命努力的過程中,能得到你的鼓勵和支持”。這一年,她43歲。
43歲懷孕生子,可以說是高齡,然而,當今社會,唐涯現象并非個例,“高智中產群體”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趨勢,正越來越明顯。他們普遍顏值在線、智商又高、工作努力、事業有成,是父母的驕傲和單位的標桿。只是,他們對工作和事業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時間,而忽視了對家庭和個人的關心。在人生這條道路上一味埋頭苦跑,等到有一天想安定下來的時候,回頭看,能跟上自己的人很少,繼續陪伴同行的則更為稀缺。最終,有人選擇降低標準,委屈自己,也有人選擇不將就,再次孤獨前行。
我不否認,存在一些人享受這個孤獨前行的過程,但更多人的感受是痛苦,優秀如唐老師,也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內心充滿了疲憊、焦慮甚至懷疑。這種疲憊感來自于家庭親人的嘮叨,來自于身邊朋友的指點,也來自社會上蕓蕓眾生異樣的眼光,要擺脫這種疲憊感,只能選擇向社會和現實妥協。人,終究是“社會人”,要遵循社會的習俗和約定,按照大部分人的模式去生活,只有融入主流,才會被社會接受。
這些人通常被冠以種種比較好聽的頭銜,譬如嫁給國家、娶了事業或者獻身科學之類,然而,上述選擇并非他們刻意追求,而往往是無奈之舉。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固然受到教育時間過長,生活壓力過大,甚至女權意識覺醒等方面的影響,但更大的原因還在自身,終究是不合群的緣故。況且,當今社會還沒做好廣泛接受這些現象的準備,領先時代一步的人是幸福的,領先時代多步的人多半會痛苦,任何時候,異類總要被排斥,一個人,思想上可以特立獨行,為了幸福,生活上最好隨大流。
這些人身邊又往往不缺作為對照的普通人,考試成績沒他們好,努力也沒他們多,甚至顏值不如他們,事業也完全被碾壓,但作為普通人知足常樂,生活得很幸福。這些幸福的人,早早地買了房,買了車,成了家,有了娃,考上了公務員,工作日上班領工資,休息日下班陪家人,朋友之間還時不時搞搞野炊和旅游,有的還培養了釣魚、長跑、攝影等愛好,生活過得其樂融融,你說氣人不氣人?
向來,奉獻有多少無好壞,工作有差異無貴賤,選擇也會有不同但無高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旁人自不必多舌。作為自認的奮斗者和成功者,他們當然希望被接納和認可,渴望被尊重和崇拜,而不是被身邊人指點和懷疑。他們自小被灌輸“知識改變命運”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育,真正到了社會上,反而變成“高知不幸”和“奮斗懲罰”,反差極大。
然而,在我看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更多是“競爭意識”和“過高定位”所致。他們內心被一種強烈的競爭意識所充塞,把現實生活看成了一場比賽,總想著在比賽中取得勝利,而根本不關心獎品是什么,只要求比別人的好,也只有比別人好,他們才會滿足。同時,他們又總是習慣性地高估自己,又過低地估計了他人,認為自己處于中上位置,配得上自己的最低也要中上,而看身邊人大多位置中下,就算遇到相對匹配的,又不珍惜,總認為有更好的在前方等自己,而在當今社會,找到一個更高的目標和更好的攀比對象是十分容易的。所以,他們就永不知足,總認為自己是受了委屈,最擅長推倒重來。
然而,對于多數人來說,奮斗都是個既孤獨又無趣的游戲,與其盲目奮斗,不如趕緊找個適合自己的定位安頓下來,穩扎穩打,更為實在。人生就像長跑,終點時一個靠前的名次固然令人欣喜,然而,若你的欣喜無人分享,勢必會大打折扣。不如在跑步的時候,暫時把終點和成績放一旁,花點時間去欣賞路旁美麗的風景,花點時間去結交身邊的朋友,也許最后的結果和成績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