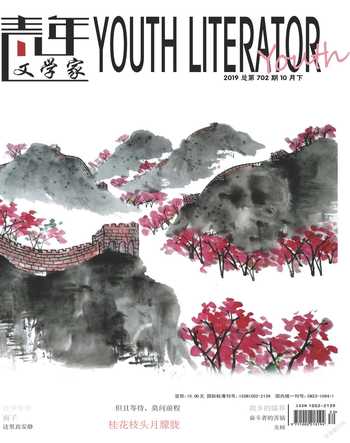后殖民女性主義視角下的《我愛比爾》
摘? 要:在后殖民女性主義的語境下,第三世界的女性面對著男性意識形態和西方意識形態的雙重建構。《我愛比爾》中的阿三,既體現出對西方虛構的文化標簽權威下的順從,在追尋自身社會身份時的迷失,又體現出了父權制、男性家長下的權力依附關系。但將男性/女性作為符號,象征西方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將性別話語與政治話語交織起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構出了性別對立的兩極,與目前的權力話語有著共謀關系。
關鍵詞:《我愛比爾》;后殖民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他者;權力話語
作者簡介:白婉寧(1995.8-),女,遼寧省葫蘆島人,遼寧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30-0-03
一、后殖民女性主義概述
瑪莎·李爾于1968年在紐約時代雜志上撰文提出了第一次女性主義浪潮與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的概念,并從此得到公認與沿用。第一次女性主義浪潮指的是19世紀主要由中產階級女性發起的對女性在社會與法律等方面不平等的改良運動,其關注點在于教育、就業、婚姻法以及中產階級單身知識女性的困境等方面。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則是指在60年代后期在美國與歐洲發生的一系列女性主義運動,鼓勵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權利爭取,其中心仍舊是白人女性。直到1992年,瑞貝卡·沃克在《女士(Ms.)》雜志上撰文宣稱“我就是第三次浪潮”,從此女性主義的第三次浪潮也登上歷史舞臺。與前兩次相比,第三次女性主義浪潮不僅反抗父權與夫權,也反對之前的女性主義者將全世界的女性同質化這一主張,試圖反映女性獨特的生活經驗,并將關注點投向少數群體,例如同性戀、跨性別者與第三世界女性等。
后殖民主義于20世紀70年代末形成,著眼于(主要包括而不限于前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文化差異與權力話語壓迫:“結果,東方就被東方主義的話語典型地制作成沉默、淫蕩、女性化、暴虐、易怒和落后的形象。正好相反,西方則被表現為男性化、民主、有理性、講道德、有活力并思想開通的形象[1]”。而在第三次女性主義浪潮的一部分支持者眼中,婦女與第三世界(權力關系中被壓迫的對象)有著內在的相似性:都被“少數話語”的主要代表,都被權力話語所歪曲,都是“啞言的主體”。斯皮瓦克在其《下屬群體能說話嗎?》中表示,第三世界的女性在數重壓迫之下喪失了自己的話語權,以一種扭曲、變形的形式由他人代言,這種歪曲不僅僅來自于男權話語,也來自于西方白人女性對想象中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殖民化。
因此,也有一部分學者將后殖民女性主義稱為“第三世界女性主義”,但“第三世界”這個分類未盡人意,因為這種地理空間的分類范疇太過狹隘——“后殖民不只限于一個被外來政權統治的地區,而是統合不同模式的權力壓迫結構[2]”,因此后殖民女性主義也應運而生,美國黑人女性的處境就是一個例子。對此,印度學者莫漢蒂給出了再定義:“第三世界是通過地理位置以及特定的社會歷史情況來定義的。因此,它也包括美國所謂的少數民族或者有色人種。[3]”就像《東方主義》一書中的“東方”并非僅僅存在于自然之中,而是人為建構出來的,可以引申為所有被壓迫、被歪曲、被想象出的地區一樣,“第三世界”也包括了在發達國家中受到壓迫和剝削的人群的含義。
二、后殖民主義:殖民化過程的烙印與標記
1、文化標簽的權威與順從
賽義德在《東方學》的開篇就寫道:“東方幾乎是被歐洲人憑空創造出來的地方,自古以來就代表著羅曼司、異國情調、美麗的風景、難忘的回憶、非凡的經歷。[4]”盡管《東方學》中的“東方”并非指的是遠東(東亞),但其面臨的境遇幾乎沒有差別:中國文化并不單一,而是融合而生的產物,在內部有著無數差異與矛盾,也逃離不了被標簽化的命運。在面對有所了解卻不精通的事物時,標簽化是最為方便快捷的方式,盡管這種標簽可能反映出一部分現實,但更多體現出一種想象與誤讀。
在《我愛比爾》的文本中,這樣的情節表現屢見不鮮。作為美國駐滬領館的一名文化官員,比爾聲稱他愛中國,而他似乎也是這么表現出來的:他愛中國飯菜,中國文字,中國京劇,中國人的臉,他還起了個吉祥的中國名字,畢和瑞,“和”與“瑞”都有其背后的典故。但實際上他在與阿三交往的最開始便亮明自己的態度:“我們并不需要你來告訴什么,我們看見了我們需要的東西,就足夠了。”而阿三自己也敏銳地有所察覺,“再聽到比爾歌頌中國,就在心里說:你的中國和我的中國可不一樣。”比爾對中國的熱愛是隔著層紗的,是浪漫與模糊化了的,他愛著的是自己想象中的中國,而非現實中的、他親眼可以得見的中國。
比爾的態度是一種代表。他對中國的印象更多地來源于中國古代的相關資料,但資料本身有限是一點,現代中國早已與古代中國相差甚遠是另一點,因此比爾以及一部分與他相似的西方人所追逐的只是他們構想中的古老符號,他們也將這樣的符號以偏概全地貼在整個群體身上。中國古代的烈女傳給比爾留下崇高與恐怖的印象,比爾便認為阿三在性觀念的想法上也是如此;等到阿三用自己的畫向他展現自己的性觀念時,他則有一種盲目的自信:“中國人對性不是這樣的態度”。在比爾眼中,東西方的文化是涇渭分明、是格格不入的,就算將事實擺在他眼前,他也仍舊會去維護自己想象中的刻板印象。
而與此相對的,這樣的文化標簽下,是被貼上標簽的對象的順從。阿三清醒地理解比爾的中國與自己的中國不一樣,也知道自己之所以吸引比爾是因為自己是一個中國女孩,但有她為了迎合比爾的喜好,或者說迎合在話語權力處于支配地位上的西方人的喜好,也很多次主動將自己標簽化了。當第三世界被遮蔽與歪曲的時候,它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這種遮蔽與歪曲。
2、社會身份的建構與迷失
在這種情況下,阿三就面對著在身份認同上的困境。一方面,她渴望擺脫掉自己的原始身份,離開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將自己同化進西方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她又無法真正脫離自己原本的文化身份,同樣也沒辦法讓自己真的變成一個西方人。阿三看比爾,覺得比爾是“銅像”,比爾看她也一樣:“兩人互相看著,都覺得不像人,離現實很遠的,是一種想象樣的東西”。
阿三對此也心知肚明。“她不希望比爾將她看做一個中國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爾,就是因為她是一個中國女孩。”她的目的也同樣明確:她不想成為對比爾來說異質的存在,也不希望比爾對她的感情僅僅停留在獵奇心理,她渴望與比爾同化,渴望站在一個與他平等的角度上,也渴望成為她理想中那個世界的一份子。但在這樣的社會身份的建構中,她就遇上了矛盾。她不希望被比爾稱贊“特別”或是“奇異”,但想要把比爾的目光留在她身上,她就必須要延續這種“奇異”:她化濃妝,穿奇裝異服,讓自己保持一種幾乎是觸目驚心的姿態。當比爾故作驚訝地說著胡話,將上海比作曼哈頓、曼谷、吉隆坡、梵蒂岡的時候,阿三確實地感受到了歡喜,因為那一瞬間她幾乎認為自己要消弭這種隔閡,她便雙手叉腰,擺出法國歌劇中那個熱情的吉普賽女郎的姿態:“我是卡門!”但她永遠也成不了卡門。
這種文化背景的隔閡是無法消除的。如果說比爾否定她的愿望的借口是政治(“作為我們國家的一名外交官員,我們不允許和共產主義國家的女孩子戀愛”),而這還給她留下了希望,那么法國畫商馬丁對她這種重新建構身份的否定則給了她更大的打擊(“但是馬丁卻比比爾更加破壞阿三的生活”)。她與馬丁之間存在著更切實的情感交流,但卻沒有辦法互相理解:“現在,阿三覺得和馬丁又隔遠了,中間隔了一個龐然大物,就是上帝。”這樣的隔閡就是致命的。因此最后她哀求馬丁將自己帶回法國,馬丁卻給予她冷靜的回答:“我從來沒想過和一個中國女人在一起生活……因為,這對于我不可能。”而阿三的幻想,也就僅僅止步于幻想。她在社會身份的漩渦中迷失,雖然知道重構身份不可能,卻無法自拔。
三、后殖民女性主義:女性的兩難處境
1、雙重權力話語的壓制
后殖民主義理論在強調殖民霸權文化壓迫的同時,由于將第三世界作為被壓迫的整體對象進行研究,對社會性別差異也存在著一定的漠視。后殖民主義理論家關注第三世界男性,而第三世界女性與之相比也有著獨特的身份處境。與在西方權力話語的權威下的順從所相對的,第三世界的女性也同樣承受著父權與夫權的壓迫,這種壓迫并不僅僅在于現實物質層面,也在于精神層面,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隱形壓制,而不是單純的性別歧視或者性權利的控制。
作為一個在畫畫上有著才華的知識女性,阿三卻似乎并沒有自我。當她與比爾保持關系時,她的世界里幾乎只有比爾:“阿三自己也忘了自己。……沒有比爾,就沒有阿三,阿三是為比爾存在并且快活的。”但后來我們得知,阿三對比爾其實也沒有那么深厚的感情:“阿三想到,當時聽到這消息的漠然勁,她簡直不知道,她究竟愛還是不愛比爾。”阿三對于自己理想與欲望的追求過程始終處于一種權力依附關系上面,她看似獨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實際上卻并非如此。她會畫畫,也有一定的才氣,她英語口語流暢,也擅長社交,在宴會上也可以應付自如——但她卻從未想過以自己的才華與手段,在她向往的西方世界找到一個立足之地。她的才華與手段,全成為了她尋找并依附于一個男人的籌碼,而她自己則成為了客體,成為男權關系下的附庸。
但阿三自己還渾然不覺。在酒店大堂“尋求機會”的時候,她還會被同樣尋求機會的其他女孩所傷害,只因為別人會將她們分為一類。她之所以還擁有這樣的自傲,因為她有著更遠的期望,因為她似乎已經掌控了自己的親密關系(“她以她流利的英語制服了他來自經濟強國的傲慢。此外,在性上面,阿三也克敵制勝,叫他乖乖地低下頭來。”),但實際上,只要她還存留著靠保持親密關系的男性來達成目的的想法,她便是權力關系中真正的受制者。
2、性別話語與權力話語的交織
王安憶自己曾談起過《我愛比爾》的創作初衷:“其實這是一個象征性的故事,這和愛情、和性完全沒有關系,我想寫的是我們第三世界的處境。[5]”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比爾就是西方世界的象征,阿三是第三世界的象征。這似乎可以解釋王安憶這部小說對于性格構建過于平面與夸張化的原因: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因為虛無縹緲的追求草率退學,最終淪落為暗娼,這樣的故事情節夸張到不讓人信服,但因為阿三這一形象是第三世界的象征,那么故事情節也有著相應的象征化。從這個角度來說,阿三便從本應有血有肉的女主角,降級成為了政治諷喻需求的一個載體。
用兩性關系來象征政治關系的作品屢見不鮮。在1940年一幅以英法協約為題材的德國漫畫中,法國的化身瑪麗安娜便以一種蕩婦的形象出現。她背對著德國人,挽著約翰牛的手,以一種輕蔑的姿態昂首闊步地離開。愛爾蘭詩人威廉·葉芝創作的劇本《胡里痕的凱瑟琳》中,愛爾蘭的化身凱瑟琳則是表現出一種號召群眾犧牲的姿態。她則因為這種犧牲,從一位老婦人轉變為“邁著女王步伐的年輕女孩”。
但當性別話語與政治話語交織在一起時,無論是西方與第三世界,還是男性與女性的關系,都被進一步固化,以至于建構出對立的兩極。在這樣的兩極中,第三世界在西方的文化霸權下喪失自己的主體性,女性也在男性權力話語的掌控之下失去自我,以一種附屬物的方式存在。這無疑是對女性化的東方與男性化的西方這樣的建構的一種延續,是男性認同的一種延續,也是對女性的輕視的一種延續。在這樣的話語建構中,女性再一次成為了他者,處于邊緣化的地位,衡量女性的并非女性自己,而是男性的標尺。當后殖民主義將第三世界男性看做西方眼中的他者的時候,第三世界女性同樣也成為了“他者”眼中的“他者”。而“他者”是無法為自己的形象辯白的:對她們作出定義的是其他擁有話語權力的群體,盡管這樣的定義與她們本身的情況大相徑庭。
王安憶的本意可能是對這種不平等關系的諷刺,但她同時卻加重了這種加諸在第三世界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女性的身體以及婚戀關系已經不再是私人問題或自由選擇,而是與政治問題掛鉤,上升到了公共空間。在這樣的公共空間里,任何人都可以對女性的自由選擇作出批判:即,“她并非由于愛情,而是由于物質原因與社會身份的再建構,是一種拋棄祖國向西方臣服的行為”。盡管這其實仍舊是自由選擇,但隨之而來的道德壓力與蕩婦羞辱讓這一選擇不僅僅是自由選擇那么簡單;即使某位女性的選擇與上述原因無關,她也要承受同樣的審視與誤讀。而與此同時,女性特質再一次與軟弱、低效、神經質掛鉤;男性特質則(一如既往地)與堅強、高效、理性所掛鉤。
在這種情況下,第三世界女性更沒有辦法發出自己的聲音。福柯認為話語是一種力量,她們很顯然并不具備這種力量,或是聲音太小,無法讓大多數人能夠聽到。因此,將性別話語與政治話語交織起來,無疑加重了這樣的誤讀:當下屬群體的呼聲更加微弱的時刻,這種建構就與目前的權力話語產生了一定的“共謀”關系。
結語:
王安憶并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作家。“我確實很少單單從女性角度去考慮問題,好像并不是想在里面解決一個女性的問題,我沒有這樣想,總是覺得世界是男女共有的,這是很平衡的生態,偏哪一方都不行,但是有一點我覺得也許和女性主義有關聯的。”但同時她也表示:“這些東西我寫出來以后就不屬于自己了,就是任人評說的。[6]”王安憶將第三世界整體的困境通過象征的形式表現出來,她自己也說并非單純的情愛。然而只要用愛情故事和兩性關系的手段表現出來,這篇小說也就與性別敘事離不開關系。當將一個復雜的群體具象化為某個人物的時候,主題先行的弊端也就不可避免。
后殖民女性主義仍舊是在發展中的一系列理論,并非是一個完全的整體。盡管從目前來講,第三世界女性的處境已經得到了大幅改善,但也依舊面對著啞言的困境。對《我愛比爾》這篇小說文本的思考,也不應僅僅停留于作者想要并試圖表現的部分,而是需要向更廣闊的地方開掘。
注釋:
[1](p44-p45)巴特·穆爾-基爾伯特:《后殖民理論——語境 實踐 政治》,陳仲丹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p12)肖麗華:《后殖民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3](p2)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 Lourdes Torre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4](p1)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5月第一版.
[5](p252)王安憶,劉金東:《我是女性主義者嗎?》,選自張新穎,金理編:《王安憶研究資料 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6](p250)王安憶,劉金東:《我是女性主義者嗎?》,選自張新穎,金理編:《王安憶研究資料 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參考文獻:
[1]羅鋼.裴亞莉.種族、性別與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批評實踐[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0(01):100-108.
[2]林樹明.性別意識與族群政治的復雜糾葛:后殖民女性主義文學批評[J].外國文學研究,2002(03):14-21+167-168.
[3]余海艷.“民族寓言”:后殖民理論視閾下的王安憶小說[D].溫州大學,2015.
[4]葛亮.全球化語境下的“主體”(他者)爭鋒——由《我愛比爾》論“第三世界”文化自處問題[J].文史哲,2010(02):157-166.
[5]張蓉,賈辰飛.后殖民主義文化心理下的生存困境——《我愛比爾》[J].安徽文學(下半月),2008(09):179-180.
[6]薩義德.王宇根譯.東方學[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7]肖麗華.后殖民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