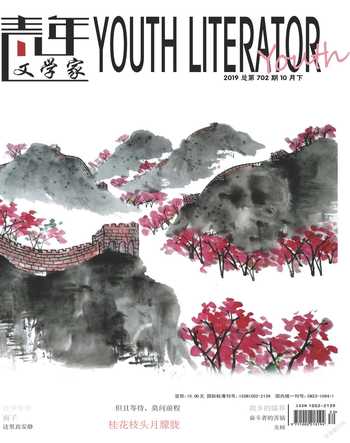日本近代兒童文學的創作形式及其流變
張婷婷 劉蒙歌
基金項目:遼寧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類青年項目“批評語言學視角下的中日近現代兒童文學創作意圖之比較研究”(L201783675)。
摘? 要:本文試從日本近代兒童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著眼,以代表作家的作品創作形式為研究對象,運用文獻綜述法梳理并分析近代社會背景下不同歷史階段的作品創作的形式特點及其流變規律。著重對作品內容進行解讀,凸顯作品的創作意圖,剖析其創作形式發生流變的內外動因,揭示日本兒童文學的創作目的及其社會功能。
關鍵詞:日本兒童文學;御伽噺;紅鳥運動;生活童話;現實主義兒童小說
作者簡介:張婷婷,女,遼寧大連人,博士學歷,遼寧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日語語言文學與文化;劉蒙歌,女,河南洛陽人,大學學歷,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學生,研究方向為日本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30--04
引言:
眾所周知,明治維新運動是日本步入近代化的標志。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包括兒童文學的誕生。日本兒童文學的誕生雖然比西方晚了上百年,但是由于日本社會經濟的推動以及日本人熱愛學習的精神,促使他們步入翻譯西方兒童文學著作的道路,期間誕生了數部外國著名兒童文學的優秀譯本。其中,若松賤子翻譯的《小公子》在當時被稱為明治時期少年文學譯本中的代表性作品。這些譯本可以說是日本兒童文學誕生的有力鋪墊。
“一般,多數學者主張1955年(昭和三十年)是現代兒童文學的起點”[1](筆者譯),也就是說日本兒童文學中的所謂“近代”是截止到昭和三十年的。以此為據,本文試從近代早期(明治時期)、近代中期(大正時期)和近代后期(大正末期至昭和三十年代)三個歷史時期入手分析各時期的兒童文學作品的創作形式,歸納其流變規律。
1、近代早期的日本兒童文學作品
1.1日本兒童文學的誕生
明治維新提倡“文明開化”,在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所以,明治初期是對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階段。日本兒童文學真正的誕生是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當時最大的出版社博文館創刊的“少年文學叢書”便是其標志。巖谷小波(1870-1933)創作的《こがぬ丸(黃金丸)》是刊登在上面的第一部作品,敘述了一只叫黃金丸的小狗在獵犬的幫助下為父報仇的故事。黃金丸的父親中了狐貍的奸計,被老虎殺死。在經歷重重困難后,黃金丸最終在獵犬的幫助下為父親報了仇。這部作品一經出版,便立刻引起了巨大反響,國家和地方的報刊、雜志紛紛刊登評論文章。當時的指導性雜志《國民之友》在《黃金丸》剛發售的時候就在書評欄中反復刊載評論。多數人稱贊這部作品開了新風,但是也有評論說它只是關于復仇的老套故事。菅忠道在他的書中寫到:
巖谷小波后來回憶說,這部作品在現在看來比較落后,但是在當時卻是彌足珍貴的,是兒童文學的一塊基石。[2](筆者譯)
1.2巖谷小波與御伽噺
繼《黃金丸》之后,巖谷小波又陸續發表了許多作品,他的這些作品被稱為“御伽噺”(講給孩子們的童話)。作為明治時期最大的兒童雜志《少年世界》的總編,巖谷小波身邊聚集了很多弟子。“御伽噺”成為了他們當時的創作形式,并且貫穿了整個明治時代的兒童文學。
巖谷小波的“御伽噺”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成為兒童文學的代表,是因為它們對明治時代的兒童的成長,以及大正時代之后國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其作品不太偏西歐化,充分考慮到了讀者的理解能力,寫作風格有自己的特色。
巖谷小波曾說,謊言有兩種。一是像事實一樣的謊言,二是像謊言一樣的謊言。前者是罪過,而后者卻是天真和單純。童話就是這樣一個天真又充滿愛的謊言。他認為童話不僅對兒童教育有輔助作用,更是一種精神教育。同時,童話并不是逗孩子們開心的工具,而是切合日本當時的時局以及社會需求的。
日本的兒童文學之所以在明治時期誕生,是因為具備了必要的社會條件,一是新的兒童觀的產生,二是日本跨入了近代的社會階段。新的兒童觀就是承認兒童的人格,認為除學校教育以外,還應給兒童能夠從中獲得快樂的文學作品。日本跨入近代化后,普及義務教育,于是關于兒童教育的雜志叢書相繼誕生。巖谷小波的御伽噺充分適應了國家對兒童教育的路線,廣受歡迎,并為此后的大正兒童文學做了鋪墊。
1.3冒險小說的流行
明治初年,翻譯文學中冒險類小說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廣受青少年讀者的喜愛。森田思軒翻譯的《十五少年》與若松賤子翻譯的《小公子》在當時被稱為明治時期少年文學譯本中的代表性作品。明治二十三年(1890),矢野龍溪創作了名為《浮城物語》的冒險小說。它并不屬于少年文學,而是一本政治小說。主要反映出了日本帝國時期的“南進論”,不僅受到了青少年讀者的喜愛,更是對后來的少年冒險小說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明治二十九年(1896),森田思軒翻譯并出版了《十五少年》,它迎合了甲午戰爭后日本想要向海外擴張謀求發展的思想潮流,廣受追捧。
對冒險小說的流行趨勢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巖谷小波的弟子押川春浪(1876-1914)。押川春浪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日俄戰爭即將打響之際,創作了《海底軍艦(海底軍艦)》等一系列作品。因其采用了武俠小說的形式而著名,成為了日俄戰爭中代表性少年刊物。
《海底軍艦》是押川春浪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故事以第一人稱的講述方式,描寫了旅行家柳川龍太郎在結束了世界之旅后,于返回日本的途中,受朋友所托,攜少年日出雄同返日本。然而在途徑印度洋的時候遇到了海盜船的襲擊,柳川和日出雄兩人漂流到了一個孤島上。這個孤島是一個名叫櫻木的海軍大佐從一年半以前就開始建造的“秘密造船廠”。柳川加入了秘密造船廠的建造,和眾人一起,克服重重難關,最終建成海底軍艦,徹底消滅了海盜。
學者岡崎由美曾指出:
因其深受法國作家維恩(凡爾納·儒勒Jules Verne)的影響,故在類型上更近似于科幻驚險小說,大都以現代的冒險家漫游各國,探索秘境為主要內容。[3]
其實,這部小說不僅在內容方面受到了凡爾納作品的影響,極具冒險與挑戰,尤為突出的是其思想層面上帶有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
總之,冒險小說在這一時期十分流行。這種以滿足刺激、驚悚等感官需求為主的冒險小說美化了帝國主義侵略思想以及種族歧視觀念。可以說,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兒童文學的一般創作形式。
1.4近代早期的日本兒童文學作品的創作形式特點
在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浪潮中被翻譯出來的《通俗伊蘇普物語》、《魯敏遜全傳》等面向成人的故事,像民間故事一樣以口頭講述的形式走進了兒童的世界。明治24年,巖谷小波創作的《黃金丸》,成為刊登在《少年文學叢書》的第一個作品,并且敲響了日本兒童文學黎明的鐘聲。從此,少年文學開始成為真正的兒童讀物。《少年文學》發刊的同年,《幼年文學叢書》也被計劃發行,巖谷小波為“幼年文學”創造了“御伽噺”這個用語。“御伽噺”由此開始普及起來。
“御伽噺”這一創作形式的特點是重視“教育意義”和“娛樂性”,而忽略原著的“文學性”,省略了原著中的人物性格、心理描寫以及環境描寫,只保留了故事的旨趣,賦予故事簡單樸素的風格。
雖然巖谷小波創作的是以健康的常識為主旋律的進步的文學形態,但保留了封建的影子,思想境界不夠深遠。而他的弟子押川春浪所引導的文學形態,一方面是將巖谷小波未完成的國民教化的任務不斷推進,另一方面則是舍棄了巖谷小波的保守的兒童文學創作,嘗試極具近代批判精神的創作形式,反映黑暗的現實社會。其創作特點是將青少年強烈的民族意識與國家主義結合起來,給青少年灌輸海外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思想。
2、近代中期的日本兒童文學作品
2.1《紅鳥》雜志與童心文學
大正時期,市民情調和近代藝術的興起對日本兒童文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鈴木三重吉(1882-1936)作為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得意門生,在眾多名作家的幫助下,于大正七年(1918)創辦并主編了《赤い鳥(紅鳥)》雜志,并且由此發起了“紅鳥運動”,激勵了童心文學的創作。
《紅鳥》創刊的主要目的是,在否定以往的、低級無味的作品的基礎之上,提倡純藝術的、有價值的、純潔美妙的創作。[4]
應邀參加紅鳥運動,為《紅鳥》撰文寫稿的名家不在少數。《紅鳥》還掀起了童話、童謠的熱潮,類似的童話雜志也相繼創刊。總之,正如坪田讓治所評價的那樣,“那個時期,沒有寫過一篇童話的作家屈指可數”[5]
大正時期的“童話”推崇“童心主義”。童心主義不只是強調兒童心理的特殊性,而且是和思想以及文學的角度結合起來的。最早將童心作為文藝理念并付諸于文學創作實踐的是小川未明。
小川未明主張童話不一定是僅僅面向兒童的,而是面向一切擁有童心的人的。秋田雨雀也曾說過童話是為“永遠的孩子”創作的。大人為兒童展現的童話世界是大人對自身的生活的反省。但是,秋田雨雀同時也指出,即使童話是大人的理想世界,大人也不能將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兒童。每一個兒童都是獨立的人,要讓他們自由地成長,大人只是在一旁幫助他而已。這是秋田雨雀的兒童觀及教育觀。
2.2 小川未明的童話創作
伴隨童話流行的這股熱潮,積極投入童話創作的名家大有人在,但是也有圍繞著童話的創作而對社會現實進行批判的作家,小川未明(1882-1961)便是其中一員。一戰后,日本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露出了它的弊端,各種因資本主義產生的社會問題使得勞動大眾苦不堪言。小川未明作為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發起人,出版了一系列對勞苦人民飽含同情的作品。
小川未明于大正十年(1921)創作的童話《赤いろうそくと人魚(紅蠟燭與美人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這個充滿幻想的作品其實反映了現實的兒童問題。故事講述了一個生活在深海里的人魚母親聽說人間是個溫暖的地方,便把剛出生的女兒送給了一對賣蠟燭的老夫婦。兩人把女兒撫養成了一個美麗的人魚姑娘,但是因為人魚姑娘能夠畫出暢銷的畫作,老夫婦便利欲熏心,對女兒的過度勞動不管不問,后來甚至把她當作物品賣掉了。這篇童話作品反映的社會問題有“棄子”“童工”以及“人身買賣”,表達了作者對弱者的同情和以及對不公的憤怒,同時也揭露了當時社會遺留的封建性和資本主義的弊端給兒童帶來的傷害。
小川未明的童話是無產階級兒童文學的先驅。將社會主義思想用浪漫主義手法表達出來是小川未明童話的一大亮點。
2.3近代中期的日本兒童文學作品的創作形式特點
為了把明治期的說書性質的御伽噺轉變為文學性強的童話,提高兒童文學的質量,鈴木三重吉在眾多文壇名人的協助下創辦了《紅鳥》雜志并發起了“紅鳥運動”。紅鳥運動不僅止于“童話童謠運動”,還發展到涵蓋音樂、兒童畫、自由詩、自由畫等方面的“綜合性兒童文化運動”,這是“紅鳥運動”最大的特色。
近代中期童話的特點是重視“童心主義”。“童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美、詩心、驚異、靈魂和永生構成的。描寫對絕對事物的探究,通過幻想性童話是最合適的。”[6](筆者譯)
巖谷小波所代表的御伽噺含有封建道德觀念,宣傳的是仁義忠孝,勸善懲惡的陳舊儒教思想,迎合了明治時期富國強兵的時代風潮。而大正期以《紅鳥》為代表的童話則是基于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新思想,響應的是探索個人生存方式的時代風潮。與巖谷小波的“御伽噺”相比,小川未明的童話更具有近代文學思想性。明治到大正的兒童文學從“御伽噺”發展到了“童話”(這里的童話在當時泛指創作兒童文學),這是作家創作形式的流變,也是日本兒童文學的質變。
3、近代后期的日本兒童文學作品
3.1楨本楠郎與無產階級兒童文學
如果把大正時期的兒童文學比喻成百花齊放的春天的話,那么大正末期至昭和前期這段時期便是兒童文學的寒冷冬天了。
昭和二年(1926),日本爆發金融危機,民生處于崩潰邊緣。在這樣的經濟大蕭條中,大正時期兒童文學的支柱性雜志基本都停刊了。雖然在1929年停刊的《紅鳥》雜志于1931年重新復刊,但是再也回不到那個繁盛時期了。取代大正時期童心文學的是無產階級兒童文學。
楨本楠郎作為無產階級兒童文學的理論指導者,于1930年出版的《プロレタリア児童文學の諸問題(無產階級兒童文學的諸問題)》和《プロレタリア童謡講話(無產階級童謠講話)》這兩部評論集,成為了那個時期兒童文學的里程碑式作品。這兩部評論集的主要內容是對大正時期童心主義兒童文學的超階級性的批判。楨本楠郎關于兒童文學的理論是最早而且是比較系統的理論,這一點是必須予以肯定的,但是他的理論的政治性太強,并且偏急進主義傾向。
3.2坪田讓治與生活童話
無產階級兒童文學后來遭受了日本政府的瘋狂鎮壓,當時的日本兒童文學作家只好把“生活童話”[7]當做無產階級兒童文學的偽裝。“生活童話”主要描寫勞動階級的兒童的現實生活,其中成就卓著的要屬坪田讓治(1890~1982)。
昭和二年(1926),坪田讓治的第一部小說集《正太の馬(正太的馬)》出版,同年,他第一次在《紅鳥》雜志上發表了作品《河童》,接著又發表了第二個作品《善太と汽車(善太與火車)》。且通過《お化けの世界(妖怪的世界)》(昭和十年發表)這部作品確定了他的文壇地位。并且,在此期間他投稿于《紅鳥》雜志的“生活童話”推進了日本現實主義兒童文學的發展。
坪田讓治于昭和十年(1935)在《紅鳥》雜志上發表的小說《魔法》,是他的兒童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說講述了一個叫善太的男孩半開玩笑似的對弟弟三平說自己會施展魔法,正說著要把和尚變成蝴蝶時,剛好有一只蝴蝶飛了過來,幼小的三平便信了魔法的存在。第二天,善太對三平說“我會用魔法從學校回家”,三平便信以為真,在家滿懷期待地等哥哥回來。當狗沖他跑來時,他大叫:“你就是哥哥變的吧,我認出你來了!”可是回到家的哥哥終于無法繼續編造謊話了,而且看著弟弟被自己捉弄的樣子忍不住笑了起來。弟弟三平終于明白哥哥說的不是真的,便和哥哥打鬧起來。
這篇小說中的兒童形象極具真實感,坪田讓治對文中兒童的心理、動作及表情的描寫十分細膩。
正如朱自強在他的書中所評論的那樣:坪田讓治并不像小川未明、濱田廣介等人那樣,用象征的、詩的、童話式的方法描寫兒童,而是用小說式的、現實性的手法來描寫兒童,他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現實感的活生生的兒童形象。[8]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的兒童文學界付出了諸多努力,期間也誕生了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及作品,但總體而言還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冬天。原因主要是戰爭的影響以及政府的束縛。
3.3現實主義兒童小說
昭和二十年(1945),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處于寒冬期的日本兒童文學也隨著戰爭的結束而逐漸出現了轉機,日本兒童文學的創作形式也從“童話”向“小說”轉變。究其原因,日本戰敗后受美國控制,甚至可以說是變成了美國的附屬地,日本兒童也不再像戰前那樣受到保護。被美國駐扎在日本的軍事基地奪走生存區域的孩子們,深深體會到了社會現實的殘酷,再也無法用童話喚起他們美妙的幻想了。因此,描寫現實的兒童小說開始成為了時代的潮流。
戰后現實主義的里程碑是山中恒的《紅毛小狗》[9]昭和二十八年至昭和三十一年(1953-1956),山中恒的小說《赤毛のポチ(紅毛小狗)》連載于《小伙伴》雜志上。名叫和子的主人公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有一天她意外得到了一只可愛的紅毛小狗,卻又被有錢人家的孩子館田武搶走,并被他辱罵為“鄉巴佬”。然而,和子在經歷了種種殘酷的社會現實后并沒有灰心喪氣,而是慢慢成長了起來。
這部作品通過對當時社會的貧富差距及底層人民的窮苦生活的描寫,表達了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孩子們的同情和鼓勵。
作家唐戈云在文章中這樣描述山中恒的作品:在多角度展示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和家庭關系、社會關系的同時,作者也溫熱地關注著孩子們在壓抑中、在成長過程中潛在的求知愿望和抗爭意識、自由意識。[10]
3.4近代后期的日本兒童文學作品的創作形式特點
《紅鳥》雜志由于昭和二年的金融危機而衰敗,童心文學也被無產階級兒童文學所取代。無產階級兒童文學批判童心文學脫離了社會性,認為在創作兒童文學時應該考慮兒童所處的社會環境。雖然無產階級兒童文學的特點是政治性太強,在現在看來沒有很多值得鑒賞的,但是它不僅影響了兒童文學界,還影響了教育界。而生活童話作為無產階級兒童文學的偽裝,它的特點是偏現實主義,它也確實推動了現實主義童話的進步。
日本的兒童文學向小說轉變的原因主要是戰后兒童的問題已經無法用童話來應對。大多學者認為小說是從1954年山中恒創作的《紅毛小狗》開始的。山中恒的作品成為戰后小說的鼻祖不是因為他的寫作方法,而是因為他活用連載的優點,把握變化中的社會形勢并反應在作品中的創作態度。他的作品特點是通過把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社會融入作品反過來再去影響現實,這也對后來的很多作品產生了影響。
結語:
自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兒童文學的誕生以來,為構建和改良日本兒童文學,為兒童書寫美妙篇章的近代作家,不僅僅是以上列舉的幾位,只是由于篇章關系舉出了典型的代表。日本兒童文學以翻譯外國著作為鋪墊,以巖谷小波開創的“御伽噺”為開端,“御伽噺”又逐漸發展成為“童話”,“童話”后來又向“小說”轉變。兒童文學作家們為適應社會的需求和時代的潮流,成就了兒童文學創作形式的流變。分析日本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后,可以從側面看出日本社會文化以及教育方面的特點,比如深受童心主義兒童觀影響的教育觀,即“主張讓兒童躬行實踐, 通過體驗感知社會, 感受世界, 保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環境。”[10]
日本的兒童文學的創作基本都是反應社會需求的,比如巖谷小波的作品都是以仁義忠孝的教育為根本,目的是回應明治時期國家富國強兵、立身出世的時代要求。雖然傳播的是勸善懲惡的古老儒教思想,但是實際上也適應了明治時期的社會需求。另外也有對社會的批判,比如小川未明的作品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給兒童帶來的傷害。但是兒童文學始終不變的目的是通過創作更好的作品,幫助兒童更好的成長和進步。
正如前文說道,巖谷小波認為童話并不是逗孩子們開心的工具,而是切合日本當時的時局以及社會需求的。的確,兒童文學并不只有娛樂功能,它更多的是社會功能。通過切合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需求,兒童文學的創作形式產生流變也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其“教育”這一社會功能。
注釋:
[1]日本児童文學學會編.日本児童文學概論[M].東京書籍,1976:87,88.
[2]菅忠道.日本の児童文學[M].東京:大月書店,1979:24.
[3]岡崎由美.“劍俠”與“俠客”——中日兩國武俠小說比較[A].縱橫武林——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臺灣:學生書局,1998:2.
[4]王敏.日本兒童文學中的童心主義[J].外國文學研究,1986(03):101.
[5]菅忠道.日本の児童文學[M].東京:大月書店,1979:100,101.
[6]日本児童文學學會編.日本児童文學概論[M].東京書籍,1976:109.
[7]陳玲玲.中日現代兒童文學發展進程比較[J].北京社會科學,2001(02):51.
[8]朱自強.日本兒童文學導論[M].湖南: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148.
[9]朱自強.日本兒童文學導論[M].湖南: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190.
[10]唐戈云.神奇山中恒的鬼魅力量[J].中華讀書報,2006(12):1.
[11]張婷婷.“從兒童文學中的動物形象看中日兩國的兒童教育觀”[J].東北亞外語研究,2018(4):96.
參考文獻:
[1]小川未明,『赤いろうそくと人魚』,巖崎書店,1982.
[2]押川春浪,『海底軍艦:海島冒険奇譚』,平凡社, 2015.
[3]坪田譲治,『魔法の庭:坪田譲治児童文學選』,株式會社香柏書房,1946.
[4]新美南吉,『新美南吉童話集』,偕成社, 1982.
[5]宮沢賢治,『銀河鉄道の夜』,講談社, 1982.
[6]山中恒,『赤毛のポチ』,理論社,1969.
[7]劉曉東,“日本大正時代童心主義史論”,《南京師大學報》,2018.3.
[8]莽永彬,“鈴木三重吉與日本現代兒童文學”,《東北師大學報》,1981.1.
[9]周曉靚,“初探日本近代兒童文學中的國家主義基因——以萌芽期為中心”,《對外傳播》,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