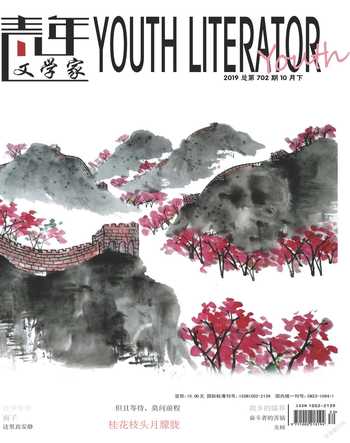從冠禮演變看宋明社會文化特征
摘? 要:冠禮隨著社會歷史發展不斷演變。比較《儀禮》《朱子家禮》《司馬氏書儀》等史籍中記載的冠禮儀式可知,冠禮從早期面向貴族的成人禮,逐漸發展成適用于士庶兩族通用的禮儀。這一變化是唐宋以來門閥貴族衰落,庶族與市民階層興起導致的。同時,冠禮中的“家族”元素也不斷增強,這反映了宋明以來近世社會思想文化的演變潮流。
關鍵詞:冠禮;變化;宋明社會
作者簡介:王藝然(2002.9-),漢族,黑龍江大慶人,大慶實驗中學2020屆在讀高中生,研究方向:歷史學。
[中圖分類號]:K8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30--02
冠禮是中國古代的基本禮儀之一。國內學者關于冠禮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大多著眼于冠禮的某一方面或某一時代的冠禮,對冠禮長時段的演變過程鮮有涉及。[1]
研究冠禮,《儀禮》與《朱子家禮》是基本文獻,《司馬氏書儀》承上啟下,同樣有著較高的研究價值。《儀禮·士冠禮》是記載中國古代冠禮儀式最詳細的文獻資料。《司馬氏書儀》和《朱子家禮》以《儀禮》為本,根據社會發展和現實狀況不斷變通,對冠禮儀式進行調整。三部文獻對冠禮的闡述不盡相同,卻一脈相承。雖然這些文本中的儀式往往不能完全落實,但文本反映了文人群體對冠禮的認識及其相對應的禮儀觀念。因此,本文擬以《儀禮》《司馬氏書儀》和《朱子家禮》這三種記載冠禮儀式的文獻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文獻中冠禮儀式的發展演變,簡要探究各時段冠禮的特征,梳理冠禮與宋明之后社會發展的關系及其體現的社會思想變化。
一、冠禮變化的特點及趨勢
1、冠禮的適用范圍擴大。
冠禮的主體逐漸由貴族士大夫擴展到平民階層。這一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本中關于冠禮適用范圍的表述存在明確變化。《儀禮》中有關冠禮的記載很明確指出是“士冠禮”。《〈儀禮〉疏注》解釋道:“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2]可以看出,此時的冠禮是貴族男子年滿二十歲,成為本族正式成員之際舉行的一種加冠典禮,使親族明確認定其已經成人。而這類用詞和表述在《司馬氏書儀》和《朱子家禮》已經不見蹤影。
二是儀式的簡化,如加冠時衣冠服飾的變化。據《儀禮》所記,舉行冠禮的男子初加緇布冠,象征將涉入治理人事的事務,相應的衣服是玄端,為士級別的朝服和私祭的禮服,配緇帶、爵鞸;再加皮弁,象征該男子將介入兵事,擁有兵權,配緇帶、素鞸;三加爵弁,象征該男子擁有祭祀權,爵弁服是士助君祭祀時所穿的服裝,為士的最高禮服。從中可以看出,《儀禮》主要面向士以上階層,適用范圍較小。《司馬氏書儀》的冠禮儀式與《儀禮》大體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對相關儀式進行了調整和省簡。如將《儀禮》中“三加”使用的緇布冠、皮弁冠、爵弁冠,換成了宋代流行的巾、帽、幞頭,降低了舉辦冠禮的成本,更適合普通百姓。《朱子家禮》沿用《司馬氏書儀》的做法:“一加冠巾,服深衣,納履;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帶,系鞋;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襕衫,納靴。”[3]宋代冠禮儀式中的簡化,在保存了古代冠禮典型形式的同時,降低了舉行儀式的經濟成本與知識壁壘,體現了“禮下庶人”的思想,這無疑有利于冠禮的普及。
除適用階層的擴大外,冠禮適用范圍的擴大還體現將女性納入儀式主體的做法。《儀禮》詳細記載了冠禮的禮儀,卻集中于男子的冠禮,只是偶爾提及女子的角色。《司馬氏書儀》和《朱子家禮》中不單記載了適用于男子的冠禮,且附載了適用于女子的成年禮——笄禮。關于笄禮的明確記載,表明家庭禮儀的適用主體已由男性擴展到女性。雖然笄禮和冠禮在內容和禮儀的隆重程度上有明顯的差別,且笄禮在本質上從屬于婚姻,但仍能從中看出女性禮儀的發展以及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變化。
上述種種變化反映了儒家學者將普通百姓逐漸納入禮制范圍的努力,擴展了禮儀在百姓中的影響力,體現了傳統禮學的革新。
2、冠禮儀式中家族意義的增強。
這主要表現在“家族”在儀式中的參與度增強。一方面,隨著社會觀念的變化,鬼神祭祀已不再是主流,“筮日”“筮賓”等環節至宋代已不適用。《儀禮》詳細記載了筮日、筮賓的過程。《司馬氏書儀》仍將其保留,但《朱子家禮》卻做出更換:“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前一日,宿賓。”[4]《朱子家禮》不再以筮日來確定舉行冠禮的日期,“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5];不再以筮賓來確定行禮的賓客,“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6]。古禮筮日、筮賓的習俗在宋代已經無法執行,只得刪去。《朱子家禮》中對此提出了相似的、可作替代的方式,如“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等。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宋代宗族勢力的擴張,建設家族組織的構想和家族觀念的增強。
另一方面,宋代家族觀念的塑造在不斷增強。如《儀禮》中男子加冠后見國君、卿大夫及鄉賢,在《司馬氏書儀》和《朱子家禮》中改為見于鄉先生及長輩。至宋代,人們加冠時拜見國君顯然很難實現,所以改為見鄉先生和父親的好友,向社會宣告自己的成人身份,這顯然更具有現實意義。又如“見母”的程序“改為見尊長”,包括堂中父母、諸叔母姑、諸姊嫂,統一拜見家中長輩。
上述所舉內容僅是冠禮在《儀禮》和《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中若干差異的一部分。這些差異集中反映了在禮制發展過程中,冠禮儀式步驟中家族意義逐漸增強這一特點。
二、冠禮儀式轉變原因分析
《儀禮》記載的禮儀,帶有明顯的貴族色彩。隨著氏族制社會進入貴族宗法制社會,原本作為習慣使用的禮儀轉化為鞏固貴族統治的手段。“冠禮”也隨之出現,由氏族公社的成丁禮變為貴族在本族舉行的成年禮,用以明確成員們的權利和義務,從而維護貴族階層利益和宗法制度,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因此該時期舉行冠禮的主體為貴族階層,且禮儀較復雜繁瑣。
隨著社會的變遷,“士禮”運用范圍越來越小。隋唐以后,門閥制度衰落。隨著科舉制的產生與發展,庶族通過考試進入政治核心,社會階層流動加快,士族和庶族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他們要求有適合自身的禮儀,士庶通禮由此出現。
而到宋代以后,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擴大,士庶之間的界限也逐漸模糊,禮儀面向的社會群體進一步擴大。許多有學之士如司馬光和朱熹,在儒學復興的背景下提出了恢復冠禮的倡議。因此,宋代冠禮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又被賦予了新的內容。禮儀的簡化調整使其更易被士庶接受,成為人們家庭生活參考準則,而適用范圍的擴大也推動了禮儀的普及和發展。
三、結語
冠禮作為士冠禮,是屬于早期貴族階級的特權。然而隨著各朝各代的不斷更替,冠禮從形式到內容都出現變化,逐漸發展成適用于士庶兩族通用的禮儀。這與整個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
冠禮的這一演變順應了時代的發展趨勢,這從明代冠禮復興中可見一斑。例如,成書于萬歷年間的《皇明典禮志》記載了皇帝加元服、皇太子冠禮、品官冠禮和庶人冠禮,在皇室、士人、庶人等多個階級中普遍推行冠禮,可見冠禮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力。在《皇明典禮志》有關冠禮儀式記載的末尾,作者郭正域闡發了一段議論,說道:“今縉紳先生冠其子弟,不備禮,不卜賓,況齊民乎?載在令甲,鮮有能行之者,蓋禮之廢久矣。”[7]這段話很好地體現了包括冠禮在內的禮儀儀式發展趨勢。假使冠禮仍按照《儀禮》中的規定,不隨著社會發展加以變通,那么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僵化、失去生命力。
而改良后的冠禮在維持生命力的同時,也以家庭禮儀的形式塑造著社會。冠禮儀式的改變不僅使衰落的禮制文化在家庭中得以延續,而且加強親族聯系,強調家族本位等觀念,展現了宋明之后重視構建親族內部凝聚力的思想演變潮流。
注釋:
[1]戴龐海:《冠禮研究文獻綜述》,《河南圖書館學刊》2006年第26卷第4期,第110-113頁。冠禮研究成果,如楊寬《“冠禮”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彭林:《士冠禮的禮法和禮義》,載《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錢玄:《三禮通論》,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2]賈公彥等:《〈儀禮〉疏注》卷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2頁。
[3]朱熹:《朱子家禮》卷第二《冠禮》,《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91頁。
[4]朱熹:《朱子家禮》卷第二《冠禮》,《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89頁。
[5]朱熹:《朱子家禮》卷第二《冠禮》,《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89頁。
[6]朱熹:《朱子家禮》卷第二《冠禮》,《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89頁。
[7](明)郭正域:《皇明典禮志》卷之八,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刻本,影印版,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