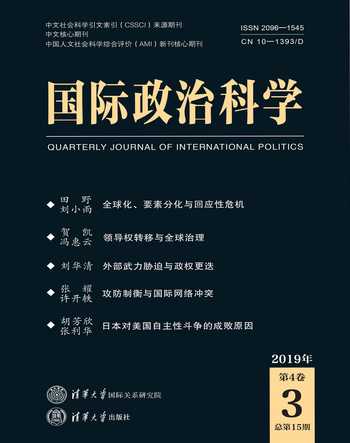領導權轉移與全球治理: 角色定位、制度制衡與亞投行
賀凱 馮惠云
【內容提要】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開始走向多邊制度并對現有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展現自身的吸引力。如果說中國崛起勢不可當,那么未來世界將會走向何處?其他國家又應做何準備?借鑒制度制衡理論與外交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論,本文提出“領導權轉移”的分析框架,以解釋全球治理中不同國家進行政策選擇的動態原因,并以亞投行作為案例進行考察。本文認為,中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采取了不同類型的制度制衡戰略,包括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間制衡,以便在亞投行的籌建過程中爭奪影響力和利益。在全球治理“領導權轉移”的過程中,國家具有領導者、挑戰者和追隨者三種不同的角色定位,這些角色定位會塑造國家對于不同制度制衡戰略的政策選擇。制度制衡是國家在全球治理未來轉型過程中的一種新型制衡行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崛起會比普遍預測的結果更加和平。
【關鍵詞】領導權轉移?制度制衡?角色理論?亞投行
一、 引?言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下簡稱亞投行)是當前世界政治中最熱門的話題之一。自中國2013年提出設立亞投行的構想以來,亞投行的發展就充滿了質疑、驚喜和活力。亞投行正式成立于2015年3月,其創始成員有57個國家,其中包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澳大利亞和韓國等發達國家。2016年8月31日,加拿大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成為首個尋求亞投行成員資格的北美國家。但迄今為止,美國和日本依然拒絕加入亞投行。
對于決策者和學者而言,亞投行的案例既有政策相關性,也有學術重要性。Rebecca Liao, “Out of the Bretton Woods: How the AIIB is Different,” Foreign Affairs, 27 June, 2015; Phillip Y.Lipscy, “Who's Afraid of the AIIB: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upport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oreign Affairs, 7 May, 2015; Helmut Reisen, “Will the AIIB and the NDB Help Reform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ing?” Global Policy, Vol.6, No.3, 2015, pp.297-304; Xiao Ren, “China as an Institution-Builder: the Case of the AIIB,” The Pacific Review, Vol.29, No.3, 2016, pp.435-442; Mike Callaghan and Paul Hubbar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Multilateralism on the Silk Road,”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9, No.2, 2016, pp.116-139; Gregory T.Chin,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Prospects,”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22, No.1, 2016, pp.11-25; Silvia Menegazzi,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the Case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5, No.2, 2017, pp.229-242; Yu W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oining the AIIB,”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2, 2018, pp.105-130; Jeffrey D.Wils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rom a Revisionist to Status-seeking Agend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9, No.1, 2019, pp.147-176.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提出設立亞投行的構想意味著中國正式開始挑戰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以及戰后國際秩序。Cary Huang, “China-led Asian Bank Challenges US Dominance of Global Econom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1 April, 2015; Daniel McDowell, “New Order: China's Challeng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Review, Feature Report, 14 April, 2015; Stephen Roach, “China's Global Governance Challenge,” YaleGlobal Online, 6 June, 2015; Ming Wa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如果說中國崛起勢不可當,那么亞投行就可以被視為對中國在未來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中潛在領導權的首次檢驗。中國在亞投行的表現及其對美國在世界政治中霸權地位的影響,也會吸引各國決策者的關注。
從各國對亞投行的不同反應和政策選擇角度考慮,亞投行為學者們提供了幾個有趣的研究問題。首先,為什么中國當初要發起設立亞投行的倡議?如果中國希望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挑戰美國,那么中國為什么要向所有國家開放亞投行,使得美國也有資格加入?其次,為什么美國拒絕加入亞投行,并且試圖勸阻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及其歐洲盟國加入?最后,為什么英國、澳大利亞、韓國等國選擇加入亞投行,而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拒絕加入?
關于亞投行的成立,學界目前存在兩種觀點:一部分學者提出了多種不同版本的“美國失誤論”,而其他學者則關注亞投行中代表“中國勝利”的要素。關于美國在亞投行中的失敗,最盛行的論點可以追溯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額改革。外界普遍認為,美國國會的阻撓導致IMF改革失敗,這是中國決定創建亞投行的一個主要原因。參見:Anna Yukhananov, “US Congress Will Not Pass IMF Reforms This Year,” Reuters, 10 December, 2014; Daniel Drezner, “Anatomy of a Whole-of-Government Foreign Policy Failure,” The Washington Post, 27 March, 2015.美國政府對亞投行犯下的另一個錯誤是一開始就堅決反對設立亞投行的構想。盡管美國沒有公開承認,但正如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所言:“美國反對亞投行只是因為它是中國的倡議,僅此而已。”Stephen Roach et al., “Washington's Big China Screw-up,” Foreign Policy, 26 March, 2015.這種態度無意中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聲譽和合法性。例如,雖然美國對亞投行持批評態度,但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金墉(Jim Yong Kim)卻在2015年初公開支持亞投行,稱“貧困才是真正的敵人,而不是希望幫助解決貧困的新參與者(亞投行)”參見:Lean Alfred Santos, “Jim Kim: Poverty, Not AIIB or the BRICS Bank, is the Enemy,” April 8, 2015, https://www.devex.com/news/jim-kim-poverty-not-aiib-or-the-brics-bank-is-the-enemy-85880.。金墉此舉將美國置于一種尷尬的境地,使得美國對世界銀行的實際控制遭到質疑。最后,同樣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在亞投行問題上向其他國家尤其是其盟友施壓,這被視為不明智甚至“無禮”的舉措。Jonathan Pollack, “Joining the Club: How Will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 to AIIB's Expanding Membership?” Brookings, 17 March,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3/17/joining-the-club-how-will-the-united-states-respond-to-aiibs-expanding-membership/.正如美國前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后來承認的那樣:“我們(美國)不應該這樣做。”David R.Sands, “Democratic Titans Say Obama ‘Screwed Up’ and Gave Rise to China's New Bank,” The Washington Times, 1 April, 2015,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5/apr/1/efforts-to-head-off-china-development-bank-called-/.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亞投行的成功不是由美國的政策失誤而是中國在外交上積極進取的成果。首先,亞投行倡議填補了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空缺。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以下簡稱亞開行)2009年的一項估計,2010年至2020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融資缺口約為8萬億美元,而亞開行和世界銀行每年為亞洲地區提供的基礎設施資金僅為約200億美元。“Why China is Creating a New ‘World Bank’ for Asia,” Economist, 11 November, 2014,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conomist-explains/2014/11/eco nomist-explains-6.在一定程度上,亞投行倡議旨在彌補這一融資缺口。中國的第二個成功之處在于其對亞投行的包容性制度設計。盡管亞投行以亞洲的名義創建,但任何國家都有資格加入。這種包容性的制度設計幫助中國緩解了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的疑慮。中國在亞投行取得的另一個顯著成果,就是借助高超的外交技巧贏得了英國的支持。英國可以被視為西方世界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因為其他西方國家很快也紛紛效仿英國而加入了亞投行。換句話說,中國對英國的吸引力造就了中國在亞投行的外交成功。
盡管“美國失誤論”和“中國勝利論”都揭示了關于亞投行創建動力的一些事實,但它們的分析存在兩個弱點。第一,現有的兩種觀點都建立在有缺陷的假定之上。例如,“美國失誤論”假定,美國應該接受中國的亞投行倡議,或者至少不應該試圖壓制它。Zachary Keck, “Why the US is Trying to Squash China's New Development Bank,” The Diplomat, 10 October, 2014.而“中國勝利論”則假定,中國通過亞投行提供了任何國家都無法拒絕的公共產品。但是,為什么美國應該接受亞投行?對美國來說,拒絕亞投行是一個確鑿的外交錯誤,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政策選擇?關于這些問題,我們無從知曉其答案。而對中國來說,亞投行確實在亞洲亟需的基礎設施發展融資方面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發展空間,但這種根植于公共利益的利他主義顯然不是中國創建亞投行的全部原因。此外,中國將如何利用亞投行或其他制度挑戰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還不得而知。
第二,現有的兩種觀點都聚焦于美國和中國,沒有對其他國家不同的政策選擇作出解釋。例如,盡管面臨美國的壓力,但澳大利亞和韓國還是決定加入亞投行。與之相反,日本則選擇與美國保持相同的立場。這三個國家都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由此產生了一個仍待回答的問題:為什么這些國家對亞投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除此之外,為什么英國和其他歐洲大國在亞投行問題上似乎比澳大利亞和韓國更容易作出選擇?可以肯定的是,亞投行不會是中國對美國發起的最后一個制度性挑戰,在這一背景下,其他國家如何應對類似的情況將直接影響中美兩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競爭結果。以上分析表明,亞投行的成立是一個與體系轉型相關的問題,僅僅指責美國的失誤或贊揚中國的成功顯然無法為此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
本文試圖借助一個新的理論視角——“領導權轉移”(leadership transition)理論——來回答上述問題。通過結合制度制衡理論和外交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論,本文指出,亞投行代表了全球經濟治理中“領導權轉移”的動態互動,美國和中國為領導權而展開競爭,其他國家則不得不在兩大國之間選擇站位。基于其在“領導權轉移”博弈中不同的角色身份,各國選擇不同類型的制度制衡戰略,包括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間制衡,從而在全球治理體系不斷演變和轉型的過程中尋求自己的影響力和利益。
特別是,本文認為,美國作為現有體系的領導者,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領導權,因此更有可能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戰略,以此來反制現有制度面臨的潛在挑戰。而作為挑戰者,中國在體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日益提升,中國需要為此尋求國際社會的承認以及自身的合法性,這也構成了中國更有可能選擇包容性制度制衡戰略的原因,這一戰略要求中國邀請包括美國在內的盡可能多的支持者加入其創建的制度。至于在“領導權轉移”博弈中扮演追隨者的國家,它們對平衡特定利益的考量會塑造其政策選擇。具體來說,如果一國在新制度中感知到具體的利益,它將更有可能“為利益而追隨”——加入由挑戰者創建的新制度,以獲得舊的治理制度無法提供的利益。然而,如果一國無法從新制度中感知到具體的利益,那么它更有可能選擇“為穩定(或安全)而追隨”——與領導者保持相同的立場,以維持體系的現狀。關于“為利益而追隨”,參見: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72-107.關于“為安全而追隨”,參見: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本文由三部分組成。首先,本文將制度制衡理論與角色理論進行結合,進而提出“領導權轉移”理論,以闡明不同國家在全球治理的動態轉型中如何運用不同的制度戰略。其次,本文通過考察美國、中國、英國和日本對亞投行的不同政策選擇來檢驗“領導權轉移”模型的解釋力。在結論中,本文提出,亞投行的成立是中美兩國在全球金融治理多邊制度框架下的一場制度性權力博弈。盡管現在預測中美博弈和制度轉型的最終結果還為時過早,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通過多邊制度而實現的崛起會比人們普遍預期的結果更加和平。
二、 “領導權轉移”理論: 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領導權轉移”模型——來解釋亞投行的發展動力以及中美兩國在未來全球治理領域的競爭。需要說明的是,“全球治理”在國際關系領域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本文采納托馬斯·韋斯(Thomas G.Weiss)和拉梅什·塔庫爾(Ramesh Thakur)的定義,將“全球治理問題”(the problématique of global governance)界定為“增進有力應對跨境(尤其是全球性)集體問題出現的政府間制度的發展”Thomas G.Weiss and Ramesh Thaku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UN: An Unfinished Journe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韋斯和塔庫爾進一步將聯合國事務分為安全事務和經濟事務兩大領域,即全球安全治理和全球經濟治理。本文遵循這一路徑,認為在考慮全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內的領導權轉移時,應該區分不同的問題領域。換句話說,包括美國在內,任何國家都不能在全球治理的所有問題領域中發揮主導作用。因此,在討論全球治理中可能出現的“領導權轉移”時,我們需要確定全球治理涉及的問題領域。
本文提出的“領導權轉移”理論借鑒了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分析領域的制度制衡理論和角色理論。Kai He, “Role Conceptions, Order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Pacific: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2, No.2, 2018, pp.92-109.制度制衡理論認為,國家可以利用不同的制度戰略在國際體系中追求權力和影響力等現實利益。關于制度制衡,參見: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4, No.3, 2008, pp.489-518;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Routledge, 2009); Kai He, “Facing the Challenges: ASEAN's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na's Rise,” Issues & Studies, Vol.50, No.3, 2014, pp.137-168; Kai He, “Contested Regional Orders and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2, No.2, 2015, pp.208-222; Huiyun Feng and Kai He, “China's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1, No.4, 2017, pp.23-49.各國對亞投行的不同政策選擇歸因于它們在全球金融治理領域實施不同的制度制衡戰略。另一方面,角色理論則探討了個體國家的角色身份如何塑造其對于不同制度制衡戰略的政策選擇。Kalevi J.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3, 1970, pp.233-309; Stephen G.Walker, e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ameron G.Thies,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in Robert Denmark, ed.,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Oxford: Blackwell, 2010).
制度制衡理論包括三類: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間制衡。參見: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Pacific.也可參見:Seungjoo Le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the Politics of Mega-FTAs in East Asia,” Asian Survey, Vol.56, No.6, 2016, pp.1055-1076.包容性制度制衡是指將制衡的目標國家納入多邊制度的戰略。這個多邊制度的規則及規范將被用來約束和塑造目標國家的行為。東盟地區論壇(ARF)是包容性制度制衡的一個成功案例。20世紀90年代,東盟國家利用ARF中關于多邊主義和合作安全的規范和規則,來約束中國的行為。
排他性制度制衡是指從現有制度中將制衡目標國排除在外的戰略選擇。這一制度的凝聚力和合作會對制衡目標國施加壓力或抵消目標國所帶來的威脅。排他性制度制衡的一個案例是由美國主導的地區貿易集團,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雖然TPP宣稱對所有國家開放,但其高準入標準(尤其是在勞工保護和對國有企業的限制方面)實際上從一開始就阻止了中國的加入。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正在對TPP實施觀望戰略。然而,即使在美國于2017年退出TPP之后,盡管國內存在一批支持者,中國也沒有加入TPP-11。對中國而言,TPP是美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對中國進行制度制衡的一個案例,借助這一制度,美國可以利用TPP國家之間的團結和凝聚力來疏遠中國,并進一步削弱其在該地區內的影響力。
排他性制度制衡的另一個典型案例是上海合作組織(SCO)。作為SCO的主要發起者,中國在SCO中享有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然而,為了抗衡中國在SCO的影響力,俄羅斯堅持邀請印度加入。這是俄羅斯實施的一項針對中國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戰略,因為印度可以與俄羅斯合作,以限制中國在SCO內的行為。2017年,俄羅斯的制衡取得了成功,印度最終加入了SCO。而中國方面同時也邀請巴基斯坦加入SCO,以抵消印度在SCO內對中國施加的制度性壓力。
制度間制衡是排他性制度制衡的擴展形式。當一國被一個特定的制度排斥在外時,它可以支持另一個或創建一個類似的制度,以抵消將其排斥在外的制度所帶來的壓力。例如,面對TPP的壓力,中國支持東盟創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以應對TPP的壓力。此外,在2014年于中國舉辦的APEC(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中國提倡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協定(FTAAP)。FTAAP提案也可被視為中國對美國主導的TPP實施的制度間制衡,FTAPP的成功可以減少TPP對中國的負面影響。
制度制衡理論為解釋各國對亞投行的行為動力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但它無法解釋為什么各國對亞投行選擇不同的制度制衡戰略。例如,為什么美國拒絕亞投行,而英國卻支持?此外,加入的國家越多顯然越會削弱中國對亞投行的影響力,那么為什么中國還要選擇包容性的制度設計并邀請所有國家加入?本文將角色理論與制度制衡理論相結合,以解釋國家如何應對全球治理中潛在的“領導權轉移”。
角色理論是一個包含多種理論視角的研究綱領,它對“角色”概念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有著相似的看法。“角色”這一概念是從戲劇中借用而來的隱喻。角色理論家認為,每個人都扮演著特定的社會角色,社會實際是由不同的個人角色組成的網絡。角色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被引入外交政策分析和國際關系領域。角色理論對外交政策分析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分析框架,能夠將不同的理論視角整合到外交政策研究中。Marijke Breuning, “Role Theory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ebastian Harnisch, Cornelia Frank and Hanns W.Maull, eds., Role Theory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ual Challenges and Political Promise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16-35; Stephen G.Walker, Rol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Architecture of British Appeasement Decisions: Symbolic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Sebastian Harnisch,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8, No.1, 2012, pp.47-69; Kai He and Stephen Walker, “Role Bargaining Strategies for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8, No.4, 2015, pp.371-388.正如蒂斯(Cameron G.Thies)所言,盡管角色理論的理論價值在國際關系領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略與質疑,但它確實具有將外交政策分析領域內的不同層次聯系起來、將國際關系領域的施動者與結構聯系起來的潛力。Cameron G.Thies,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in Robert Denmark, ed.,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Oxford: Blackwell, 2010).
角色理論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國家的角色身份塑造了它的政策選擇。換句話說,一國如何看待它在國際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將影響其政策。例如,蘇聯自認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因此在冷戰期間介入了東歐的國內事務。與此類似,美國在冷戰期間將自己視為全球反共產主義的領導者,因此挑起了越南戰爭,以防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地區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式的擴散。
以亞投行為案例,本文提出了基于制度制衡理論和角色理論的“領導權轉移”理論。由于外界普遍認為亞投行的成立是對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制度性挑戰,本文由此認為,亞投行的創建代表著全球治理體系潛在的“領導權轉移”,但這個過程最終是否會成功仍然無法確定。正如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轉移一樣,當一個國家創建一個新制度,并且該制度被主導國視為對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威脅時,將會引發全球治理體系“領導權轉移”的進程。此外,與霸權國和崛起國之間的權力轉移類似,全球治理體系的“領導權轉移”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因此,“領導權轉移”模型側重于考察轉移期間不同類型國家的制度戰略選擇。根據角色理論,可以將“領導權轉移”過程中的角色分為三類:領導者、挑戰者和追隨者。權力轉移理論預測崛起國和霸權國在沖突中會采取軍事制衡的手段。與此不同,全球治理體系的“領導權轉移”進程將通過制度制衡的方式進行,包括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間制衡。參見:Kai He, “Role Conceptions, Order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Pacific: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2, No.2, 2018, pp.92-109.
所有國家在參與全球治理制度轉型的過程時,都需要計算成本和收益。對于體系主導國來說,其權威與合法性將面臨來自于挑戰國最嚴峻的挑戰。因此,對于體系主導國來說,最大限度地減少競爭對手對現有體系的制度性影響是其合理選擇。而實現這一目標最簡單及最好的方法是一開始就拒絕承認新制度的合法性并貶低其價值。因此,主張拒絕認可和加入新制度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成為主導國一種合理的政策回應。此外,主導國還需要勸阻其他國家加入新制度,因為新制度的成員越少,對體系的影響力就越弱。
對于挑戰國來說,其直接目標是利用一個新制度來增強其在體系中的權力和價值。從長遠來看,新制度可以成為挑戰者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接管主導地位的制度基礎。然而,挑戰者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將是如何讓新制度發揮作用。換句話說,挑戰者必須向其他國家證明,它創建的新制度能夠提供現有體系無法提供的額外收益。為了做到這一點,挑戰者必須放棄一些短期經濟收益,才能讓新制度運轉起來。包容性制度制衡是挑戰國在當前體系下爭取其他國家支持的合理政策選擇。雖然新制度的成員越多,挑戰國受到的限制可能也越多;但是,新制度的成功將有利于挑戰國的長期目標,即在未來全球治理體系中確立新的主導地位。
對于其他國家來說,它們的角色是在主導國和挑戰國的制度競爭中充當追隨者。它們必須在主導國和挑戰國之間作出選擇。具體來說,這些國家可以追隨主導國,從而與新制度保持距離;也可以支持挑戰國,進而加入新制度。如上所述,為了吸引追隨者,挑戰國需要提供主導國無法提供的額外利益。因此,如果追隨國從新制度中感知到一些具體的利益,它們將選擇加入新制度來支持挑戰國。但是,如果追隨國沒有發現新制度帶來的任何好處,它們就會追隨主導國,因為維持現有體系會帶來更高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通過結合角色理論和制度制衡理論,“領導權轉移”理論提出了以下三個假設。
假設1: 如果一國認為自己在全球治理的某個領域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那么它更有可能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或制度間制衡戰略,也可能同時采取這兩種制衡戰略,以削弱體系中其他國家創建的任何新制度的影響力和價值。
假設2: 如果一國認為自己在全球治理的某個領域扮演著挑戰者的角色,那么它更有可能采取一種包容性制度制衡的戰略,以此爭取其他國家的支持,確保它所創建的制度取得成功。
假設3: 如果一國認為自己在全球治理的某個領域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那么它可以對新制度采取包容性或排他性制度制衡戰略。如果該國感知到某些具體的利益,它更有可能支持挑戰者的新制度。否則,它將追隨領導者,從而與新制度保持距離。
有兩點需要注意。首先,“領導權轉移”理論是一個關于全球治理特定問題的模型。本文認為,對全球治理的不同問題領域進行分類具有重要的意義。
全球治理既包括權利(權力),也包括責任。正如前文所述,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全球治理的所有問題領域都成為領導者或挑戰者。例如,自二戰以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貿易和金融體系)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但在氣候變化、文化交流等其他問題上,美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成為領導者。因此,“領導權轉移”模型是一個特定問題的模型,適用于領導者、挑戰者和追隨者之間存在權力變化的任何全球治理領域。本文對亞投行進行的案例分析將作為這一模型在全球金融治理領域的實證檢驗。此外,它還將為全球治理其他領域的“領導權轉移”提供一些啟示。
其次,在經驗檢驗層面,本文面臨搜集用于案例分析的直接證據的難題。亞投行的籌建發生在2013—2015年,目前許多相關的官方文件仍然是機密文件。由于事件的敏感性,采訪任何直接參與亞投行的官員也很困難。因此,本文不得不依靠二手資料,如報紙報道,來對不同國家對亞投行的政策行為進行初步研究。因此,這項研究可以被視為一種理論驅動的合理性探索,它將在未來啟發更多的研究和假設檢驗。
本文采取一致性檢驗來考察這些假設的有效性。在一致性檢驗中,本文探討了四個國家即美國、中國、英國和日本對亞投行的政策選擇。在每個案例中,本文都會考察這些國家的角色身份與它們對亞投行的政策選擇之間的關系。如果一國的角色身份與假設中提出的政策選擇趨同,那么本文的模型就通過了一致性檢驗。如果沒有,那么本文的假設就被證偽,需要探索其他變量來解釋這種不同的結果。
三、 亞投行中的制衡博弈
根據角色理論,確定一個國家的角色需要經過兩個步驟。第一,國家或國家領導人需要經歷一個自我角色識別過程,以便指定國家將扮演的角色。第二,這種自我的角色認同必須得到外部世界的認可。如果外部世界認可國家自我認同的角色,那么該國就完成了其角色定位的過程。如果外部世界拒絕國家自我認同的角色,該國就需要與外部世界重新協商其角色。自我角色定位與角色認可之間的差異有時會導致政策的失敗以及國家與外部世界的對抗。Cameron G.Thie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vs.Israel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Can Role Theory Integrate IR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8, No.1, 2012, pp.25-46.
(一) 美國的領導者角色與排他性制度制衡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將自己視為國際體系的領導者。如上所述,美國的主導地位建立在其軍事實力以及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之上。在201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美國明確表示:“美國強大而持續的領導作用,對于一個促進全球安全與繁榮以及各國人民尊嚴和人權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言必不可少。問題從來不在于美國是否應該領導,而在于我們如何領導。”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15).在這份長達35頁的文件中,“領導權”被強調了15次。換句話說,美國并不掩飾其世界領導者的地位。
作為全球治理體系的領導者,美國的自我角色定位也得到了外部世界的認可。例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于2016年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明確指出:“美國可能會被國內政治攪得很亂,但它在貿易和安全方面的主導地位是不可或缺的……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無可替代。”William McGurn, “Lee Hsien Loong'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1 March, 2016, http://www.wsj.com/articles/lee-hsien-loongs-american-exceptionalism-1459464855.更重要的是,中國也公開認可了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2014年底,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發表公開講話稱:“引領世界的是美國。對此,我們有清醒的認識……中國既沒有想法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領導者地位。”Wang Yang, “The road to Sino-US economic partners is getting wider and wider(中美經濟伙伴之路越走越寬廣),”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412/201412 00840915.shtml
根據“領導權轉移”理論,美國作為全球金融治理的領導者,更有可能對中國的亞投行倡議選擇一種排他性制度制衡戰略。事實上,美國對亞投行采取了“三不”政策。首先,“不認可”亞投行的倡議。美國認為亞投行是多余的,因為當前體系中已經有世界銀行、IMF和亞開行。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雖然白宮沒有公開批評亞投行,但美國政府實際上將亞投行視為“中國創建的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進行競爭的工具”。Peter Ford, “A Newly Modest China? Official's Reassurances Raise Eyebrows in U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7 January, 2015.
其次,“不加入”亞投行。盡管中國努力游說,許多美國學者和政策顧問也主張加入亞投行,但美國政府仍拒絕加入亞投行。據《紐約時報》報道,奧巴馬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顧問埃文·梅代羅斯(Evan Medeiros)在一次會面中告訴中國代表團:“我不會買你做的蛋糕。”這支中國代表團由金立群領導,金立群是后來的亞投行行長,并且在2014年計劃游說美國接受亞投行的構想。據報道,金立群回答:“隨時歡迎你來廚房幫忙烤蛋糕。”Jane Ferlez, “China Creates a World Bank of Its Own, and the US Balks,” The New York Times, 4 December, 2015.值得一提的是,埃文·梅代羅斯對他與金立群談話的報道質疑。然而,描述這段對話的原始消息來源堅持自己的說法。這里,真正的問題不是“蛋糕”,而是“廚房”。美國不愿進入廚房,因為它在那里沒有發揮主導作用。
再次,美國試圖說服其盟國“不加入”亞投行。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主管國際經濟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卡羅琳·阿特金森(Caroline Atkinson)是現有金融治理體系的強力捍衛者,也是試圖影響亞投行成員構成的主要參與者。在一系列高級別會議上,阿特金森和她的同事們試圖制定針對亞投行的“遏制戰略”,特別是,“美國勸阻澳大利亞和韓國不要簽署協定,它給七國集團成員國的建議是,美國需要團結的統一戰線”Jane Ferlez, “China Creates a World Bank of Its Own, and the US Balks,” The New York Times, 4 December, 2015.。通過“三不”政策,美國的目標是疏遠、削弱亞投行,甚至將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價值去合法化。因為如果只有亞洲小國加入,那么亞投行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以及中國對當前體系的挑戰將會大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這并不是美國第一次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面臨制度性挑戰。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提議建立一個名為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EC)的自由貿易區,以鼓勵東盟國家與日本、中國和韓國這三個東亞國家之間的貿易和經濟合作。由于美國強烈反對EAEC的構想,因此日本拒絕加入,這導致EAEC構想在萌芽階段就夭折了。Takashi Terada,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 3,” The Pacific Review, Vol.16, No.2, 2003, pp.251-277. 1997—1998年經濟危機后,日本提議建立名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區域貨幣基金組織,以作為對IMF在危機期間沒有充分幫助亞洲國家的制度性反應。但由于美國的強烈反對,日本最終放棄了建立AMF的構想。Phillip Y.Lipscy, “Japan's Asian Monetary Fund Proposal,”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3, No.1, 2003, pp.93-104; Yong Wook Lee, “Japan and the Asian Monetary Fund: An Identity-Intention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0, No.2, 2006, pp.339-366.
EAEC和AMF的案例進一步證明,在面臨全球治理體系的制度性挑戰時,“領導權轉移”理論針對主導國的政策選擇作出的推斷符合現實情形。EAEC和AMF都屬于全球貿易和金融治理領域,美國自二戰以來一直被定位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對EAEC和AMF這些僅面向亞洲的制度建設采取了反對的政策。因為不論馬來西亞或日本是否將自己在EAEC或AMF中的角色定位為美國的挑戰者,在美國決策者看來,EAEC和AMF的提議都嚴重威脅了美國在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這里,重點在于威脅的級別和性質,而不是威脅的來源。特別是,馬來西亞的EAEC倡議是一個將美國排除在外的亞洲區域貿易集團,它將嚴重威脅到美國在該地區倡導的自由貿易體系,比如削弱APEC的作用。而日本的AMF提議則反映了亞洲國家對IMF和世界銀行的不滿,因為它們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沒有為亞洲經濟體提供有效的援助。AMF潛在的成功會嚴重損害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瓦解,因此這句話存疑。——譯者注,尤其是IMF和世界銀行的合法性。因此,根據“領導權轉移”模型,如果新制度可能對美國在全球治理特定領域的主導地位構成挑戰,那么美國不參與并且反對新制度的政策選擇就是合理的。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會一直反對新成立的金融制度或僅面向亞洲的制度。20世紀60年代,美國支持并加入了亞開行。在冷戰結束后不久,美國也同樣加入了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參見:Steven Weber,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1, 1994, pp.1-38.這是因為,美國決策者認為,亞開行和EBRD都不會對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構成威脅。相反,EBRD和亞開行在成立之初都加強了美國的主導作用,并為美國的戰略利益服務。美國最初不愿支持日本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亞開行。然而,由于越南戰爭的戰略需要,美國改變了對亞開行的態度。關于美國對亞開行的政策,參見:Nitish Dutt, “The US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Origins, Structure and Lending Oper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31, No.2, 2001, pp.241-261.
SCO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制度,它僅面向亞洲地區,最初被稱為“上海五國”,是一項針對中國和中亞四個鄰國的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由于SCO不在美國的全球治理范圍內,美國雖然可能不喜歡其反西方的傾向,但也無力提出反對。此外,一些非東亞地區的金融制度,例如伊斯蘭開發銀行(the Islamic Development Bank)或安第斯基金(Andean Fund),則聚焦于某些伊斯蘭國家或某一地理區域(安第斯基金面向拉丁美洲)。這些制度帶來的潛在“威脅”(如果有的話)還不足以削弱美國在IMF和世界銀行等全球經濟治理制度中的主導地位,因此美國沒有給予它們與EAEC和AMF同等的關注。
公平地說,美國一開始就拒絕亞投行并不一定是政策上的失敗,因為在“領導權轉移”的情況下,主導國通常都會進行排他性制度制衡。這種戰略在之前的EAEC和AMF案例中都發揮了作用。實際上,在亞投行的案例中,美國排他性制度制衡的失敗并非源于戰略上的失誤,而是因為這次的對手與以往不同。
需要澄清的是,美國自我定位的領導者角色并不總能推導出排他性制度制衡戰略的政策選擇。如前所述,二戰結束后,美國首先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那時美國的戰略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與此相同,美國也曾在2000年實施包容性制度制衡,鼓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通過包容性制度制衡戰略,美國有意利用WTO的規則和規范來社會化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行為選擇。然而,上述案例并不能駁斥“領導權轉移”模型,因為本文的模型只適用于全球治理中潛在的“領導權轉移”。換句話說,該模型并不總能解釋所有的制度戰略。在美國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并允許中國加入WTO之時,全球治理體系并沒有發生領導權轉移。相反,美國在全球治理領域是毫無疑問的領導者,因此美國將其他國家納入其創建和主導的制度是合理的。然而,當其領導權受到挑戰時,正如“領導權轉移”模型所解釋的那樣,美國將選擇不同的制度戰略來應對這些威脅。
(二) 中國的挑戰者角色與包容性制度制衡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被視為現有國際體系的“威脅”。中國領導人一直在努力讓世界相信,中國的崛起將是和平的。為了消除外界的疑慮,中國政府在2004年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堅持“和平發展”。Bonnie S.Glaser and Evan S.Medeiros, “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90, 2007, pp.291-310.然而,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中國是一個后來者,并且被認為過于弱小,無法對當前體系構成威脅。關于中國參與現有國際制度的主要論述是如何使中國與西方主流的規則和規范相適應。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被動地位開始發生變化,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唯一動力。在2009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未指名地嚴厲批評了一些國家“不適宜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長期低儲蓄高消費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結合當時的國際環境,溫家寶總理所指的國家顯然包括美國。Andrew Edgecliffe-Johnson et al., “Wen and Putin Lecture Western Leaders: Chinese Premier Attacks ‘Blind Pursuit of Profit’,” Financial Times, 29 January, 2009.在俄羅斯的呼應下,中國開始要求在新的經濟秩序中發揮“更大的作用”。2009年3月,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公開呼吁尋找能夠替代美元的世界貨幣,并提出創造“與個別國家脫節并能長期保持穩定的一種國際儲備貨幣”。顯然,周小川的言論表明中國試圖調整當前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Zhou Xiaochuan, “Refor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China Daily, 25 March,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3/25/content_7612847.htmHYPERLINK"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3/25/content_7612847.htm".
自習近平于2012年底執政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正朝著一個新的方向發展,這反映在中國近年來“奮發有為”的政策偏好上。在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中,美國的角色是領導者和霸權國,中國的角色則逐漸成為美國領導的體系的挑戰者。例如,在2014年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上,習近平提倡:“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Xi Jinping, “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 for New Progress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Remarks at the Fourth Summit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21 May, 2014.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159951.shtml.習近平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亞洲各國拒絕美國等外部勢力干涉地區事務的訴求。在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進一步提出建立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對亞洲新安全和經濟秩序的愿景。正如一些評論人士所言,習近平對命運共同體的呼吁代表著“中國開始改變近幾十年來主要在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內行動的狀態”Charles Hutzler, “China Banks on Sharing Wealth to Shape New Asian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9 March, 2015.。
中國在當前國際體系中所扮演的挑戰者角色也得到了外界的證實。例如,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在2015年的國情咨文演講中指出,中國是美國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挑戰者,他表示:“中國希望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制定規則……我們為什么會讓這發生?我們才應該是這些規則的制定者。我們應當公平競爭。”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Obama's Remarks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0, 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20/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january-20-2015.美國兩位主要政策分析人士更是斷言“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長期戰略競爭非常激烈”,中國是“最有能力支配亞洲大陸的國家,因此破壞了美國傳統的地緣政治目標,即確保這一地區不受霸權控制”。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5), p.5.
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也將中國視為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挑戰者。中國和俄羅斯每年都在官方聲明中呼吁世界多極化和國際新秩序。在俄羅斯領導人看來,中國至少會是俄羅斯挑戰美國的伙伴。2015年4月,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也加入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團隊,呼吁建立一個“向新興國家開放、不受任何特定國家集團支配”的全球經濟新秩序。Zakir Hussain, “Indonesian President Jokowi Calls for New, more Equal Global Economic Order,” The Straits Times, 23 April, 2015.盡管佐科沒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中國或美國,但大家都明白,印尼支持中國在未來全球治理轉型過程中挑戰美國。作為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的挑戰者,中國的角色定位得到了外部世界的進一步認可。
根據“領導權轉移”理論,中國更有可能選擇包容性制度制衡來挑戰當前的霸權國。中國的包容性制度戰略由兩個步驟組成。第一,作為挑戰者(也是后來者),中國和其他新興大國將努力在現有制度中爭取更多話語權。但是,它們的努力不一定會得到當前霸權國或主導國的尊重。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新興經濟體試圖增加IMF投票權所面臨的困境。
第二,如果挑戰者的需求在現有制度下不能得到滿足,那么挑戰國將創建一個新制度來挑戰現有制度的合法性,并挑戰霸權國在全球治理特定領域的領導者角色。正如假設2所表明的,為了提高新制度的合法性和成功率,挑戰國更有可能創建一個新制度,并使其容納包括當前霸權國在內的盡可能多的成員,以便在全球治理的特定領域建立自己的領導權。
亞投行是包容性制度制衡戰略運行第二步驟的經典案例。一方面,中國設計了一個包容性的多邊制度來吸引發展中國家和發達經濟體的支持。如前所述,亞投行彌補了亞洲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發展的缺口。另一方面,中國并沒有將亞投行成員限制為亞洲國家。相反,中國還積極邀請歐洲國家和富裕的阿拉伯國家加入,這主要基于兩點考慮。
第一,多邊設計可以幫助中國避免低效的融資實踐,中國曾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一些基礎設施項目的雙邊援助和貸款中經歷過這種狀況。Injoo Sohn, “AIIB: A Plank in China's Hedging Strategy,” Brookings East Asia Commentary Series, May 11,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aiib-a-plank-in-chinas-hedging-strategy.加入的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越多,越能提升亞投行和中國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影響力和重要性。中國甚至努力邀請日本加入亞投行,因為日本的加入有利于提升亞投行的信用評級。而按照亞投行的制度設計,日本如果加入,便能獲得一個副行長的職位。“The AIIB Storm: Japan Lost Its First Vice President Position,” Nikkei News,?20 April, 2015.換句話說,中國的包容性制度設計不僅是名義上的,而且也是實質上的。
第二,除了包容性之外,制度制衡戰略的關鍵特征在于其制衡功能,中國可以利用制度的規則和規范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制衡在國際關系的研究中是一個軍事戰略領域的術語,原意是實現兩國軍事力量的平衡。在全球治理中,它是指國家在多邊制度中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約束他人行為而制定規則和規范的政策行為。在亞投行問題上,中國在制定制度的規則和規范時與其他成員國進行了原則性談判。一方面,中國同意與其他成員國就股權結構和決策過程等制度機制進行談判。另一方面,中國在設計亞投行時也堅守自己的原則。
據報道,考慮到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相對于其他成員國的規模,中國最初打算持有50%的亞投行股份。而在一些發達經濟體加入之后,中國同意減持其股份。最終,在2016年1月亞投行開業時,中國獲得了26.6%的投票權。盡管中國仍是亞投行事實上擁有否決權的最大股東,但中國堅持稱無意保留否決權。正如金立群行長所解釋的:“仍然有許多國家在等待加入,隨著新成員的加入,中國的投票權會相應下降。實際上,一票否決權會逐漸消失。”Jing Fu, “AIIB Chief Rules Out China Veto Power,” China Daily, 27 January, 2016,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01/27/content_23265846.htm.
經過與其他成員國為期兩年的談判,亞投行建立了一個關鍵的決策程序,引入了“固定的”特別多數原則,特別多數由2/3的成員組成,擁有3/4的投票權。這種“固定的”特別多數原則是亞投行與世界銀行的主要區別,因為沒有單個國家能夠改變亞投行的特別多數。這意味著中國無法做到美國在世界銀行通常所做的事情,并且在新成員加入導致投票權減少時,中國也不能通過增加特別多數來保持其否決權。換句話說,中國主動限制了自己在亞投行的影響力。金立群行長解釋說,中國這種自我約束行為背后的原因是,“通過集體協商和民主決議,中國可以贏得信譽并和各國建立互信關系”。Ibid.
但中國在治理結構上堅持自己的原則,主張設計一個“精益、清潔、綠色”(lean, clean and green)的亞投行。例如,亞投行秘書處計劃招募700名員工,這遠低于亞開行總部的2000名員工。世界銀行和亞開行有時會在不同國家設立辦事處,與此不同,亞投行只會指派專家和工作人員參與項目。這種做法不僅可以減少海外辦事處不必要的開支,而且可以避免總部和區域中心在決策方面的重復。
更重要的是,與世界銀行和亞開行不同,亞投行沒有一個常駐董事會來管理日常業務。按照大多數開發銀行的做法,常駐董事會是進行有效監督的必要機構。但中國認為,這會成為不必要的和多余的成本,并且會降低決策過程的效率。Robert M.Orr,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Conditional Collaboration?” American Ambassadors Review, 4 May, 2016, https://www.americanambassadors.org/publications/ambassadors-review/spring-2016/the-asian-development-bank-and-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conditional-collaboration.這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因為日本拒絕亞投行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這種缺乏常駐董事會的治理結構。盡管中國試圖說服日本加入亞投行,但并未改變自己在常駐董事會問題上的立場。由于亞投行于2016年初才開始運營,其真實效果仍然有待觀察。但從治理結構的角度來看,不設立常駐董事會的安排將有利于中國在與亞投行其他成員打交道時的制衡效果。
中國包容性制度制衡戰略的最后一個特點在于通過亞投行提供公共產品,進而與美國展開領導權競爭。約瑟夫·奈(Joseph Nye Jr.)認為,20世紀40年代出現的“美國世紀”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具備提供其他國家所需的全球公共產品的獨特能力。Joseph S.Nye Jr.,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5).因此,任何美國的挑戰者如果想要取代美國在體系中的角色,都需要具備同樣的能力。某種程度上,中國借助亞投行和其他多邊制度,已經與美國在提供公共產品上展開了競爭。
2014年8月,在訪問蒙古國期間,習近平發表演講,表示要在經濟發展方面為其他國家提供“搭便車”服務。習近平說:“中國愿意為包括蒙古國在內的周邊國家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Xi Jinping, “Watching and helping each other, creating a new era of Sino-Mongolian relations(守望相助,共創中蒙關系發展新時代),” Xinhua Daily, 22 August, 2014,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112195359.htm.習近平的聲明被視為對奧巴馬的直接回應,奧巴馬此前指責中國30年來在國際體系中扮演“搭便車”的角色。“Exclusive Interview: Obama on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14, http://www.nytimes.com/video/opinion/100000003048414/obama-on-the-world.html?playlistId=1194811622299.與美國對“搭便車”的不滿相反,中國接受了國際體系中的“搭便車”行為,并準備在未來為“搭便車者”提供公共產品。
例如,2013年10月,中國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倡議,涵蓋了亞洲、歐洲和非洲的許多經濟體。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復興一條從亞洲延伸到歐洲的古老貿易路線,加強世界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貿易和投資。它被視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二戰后,美國曾利用馬歇爾計劃為西歐重建提供資金。相比之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將比馬歇爾計劃的規模大得多,也更具雄心。Enda Curran, “China's Marshall Plan,” Bloomberg, 8 August, 2016.如果說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向西歐提供的公共產品,那么“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向全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計劃。
2014年12月,中國宣布設立400億美元的絲綢之路基金,以改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中國承諾為亞投行提供500億美元。此外,中國承諾認購金磚國家1000億美元應急儲備安排中的410億美元。應急儲備安排旨在向遭受金融壓力的金磚國家成員國提供緊急信貸,這與IMF的全球職能相同。亞洲國家之間類似的安排是清邁協議,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亞洲各國于2000年簽署了該協議。其中,中國向清邁協議貢獻了770億美元。盡管中國向應急儲備安排和清邁協議都貢獻了很大一部分資金,但它主動限制了自己的提款權。在清邁協議中,中國貢獻了770億美元,但只能借到400億美元。在應急儲備安排中,中國提供了410億美元,但只有200億美元的提款權。Daniel McDowell, “New Order: China's Challeng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Review, Feature Report, 14 April, 2015, p.8.然而,所有這些承諾都只是停留在紙面上,因為沒有任何國家使用過這些緊急資金。但這些金融貢獻和承諾至少表明,中國愿意像美國過去那樣,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公共產品。
(三) 制度制衡中的追隨者角色與利益平衡
與領導國和挑戰國不同,其他國家不需要確定自己的角色,它們默認自己為追隨國。但是,在“領導權轉移”的情況下,它們需要決定追隨何者,是當前的領導國還是挑戰國。追隨者的角色進一步劃分為領導者的追隨者或挑戰者的追隨者。正如在“領導權轉移”模型中提到的,如果一國感知到挑戰者和新制度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利益,它就會成為挑戰者的追隨者。否則,該國就會支持領導國以維持體系的現狀。
英國和日本都是美國緊密的軍事盟友和經濟伙伴。但是,它們對中國有著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戰略重點。盡管英國偶爾會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計劃和國防預算透明度表示擔憂,但它并不把中國視為安全威脅。然而,英國與中國的雙邊關系曾受到政治和人權問題的嚴重影響。英國外交部在對華政策中設立了許多模糊而不切實際的期望。例如,英國對華政策的目標之一就是幫助中國進行內部法律和政治改革。Kerry Brown, “The UK Shows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Clarify, in Joining AIIB,” Chatham House Commentary, 20 March, 2015.因此,通過批評中國的人權記錄和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英國企圖在應對中國事務的過程中扮演“講師”或“救世主”的角色。
自卡梅倫2013年對華商務訪問開始,英國對華政策就由財政部而非外交部主導。時任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強烈主張與中國建立緊密的經濟聯系。因此,英國開始將對中國的政策重點從政治和人權轉向投資和經濟合作。同時,由于國內選舉的壓力,卡梅倫也非常希望能夠借助中國的投資和貿易促進英國國內經濟的發展。因此,亞投行成了卡梅倫無法拒絕的一個有吸引力的商業提議。
英國決策者認識到,亞投行可以帶來許多具體的經濟利益。根據英國財政部發布的一份官方聲明,奧斯本稱亞投行“對英國和亞洲來說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機遇”,因為它能“在全球發展速度最快的市場為我們的企業提供工作和投資的最佳機會”。HM Treasury and Rt Hon George Osborne MP, “UK Intends to Become a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GOV.UK, 12 March, 201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nounces-plans-to-join-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首先,英國企業將在亞投行資助的亞洲大型基礎設施交易中獲得更多商機,甚至是優惠待遇。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不是唯一一個關心亞投行經濟效益的國家,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也希望從亞投行資助的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中“分一杯羹”,因為歐盟是建筑服務的主要出口方。Mikko Huotari, “What Went Wrong with US Strategy on China's New Bank and What Should Washington Do Now?” A China File Conversation, 24 March, 2015, www.chinafile.com.對英國來說,另一個吸引之處是,它對亞投行的支持將會促成與中國的協議,從而將倫敦指定為離岸人民幣交易清算中心。
2014年2月,奧斯本會見了中國官員,討論在倫敦設立人民幣清算中心的可能性。據奧斯本稱,這次商討將確立倫敦作為西方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的地位。Grace Li and Michelle Chen, “China, UK Discuss Setting Up Yuan Clearing Bank in London—Osborne,” Reuters, 20 February, 2014, http://uk.reuters.com/article/uk-markets-offshore-yuan-idUKBREA1J06A20140220.由于人民幣已經超過新加坡元和港幣成為世界第八大支付貨幣,蓬勃發展的人民幣業務將給英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英國加入亞投行的決定與在倫敦建立人民幣清算中心的談判有何關聯。但在2016年4月(英國加入亞投行后約一年),倫敦正式超過新加坡,成為香港以外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占所有離岸人民幣交易的6.3%。“UK Becomes Second-largest Offshore RMB Clearing Centre,” Financial Times, 20 April, 2016.
英國加入亞投行的決定,是針對中國而實施的包容性制度制衡。一方面,英國的參與得到了中國的高度贊賞和獎勵。除人民幣清算中心外,英國還獲得了亞投行副行長一職。另一方面,英國聲稱將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和權力約束中國在亞投行的行為,這將使亞投行能夠在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方面成為“最佳范例”。正如英國官員所言,英國加入亞投行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確保“英國能夠塑造這一新制度”。Nicholas Watt, Paul Lewis and Tania Branigan, “US Anger at Britain Joining Chinese-led Investment Bank AIIB,” The Guardian, 13 March, 2015.換句話說,在亞投行中,英國不會總是服從中國。相反,英國將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發言權,確保亞投行在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方面保持國際標準,防止亞投行成為中國擴大自身利益的外交工具。
由于亞投行多邊主義的設定提供了制約甚至削弱中國影響力的機制,其他西方大國預計也將與英國采取同樣的政策。但是,評估英國和其他歐洲大國在亞投行中的制衡行為是否會以及如何發揮作用,現在還為時過早。但清楚的是,英國作為亞投行的內部成員,在監督和塑造亞投行未來發展方面,將比美國、日本等外部大國發揮更大的作用。
盡管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但自21世紀初以來,兩國的雙邊關系一直被領土爭端、歷史記憶和安全競爭蒙上陰影。2009年,兩國船艦相撞事件加劇了釣魚島領土爭端。2012年,日本官方的購島行為進一步惡化了與中國的關系。民族主義和歷史記憶也為兩國間的緊張關系火上澆油。自2010年以來,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日間經濟和軍事實力對比的轉變也加深了日本對中國的安全擔憂。例如,在2014年日本《防衛白皮書》中,日本將中國和朝鮮列為日本國家安全的兩大安全威脅。特別是,日本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軍事建設和活動,包括中國于2013年底宣布在釣魚島劃設防空識別區(ADIZ),表達了強烈的擔憂。Matthew Carney, “Japan's Defence White Paper Reveals Concerns over China, North Korea,” ABC News, 5 August, 2014, http://www.abc.net.au/news/2014-08-05/japan-releases-2014-defence-white-paper/5650536.
日本決策者認為,亞投行提議對日本造成的損失大于利益。日本領導人大體上需要考慮成立亞投行帶來的兩種損失。第一種是日本在亞太地區金融治理領域的地區領導權。根據《經濟學人》的一篇報道,安倍稱:“他仍然對亞投行抱有深深的懷疑,認為它是一種擴大中國戰略和經濟實力的手段。”“To Join or not to Join,” Economist, 28 May, 2015.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亞投行對日本的區域地位構成了直接的挑戰和威脅,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的區域金融治理領域。如前所述,在戰后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日本一直是亞開行的領導者。亞投行不僅威脅到美國的總體主導地位,還特別對日本在亞開行中的角色構成了挑戰。亞投行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亞開行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方面表現不佳。顯然,亞投行的成功與削弱亞開行以及日本在亞洲次區域領導權存在相關性。因此,如果將“領導權轉移”模型在區域范圍內操作,那么日本在區域金融治理中扮演的就是領導者的角色,而中國則是挑戰者。正如美國無法在全球范圍內接受中國的挑戰一樣,從地區領導者的角度看,日本也不會接受亞投行。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領導的亞投行將對日本在亞太地區金融治理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構成威脅。
另一個阻礙日本加入亞投行的成本要素是日本與美國的聯盟關系。由于美國拒絕了亞投行的成員資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日本加入亞投行,它將與盟友分道揚鑣”。此外,“為強化日美同盟,安倍曾于4月(2015年)訪問了美國,如果日本在這之后不久就宣布加入亞投行,將會顯得尤為奇怪”。“To Join or not to Join,” Economist, 28 May, 2015.很明顯,日美同盟是阻礙日本加入亞投行的另一個制約因素。換句話說,亞投行帶來的潛在好處(如果有的話)將無法超過潛在成本,這些成本包括中國的戰略壓力、日本區域主導地位的喪失以及對日美同盟關系的潛在損害。
因此,日本對亞投行采取了排他性制度制衡戰略。日本堅定拒絕加入亞投行,這與美國的立場相同。
日本還實施了制度間制衡戰略,這是排他性制度制衡的一種延伸,旨在削弱亞投行的潛在影響力。2015年5月(亞投行成立后約一個月),日本主導的亞開行宣布,將為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提升近40%的資金,達到180億美元。“Asian Development Bank Pledges to Increase Lending, Cooperate with China-led Bank,” Japan Times, 5 May, 2015.正如一些評論員所言,亞開行的決定并非巧合。Deniel Runde, “Britain Launches European Rush to Join AIIB, Now What?” Foreign Policy, 17 March, 2015.如果亞開行能夠從亞投行手中“搶得先機”,日本將從中獲利。此外,日本還于2015年5月宣布,將在5年內為亞洲基礎設施項目提供1100億美元的援助。Leika Kihara and Linda Sieg, “Japan Unveils $110 Billion Plan to Fund Asia Infrastructure, Eye on AIIB,” Reuters, 21 May, 2015.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提供的資金超過了亞投行預計的1000億美元資金總額。毫無疑問,日本試圖利用自己主導的制度,如亞開行和龐大的援助計劃,來反制中國對其在亞太地區金融領域區域主導地位構成的挑戰。
四、 結?論
通過結合角色理論和制度制衡理論,本文提出了“領導權轉移”理論,以解釋各國對亞投行的不同政策反應。全球治理涵蓋不同的問題領域,“領導權轉移”模型顯示,在全球治理特定領域潛在的領導權轉移過程中,各國確定其各自不同的角色。當挑戰國提出建立一個新制度時,就意味著全球治理某一特定領域的領導權可能發生轉移。為了爭取支持并增強新制度的合法性,挑戰國更有可能實施包容性制度制衡戰略,通過新制度提供額外的利益,以作為舊制度無法提供的公共產品。中國對亞投行的包容性設計以及大量提供基礎設施發展公共產品的資金證明了這一論點。
另一方面,體系主導國更有可能實施排他性制度制衡戰略來抵制挑戰國創建的新制度,正如美國對亞投行的強烈反對及其在歐洲和亞洲遏制亞投行的行為所表明的那樣。而對于其他國家,“領導權轉移”模型認為,它們不得不在挑戰國和主導國之間作出選擇。如果這些國家從挑戰者那里感知到一些具體的利益,那么它們會在這種“甜頭”的吸引下選擇支持挑戰國創建的新制度,正如我們在英國改變主意轉而支持亞投行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樣。然而,如果沒有感知到足夠的利益,或者潛在的成本超過了其感知到的利益,那么它們更有可能追隨領導者,因為領導者能夠通過現有制度提供更多的穩定性。日本之所以拒絕亞投行,就是因為中國在經濟和安全領域的崛起引起了它的安全憂慮。
盡管亞投行是否會引發美國向中國的領導權轉移目前還不清楚,但可以明確的是,亞投行不會是中國在全球治理的金融領域挑戰美國主導地位的最后機遇。本文提出的全球治理“領導權轉移”模型融合了有關中國和全球治理的現有文獻,并突出強調國家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潛在的“領導權轉移”時期所面臨的制度政策的動態選擇。大多數關于中國和全球治理的研究集中于探索中國如何適應、挑戰以及塑造全球治理的規則和規范,而本文的模型著重考察在全球治理體系潛在的“領導權轉移”過程中,領導者、挑戰者和跟隨者如何借助制度制衡進行戰略互動。關于中國和全球治理的研究,參見:Mingjiang Li, “Rising from Within: China's Search for a Multilateral Worl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ino-US Rel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17, No.3, 2011, pp.331-351; Jing Gu et al., “Glob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36, No.2, 2008, pp.274-292; Lai-Ha Chan et al.,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A China Model in the Making?”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14, No.1, 2008, pp.3-19; Miles Kahler, “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Negotiating Change in a Resilient Status Qu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3, 2013, pp.711-729; Gerald Chan et al., China Engages Global Governance: A New World Order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2011); Amitav Acharya, “Can Asia Lead? Power Ambi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 No.4, 2011, pp.851-869.傳統的權力轉移理論預測中美之間可能爆發沖突,與此不同,本文認為中美兩國可以通過制度競爭,以和平方式實現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領導權轉移”。關于權力轉移理論,參見: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關于權力轉移理論在中美競爭中的應用,參見:Ronald L.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 No.1, 2006, pp.35-55.關于對權力轉移理論的批判,參見: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2007).當前體系的霸權國和受益者則需要考慮如何容納和適應中國為實現國際體系和平轉型所提出的合理要求。
最后,制度制衡絕不是唯一的戰略博弈。霸權國仍然可以使用軍事制衡的戰略來壓制崛起中的大國。崛起中的大國也可以使用武力來追求自己“在陽光下的位置”。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和法國計劃利用國際聯盟(包容性制度制衡)來約束德國和日本。然而,這種包容性制度制衡并未奏效。德國和日本都退出了國際聯盟。它們沒有尋求其他的制度手段,而是發動戰爭,利用軍事手段挑戰當時的國際秩序。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們也目睹了美國通過“重返亞太”或“再平衡”戰略,在亞太地區對中國進行軍事制衡。本文認為,如果中國和美國的決策者足夠明智,能夠克服傳統軍事制衡和使用硬實力所帶來的誘惑和恐懼,那么通過制度制衡實現相對和平的領導權轉移仍是可能的。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生?魏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