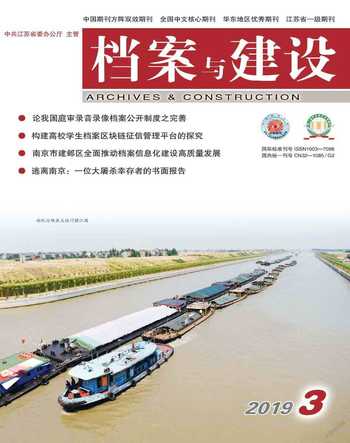社會記憶建構視角下社會情感記錄的缺位與重現
石桂蓉
[摘要]社會情感記錄作為檔案的一部分,由于形成主體權力失衡、記錄方式單一及個人記錄邊緣化等原因被排除在社會記憶構建之外。論文從根源上對社會情感記錄缺失的原因進行不同層次的剖析,試圖讓公眾認識到社會情感記錄的缺失對社會記憶建構的影響,后從“先天塑造”和“后天培養”兩種途徑針對性地提出讓社會情感記錄重現的策略,以期引起公眾對社會情感記錄的價值的認可與重視。
[關鍵詞]社會記憶社會情感個人檔案
[分類號]G270
The Absence and Reappear of Social Emotional Reco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Shi Guirong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Social emotional records, as part of the archives, are exclud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due to the imbalance of the power of the subject, the single mode of recording,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ersonal recor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lack of social emotional records, tries to make people realize the impact of the lack of social emotional record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And it proposes strategies to reproduce the social emotional record, and hopes to arouse the people’s recognit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social emotional records.
Keywords: Social Memory; Social Emotions; Personal Archives
隨著“城市記憶工程”和“鄉村記憶工程”等項目的不斷推進,檔案的記憶屬性開始受到關注與挖掘。一部分學者提出采用多元方式來加強社會記憶建構的觀點,如丁華東將大眾傳媒作為建構社會記憶的重要渠道和必不可少的條件,在不同的社會框架下進行著歷史敘事,形成了社會記憶傳承、建構、控制的獨特模式和絢爛風景,希望人們在保管、開發好檔案資源的實踐中,運用多種手段和渠道,充分發揮現代傳媒對社會記憶的主體性建構作用[1];韓良則表示可以通過口述檔案還原歷史真實性,“口述檔案作為一種新的歷史記錄形式,對于彌補、豐富傳統檔案和社會記憶有著獨特、不可或缺的作用”[2]。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學者主張從“主觀情感”出發,喚起公眾參與社會記憶建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王思怡認為,通過創傷敘事的策展,將個人、社會、民族、國家的記憶與情感凝聚成一種力量,讓觀眾自發地參與到集體記憶的建構中來,共同承擔社會責任,使受難者的歷史不被遺忘[3];李晶偉也進一步指出:“后現代社會,檔案情感價值逐漸凸顯,檔案與情感之間存在觸發、建構關系”,檔案情感價值具有“發揮著守望真實性情感世界、傳承民族集體感記憶、建構和諧有序的檔案主題情感網絡關系的社會功能”[4]。
雖然有不少學者致力于社會記憶建構的研究,但是由于記憶本身的脆弱性以及記憶依附載體的不完善性,導致無論是從客觀事實角度立基還是依托主觀敘述補充,都無法還原一個真實、立體的記憶空間。究其緣由,筆者將其歸結于社會情感記錄的長期缺位。社會情感記錄在社會記憶建構過程中的缺位致使實踐參與個體的主觀情感維度展現困難,最終使得構建的社會記憶缺乏公眾對情境的充分感知和普遍認同。自古以來,人們留存下來的檔案都傾向于對客觀事實的記載,忽視了對實踐參與者主觀感受的記錄與描述;另一方面,個人檔案,如日記、回憶錄等,因為帶有很多私人情感的偏向使得記錄文本的客觀性難以顯現,致使個人檔案一直不被正視。筆者從社會情感這個維度出發,研究社會情感記錄缺位的具體表現以及缺位原因,以期引起學界對個體情感記錄方面的檔案的重視,尤其是改變個人檔案的邊緣化處境,建議檔案形成者今后在記載客觀事實的同時也要重視對社會情感的記錄與分析。
1社會記憶建構視角下社會情感記錄的缺位詮釋
1.1社會情感記錄的界定
丹麥宗教哲學心理學家克爾凱·郭爾曾說,“情感體驗是個人把握自己存在境況的唯一方式”[5];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也強調:“人對世界的知覺,首先是由情感揭示的,而不是概念”[6];對情感的推崇最早在蘇格蘭哲學家休謨處便達到極致,他認為,“情感自從世界開辟以來就是,而且現在仍是,我們所見到的人類一切行為和企圖的源泉,這些情感的混合程度雖然有不同,卻都是遍布于社會中的”[7]。哲學家如此推崇情感的價值在于,衍生于社會中的情感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高級的內在體驗和實踐本質,它與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不斷推動著歷史的發展。正如湯姆金斯所言:“情感是最基本的動機系統,它的作用是激活、喚醒或放大內驅力,成為行為的動力”[8]。
《心理學大辭典》將情感定義為“人對客觀事物是否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產生的態度體驗”。情感與社會因素密切聯系,是導致社會情感產生的直接原因。從心理學角度來看,社會情感是情感的一種表現形式,同其他情感一樣,是人在生存和交往中對客觀對象(物質世界、他人及其行為)和自身態度的內在體驗的心理狀態和心理反應,是人的一種精神現象,通常表現為喜悅或悲哀、歡樂或憂愁、喜歡或厭惡、熱愛或憎恨、滿意或不滿等。從社會情感的內容角度上看,社會情感包括自然情感、民族情感、愛國情感、理智情感、階級情感和道德情感等[9]。
社會情感記錄則是將這些由社會群體對不同客觀事物產生的精神現象附注于具體的文字符號里,通過不同形式的表述和刻畫使得這些抽象的主觀感受得以具體化和形象化。記錄社會情感的實質是將產生在個體身上的情感信號變成可供參閱者捕捉的信息符號,通過這種方式讓旁觀者能鮮明地感受到每個事件發生過程中參與主體的情緒波動和精神狀態。記憶建構者通過對記錄下來的社會情感的解讀與分析,既可以避免依賴邏輯推理和想象力過度釋義,也使得構建的社會記憶能觸及到人文主義實質的靈魂,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1.2社會情感記錄的缺位
檔案具有原始記錄性,這個特質使得檔案成為社會記憶延續的主要載體之一,“形成檔案的初始動機就是為原初歷史‘備忘’,可以說檔案是社會記憶的初始形態,或稱之為‘儲存的記憶’,再現歷史、延傳過去是檔案的旨歸和目的”[10]。社會記憶依靠檔案實現跨時空延續,而記憶的建構也必須通過解讀檔案才能轉成具象。社會情感記錄在檔案中的缺失使得構建的社會記憶一直缺少情感層面的臨摹。因此,根據歷史主義思維索驥,不予置否的是,導致社會情感記錄缺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這些因素在檔案形成之時就已經存在。
(1)檔案形成主體權力失衡使得社會情感得不到實時反饋
客觀來說,檔案的形成主體應當包括當時社會實踐的所有參與者,可喻之為檔案的“共同形成者”。實際上,檔案的形成主體是可分為兩類,即組織者和被組織者。當權力失衡時,被組織者沒有權利進入到檔案的話語建構之中,因而使得檔案成為組織者一方的陳詞,被組織者的情感反饋尤其是負面的情感就會被抹去。按照美國人類學家保羅·康納頓的觀點,“所有極權主義都有這樣的行為方式:極權統治剝奪臣民的記憶之日,便是他們受精神奴役之始”,這種現象是為“有組織忘卻”[11]。慰安婦檔案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因為慰安婦處于權力失衡的低端,檔案無法記錄當時情境下她們經歷的情感折磨,導致她們的記憶會遭到“有組織忘卻”,進而后世在追溯的過程中也會造成當事人的二次傷害。
(2)檔案缺少雙向性記錄導致弱勢群體的主觀情感邊緣化
麥克米希和皮戈特認為“西方檔案理論和實踐是存在特權現象的,并且對情感和精神都是盲目的”[12],組織記錄的嚴肅性使得檔案記錄的內容主要偏向于對客觀事實的單向記錄,比如1950—1995年蘇格蘭住宿學校和兒童之家的看護檔案,由于缺少完整的記錄致使兒童住宅區內“虐童事件”得不到徹底審查。原因在于,把控話語權的看護人員會選擇性地“制造檔案”,這種選擇性直接表現為凡是不利于看護方的檔案要么及時銷毀,要么根本不會記錄在冊(如懲罰記錄的缺失)。對看護人員來說“記錄這些負面事件的檔案,具有行政性,并不打算給孩子閱讀”,所以他們更不會讓孩子參與到檔案的“制造”過程中來[13];除此之外,被看護者的情感表象(如情緒)也不會作為評判他們工作的標準,斯溫和馬斯格羅夫在訪問和閱讀澳大利亞護理人員記錄時發現“它們(留存的案例文件)是出于官僚的原因而編制的,并保留了確保組織有效運作所必需的表格和文件,而沒有試圖講述生活的故事”[14],在缺乏完善的規章體制和社會正義的牽制之下,社會情感記錄的缺失一度成為看護者為所欲為的法律屏障。最終,弱勢群體的社會情感逐漸被邊緣化直至完全消失在客觀的敘事規則之中。
(3)個人記錄的邊緣化致使主要承載社會情感記錄的個人檔案不被正視
個人檔案是“是由個人在其生活、工作和休閑過程產生的”[15]。個人檔案定義的廣泛性使得其客觀屬性一直存在爭議,從而使得個人記錄在某些關鍵方面被視為規范之外。伯克認為個人檔案是有情感的,具有主觀性,而組織檔案是務實客觀和非人格的,因而比個人檔案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影響和重要性[16];除此之外,個人檔案的無序性也使得它被排除在傳統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對象之外。但是,檔案不應僅僅是文件有序積累的產物,還應通過個人的干預、審訊和解釋,達到“無限激活”的目的,從而發現其記錄的用途和動機。加拿大檔案學者詹弗妮·道格拉斯從記憶的激活角度說明了個人在檔案中扮演的角色:“激活檔案的應是記錄者(個人)而不是記錄的內容,因為檔案是由人(檔案創建者)產生的,并為人(創建者、用戶、檔案工作者等)所用”,并闡釋道,“組織記錄也是由個人記錄表現出來的,并且個人的記錄可以完善組織記錄”,因此她拒絕個人檔案與組織檔案的二元區分[17]。從個人檔案潛在價值來講,“個人檔案的基本特征是反映其創作者的‘心理學’和‘性格’的方式”[18],所以個人檔案具有組織檔案所不具備的情感記錄,因而借助個人檔案不僅能夠激活記錄者的親身經歷、重塑群體影像,而且還能夠滿足個體未來尋求身份認同的情感需求,打破“結構性”遺忘程序。記錄一旦塵封成檔案,在跨時代宏大敘述的背景下,如何激活檔案的記憶功能,是為社會記憶建構之難題。而個人作為社會與記錄之間互動的紐帶,在解讀鄉愁、維系宗族關系中確實能夠起到很好的輔助作用。
檔案形成主體權力的失衡是權力博弈的結果,檔案缺少雙向性記錄是緣于記錄制度的缺失,個人檔案的邊緣化則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概而言之,社會記憶建構的過程中,主觀行為有意識的自我規避,具有深層次的政治和意識緣由。如若想打破這個局面,必須重新構建社會情感的延續方式,大到制度、意識等宏觀層面,細至情感、行為等微觀動態。
2社會情感記錄在社會記憶建構中的重現策略
社會情感記錄在社會記憶建構過程中的重現要從“先天塑造”和“后天培養”兩種行為途徑著手。“先天塑造”是檔案形成者的主動行為,主要是從檔案的形成源頭開始有意識地記錄含有情感色彩的信息符號;“后天培養”則是檔案開發和利用者利用多元方式重新搜索和補充情感記錄,再將捕捉的情感記錄放置于社會記憶建構的立體空間之中,是被動記錄行為。
2.1平衡記錄主體話語,打破官方敘事規則
社會記憶的建構不僅需要大量客觀數據和史料的支撐,還需要情感維度的把控。所以,為了充分還原社會記憶的立體性,必須將記憶的主要載體——檔案作為突破口。首先是要平衡檔案“共同形成者”之間的關系。這種平衡不僅體現在組織者與被組織者雙方的權力牽制上,還應表現在雙方話語內容與分量上的互證上。也就是說,不論權力大小、社會地位高低,形成的檔案應當充分顯示出“共同形成主體”的全部意識與主觀情感,而不應僅淪為官方客觀事實的發聲筒。那么如何進一步平衡記錄主體話語呢?第一,要擴大民主權利,只有在民主思想成為主流意識的情況之下,民眾的話語權才能得到充分尊重;第二,借助傳媒介質擴大民眾的發言途徑,使得民眾的呼聲逐漸被重視起來;第三,提升國民素質,從根本上平衡權力與話語的爭奪力量。如此,在重建慰安婦檔案記憶的過程中,應當充分體現受害者的話語分量與情感傾訴,借助媒體的效應,將這段慘痛的歷史教訓曝光于現實之中,讓失語者重新回到話筒的跟前揭露一段欲蓋彌彰的歷史。總之,只有平衡記錄主體的話語力量,才能打破官方敘事的任意性,使得實踐中產生的所有情感得以真實與完整記錄。
2.2改變社會記錄方式,規范雙向記錄行為
自封建社會以來,統治階級的記錄方式便是一種管制行為,比如審批、通知和公告等,是對被統治階級行為與話語權的一種約束。但在社會正義的牽制下,已經引發了社會記錄方式的改變,但這種改變還不夠徹底。若想構建完整且客觀的社會記憶,就必須重新建構一種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有利于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另外一種公平、全面的記錄方式,即全員參與式的記錄方式,這種記錄方式主要特征就是實現參與主體的雙向互動與全面反饋。在這種記錄方式的基礎上將參與者的情感反饋作為一個記錄指標,從而續寫完整的記憶內容。這種記錄方式的改變,最有利于規避弱勢群體的不公正傷害,尤其是在社區福利院和幼兒園等灰色管理地帶,更需要將被照顧者的情感作為記錄指標之一。因為,這些記錄是由被照顧群體自行反饋,并且能得到組織與社會實時的接收與反饋,如此不僅能夠及時傳達出雙方的情感需求,以期獲得更好的照顧,還能成為評判社區福利院等管理工作的標準。但即便是實現了互動式記錄,但因為記錄行為缺少有效的監督,存在欺騙性與威脅性,致使情感記錄存在失真嫌疑。因此,就需要進一步規范雙向記錄行為,完善社會監督與第三方介入的行為模式。比如,志愿者的反饋記錄和視頻的監控等,都能起到很好的規范行為的作用。
2.3重視個人檔案價值,充分體現社會情感
從“后天培養”的層面來說,我們對已經形成的記錄無法進行即時性修補,但若想進一步追溯當時社會情感的具體表現,后世還不至于完全處于被動的地步。原因是可以通過對個人檔案的開發來追索社會參與者的情感表象,如道格拉斯所言,“制度記錄無法講述‘整體’故事,但是,‘整體’故事是我們在閱讀它們時試圖重建的故事”[19],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醫療檔案中的客觀記錄無法講述她喪女悲傷的故事。所以,走出喪親之痛后,她運用自動人口統計學的特殊方法,利用個人記錄,包括“日記摘錄、醫療記錄(自己和家人對醫療事件的記錄)、草圖和照片”,并結合部分從醫院申請到的醫療檔案,才保留了有關她女兒的全部情感記憶。在這個案例中,詹弗妮·道格拉斯證明了“通過協商和使用其他類型的機構記錄可以激活經歷過的重要且強烈的情感維度”[20]。在道格拉斯看來,這種情感維度可能不是記錄創建環境的一部分,但它至少是一些檔案用戶的經驗的核心。所以,在構建社會記憶的過程中,可以將個人檔案作為補充材料,重視個人檔案的價值。比如,個人記錄形成的日記,雖然具有明顯的文學性,但正是因為這種文學性反而更能反映出記錄個體的真情實感。記憶的延續需要情感,記憶的感知也需要情感,我們必須正視個人在檔案中的潛在價值。另外,如果可供解讀的檔案數量較少而當事人還健在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依賴口述檔案維系記憶的情感。雖然從個人的立場追述記憶的情感狀態,不可避免會造成二次傷害,但是記憶的產生需要情感的共鳴,這也是為什么借助慰安婦口述檔案制成的紀錄片《二十二》會引發社會的集體“反遺忘”意識。
社會情感記錄在社會記憶建構過程中,從缺位到重現的轉變不僅是社會意識形態的重塑,還是社會記錄方式的改變,啟示著人們在關注外部客觀條件的同時,更應該注重人類情感的寄托與抒發。人與人之間不僅僅依靠物質建立聯系,更多情況下是依賴情感的交叉而愈發緊密。社會記憶的建構正是基于情感的維系和尋求身份的認同而不斷推進的結果。社會記憶的構建者必須清楚當事人的社會情感狀態,從而構建一個真實的社會記憶、一個能被歷史承認、被社會接納的真理性記憶。而這種真實性的回歸,從現階段來說,必須正視個人檔案的價值,使得帶有感情記錄的檔案能夠逐漸回歸到社會記憶建構的核心范圍。
參考文獻
[1]丁華東.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12-353.
[2]韓良.口述檔案與社會記憶構建關系再思考——基于“歷史真實性”視角[J].檔案與建設,2018(4):18-20.
[3]王思怡.紀念與記憶:創傷敘事的策展建構與詮釋——以東亞社會各慰安婦主題紀念展覽為例[J].中國博物,2017(1): 14-22.
[4]李晶偉.檔案情感價值研究[J].山西檔案,2018(4): 18-21.
[5][6][9]殷霞.社會情感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J].發展論壇,2003(5):50-51.
[7][英]休謨.人類理智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1:75.
[8]申來津.激勵發生原理:一種心理學解釋[J].學術交流, 2003(4):26-29.
[10]丁華東.社會失憶、檔案與歷史再現[J].檔案與建設, 2010(4):6-9.
[11]保羅·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11.
[12]Kemmish S., Piggott M..Toward the archival multiverse: challeng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the personal and corporate archive in modern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J].Archivaria,2013(1):111-144.
[13]MacNeil H., Duff W., Dotiwalla A., Zuchniak K..“If there are no records, there is no narrative”:the social justice impact of records of Scottish careleavers[J].Archival Science,2018(1):1-28.
[14]Swain S., Musgrove N..We are the stories we tell about ourselves: child welfare recor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mong Australians who, as children, experienced out- of- home‘care’[J].Archives & Manuscripts,2012(1):4-14.
[15]Williams C..Personal papers: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In: Craven L(ed)What are archives?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M].Aldershot:Ashgate,2008:55-56.
[16]Burke F.. Research and the manuscript tradition[M]. Lanham:Scarecrow Press,1997:11.
[17][19][20]Douglas J., Mills A..From the sidelines to the center: re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personal in archives[J]. Archival Science,2018(3):257-277.
[18]Hobbs C..The character of personal archives: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the records of individuals[J].Archivaria, 2001(52):126-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