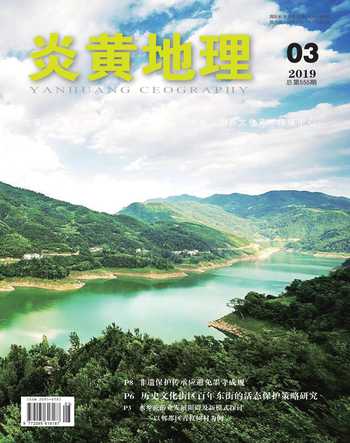印度電影中農(nóng)民失地困境的展示與解決
摘 要:新世紀(jì),印度經(jīng)濟(jì)的起飛促進(jìn)了文化的蓬勃發(fā)展,印度新概念電影迅速崛起,涌現(xiàn)出一大批貼近人民生活,又具有深刻的社會(huì)意義的影片。阿努沙·里茲維的《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便是其中之一,1955年的《兩畝地》同樣以失地農(nóng)民為主人公,并借此反映了印度社會(huì)的獨(dú)特風(fēng)貌。這兩部影片不約而同地展現(xiàn)了印度底層農(nóng)民的失地困境與焦慮,本文將對(duì)《兩畝地》與《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這兩部影片進(jìn)行對(duì)比研究,結(jié)合歷史背景分析不同時(shí)期的印度電影是如何展示失地農(nóng)民的困境與焦慮并對(duì)其進(jìn)行解決的,探究這種差異背后所的社會(huì)文化意義。
關(guān)鍵詞:失地困境;印度新概念電影;城市化;底層敘事
1 失地困境的呈現(xiàn)與原因
《兩畝地》與《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的主人公都是印度傳統(tǒng)的底層農(nóng)民,兩者都面臨在城市化的巨浪中失去土地的危險(xiǎn)。同樣的,兩部影片也都以“保住自己土地”這一最基本的欲望作為敘事的原動(dòng)力來架構(gòu)起整部影片。
誠(chéng)然,土地對(duì)于農(nóng)民的越重要,那么當(dāng)它被剝奪時(shí)農(nóng)民所面臨的困境與焦慮就越強(qiáng)烈。在《兩畝地》中,土地對(duì)于男主人公向波來說,不僅是一家老小生存的保障,也是自己一生的依靠。影片中結(jié)尾的一場(chǎng)戲,向波最終沒能湊夠保住土地的錢,落魄的他帶著妻兒回到家鄉(xiāng),老父早已被逼地發(fā)瘋而走,無奈的向波悲涼地抓了一把地上的土,用這種手段來釋放對(duì)于土地的愛與不舍。《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中,貧窮的農(nóng)民兩兄弟納塔和布萊克同樣被沉重的債務(wù)逼迫地走投無路,為了保住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兩兄弟機(jī)緣巧合之下走上了“自殺騙取補(bǔ)助金”的道路。納塔在片中直言:“我們做了這么多都是為了保護(hù)祖輩留下的土地,而現(xiàn)在我們要失去它了。如果可以,我愿意放棄我的生命來保住它。”不僅如此,導(dǎo)演還別具匠心地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挖土老人”的形象——失去土地的老人執(zhí)著地挖著土,用一種近乎詩(shī)歌意象一樣的隱喻的方式來表達(dá)土地之于農(nóng)民的重要性。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兩畝地》中最后的抒情,還是《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中的直抒胸臆與象征隱喻,兩部影片都在不斷地強(qiáng)化土地對(duì)于農(nóng)民的重要性,土地在這里已經(jīng)升華成了一種農(nóng)民自身的“身份認(rèn)同”,進(jìn)而從側(cè)面加強(qiáng)了農(nóng)民所面臨的失地困境與焦慮。
在《兩畝地》與《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中,雖然主人公們都面臨著失地困境與焦慮,但究其根本,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卻有著各自的特點(diǎn),可以說,兩部影片中的失地困境在有著相同的表現(xiàn)形式的同時(shí)還有著自身獨(dú)特的時(shí)代特色,筆者將其歸納為“既一脈相承,又與時(shí)俱進(jìn)。”
無論是1955年的《兩畝地》,還是2014年的《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在展現(xiàn)失地農(nóng)民的困境時(shí),無不和“城市化”、“現(xiàn)代化”等關(guān)鍵詞聯(lián)系在一起。在《兩畝地》中,主人公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yàn)榈刂饕谒耐恋厣辖ㄔ旃S,向波所從事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與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之間產(chǎn)生了不可調(diào)和的利益沖突;而《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里,在一次電視采訪中,當(dāng)記者問道“你對(duì)政府阻止農(nóng)民自殺有何建議”時(shí),農(nóng)業(yè)部長(zhǎng)答道:“工業(yè)化。發(fā)展中國(guó)家不能僅僅依靠農(nóng)業(yè)。”由此可見,兩部影片都在構(gòu)建著一種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與現(xiàn)代工業(yè)、原生農(nóng)村與新興城市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因此影片中主人公所面臨的困境,實(shí)則是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濟(jì)模式與生活方式對(duì)印度傳統(tǒng)的一種侵蝕與沖擊。
《兩畝地》與《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中展示的失地困境,除了具有一脈相承的二元對(duì)立之外,還有著各自獨(dú)特的時(shí)代特色。《兩畝地》成片于1955年,彼時(shí)印度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還比較落后,學(xué)習(xí)西方的范圍與程度也不及當(dāng)下。西方的生活、生產(chǎn)模式對(duì)印度影響較小,地主階級(jí)與種姓制度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在這樣的條件下,印度城市化與現(xiàn)代化的主要推動(dòng)力是其內(nèi)部的民族資本發(fā)展。因此,當(dāng)?shù)刂鳑Q心建造工廠的時(shí)候,首先就是著手侵吞底層農(nóng)民向波的土地。影片反應(yīng)是國(guó)內(nèi)地主階級(jí)與底層農(nóng)民之間的矛盾。
《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完成于2014年,這時(shí)的印度在政治環(huán)境、傳媒產(chǎn)業(yè)、生產(chǎn)生活與社會(huì)文化等各個(gè)方面大幅度向美國(guó)等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學(xué)習(xí),西方國(guó)家的生活與生產(chǎn)模式成了印度現(xiàn)代化的主要范本。在《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里,農(nóng)民們聚在一起抱怨:“怎樣才能好好種地呢?美國(guó)種子,美國(guó)化肥,花大錢買了,然后祈禱下雨”,不僅如此,在影片的后半部分結(jié)尾,導(dǎo)演借助部長(zhǎng)助手之口說出了:“薩利姆先生推薦了一個(gè)美國(guó)公司。叫什么來著?山孟都(Sonmanto)?政府所有的種子合同都給他們。”毫無疑問,矛頭直指美國(guó)轉(zhuǎn)基因種子巨頭——孟山都公司。聯(lián)系影片中納塔的命運(yùn),他在現(xiàn)代化的農(nóng)業(yè)中失去了土地,在西方化的政治制度里任人擺布,在看似開放的傳媒行業(yè)里淪為噱頭與工具。可見以美國(guó)為代表的西方先進(jìn)國(guó)家并沒有給印度帶來表面上的開明與繁榮,相反,它們資本的涌入與文化的壓制卻讓印度底層人民流離失所。在這里,美國(guó)不再是一個(gè)單純的國(guó)家,而是凝結(jié)成為了一個(gè)發(fā)達(dá)而又恐怖的“他者”形象。對(duì)比于1955年的兩畝地,《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顯然在矛盾的構(gòu)建上又上升了一個(gè)層次,擁有著更加鮮明的時(shí)代性。
2 失地困境的解決
《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與《兩畝地》均屬于現(xiàn)實(shí)題材的故事片,它們?cè)谡宫F(xiàn)印度底層農(nóng)民失地困境與焦慮的同時(shí),也在各自的故事架構(gòu)內(nèi)對(duì)所展現(xiàn)出的失地困境進(jìn)行著解決。筆者認(rèn)為,兩部影片在失地困境的解決上,既有共性,也有差異。共性在于兩部影片均采用了一種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解決手法,即“不解決的解決”;而差異在于《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較之《兩畝地》,又多了在想象與隱喻層面的解決。
在《兩畝地》與《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的結(jié)尾,片中的主人公雖然歷經(jīng)劫難,卻始終未能保住自己的土地,向波帶著妻兒遠(yuǎn)走他鄉(xiāng),納塔則在一個(gè)不知名的工地上成為了千萬農(nóng)民工中的一員。對(duì)比兩部影片,筆者發(fā)現(xiàn)它們?cè)趯?duì)底層農(nóng)民的失地困境進(jìn)行展示與描繪之后,并沒有嘗試用一種戲劇化的方式來消解這種矛盾與沖突。相反,兩部影片不約而同地讓主人公在最終走向失敗。筆者認(rèn)為,這種對(duì)于失地困境的解決方式,實(shí)際上是一種“不解決的解決”,即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解決。這樣的設(shè)計(jì),讓兩部影片以一種悲涼的情調(diào)展現(xiàn)出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無奈,映射著整個(gè)印度民族在面對(duì)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等對(duì)于傳統(tǒng)生產(chǎn)模式、生活方式的大肆侵蝕時(shí)內(nèi)心的恐懼與無所適從。可以說,這種焦慮從《兩畝地》一直延續(xù)到了《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并且通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結(jié)局獲得了強(qiáng)有力的放大表達(dá)。
不同于《兩畝地》,《自殺現(xiàn)成直播》的結(jié)局在隱喻與象征的層面為觀眾提供了更多解讀的可能。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gè)有著深厚的宗教底蘊(yùn)的國(guó)家,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對(duì)印度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的結(jié)尾,主人公納塔在經(jīng)歷爆炸之后,所有的人都以為他已經(jīng)死了,但是他最后卻重新出現(xiàn)在了一個(gè)建筑工地,沒有人認(rèn)識(shí)他,納塔以農(nóng)民工的身份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這樣的設(shè)計(jì),與宗教中的“轉(zhuǎn)世、涅槃、輪回”等概念不謀而合。納塔農(nóng)民身份的轉(zhuǎn)變,實(shí)際上成為了他的一次“轉(zhuǎn)世”,也是千千萬萬印度底層農(nóng)民的“轉(zhuǎn)世”。
除此之外,《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的結(jié)尾并非單純地涉及了宗教概念,當(dāng)我們將電影文本與印度歷史相結(jié)合時(shí),便可以發(fā)現(xiàn)導(dǎo)演在這里的匠心獨(dú)運(yùn)與良苦用心。影片末尾,伴隨著納塔在灰塵中奮力地工作,響起了悲涼的歌聲,歌中唱到:“誰知道我們?nèi)ハ蚝畏剑囕嗊€在滾滾向前。沒有食物,沒有水,找個(gè)借口活下去。疲憊的雙眼,模糊的夢(mèng)想。眼淚中也有鹽,我的朋友,如果它落下,請(qǐng)淺嘗。”我們知道,印度的民族英雄——圣雄甘地,正是從帶領(lǐng)印度人民打破殖民者的食鹽壟斷來開始爭(zhēng)取民族獨(dú)立的。那么聯(lián)系上文中的論述,以美國(guó)為代表的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中已經(jīng)凝結(jié)為了一個(gè)恐怖而又強(qiáng)大的“他者”形象。這個(gè)“他者”在給印度帶來所謂“先進(jìn)文化”、“先進(jìn)制度”的同時(shí),也在伙同印度國(guó)內(nèi)的統(tǒng)治階級(jí)去壓迫、去榨取那些底層勞苦大眾,并且不斷侵蝕著印度的傳統(tǒng)與文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這部《自殺現(xiàn)場(chǎng)直播》作為印度新概念電影之一,結(jié)尾利用“鹽”的意象,可以說是在以隱喻的方式對(duì)印度人民所發(fā)出的號(hào)召,是一種對(duì)印度長(zhǎng)久以來盲目全面學(xué)習(xí)西方的模式進(jìn)行的有力控訴,是對(duì)實(shí)現(xiàn)印度自身民族獨(dú)立與文化獨(dú)立所發(fā)出的無聲吶喊。
參考文獻(xiàn)
[1]吳曉黎.農(nóng)民自殺與印度農(nóng)業(yè)危機(jī)[J].社會(huì)觀察,2011,07:70-71.
[2]吳燕.《自殺直播》:失耕農(nóng)民命運(yùn)的另類解讀[J].民主與科學(xué),2012,01:74-76.
[3]趙國(guó)賀.轉(zhuǎn)基因種子為害印度[J].世界博覽,2010,14:36-39.
作者簡(jiǎn)介:
姓名:王亨淵(1993-),性別:男,民族漢族:籍貫:甘肅天水市甘谷縣,學(xué)歷:碩士,就讀于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現(xiàn)有職稱:碩士;研究方向:電影創(chuàng)作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