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森的語境主義倫理觀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意義及檢驗
□文|馬寧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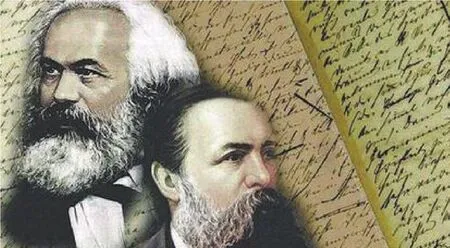
尼爾森的語境主義倫理觀有力的維護了馬克思主義倫理觀,在經過對文本的合理闡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馬恩經典文本中對資本主義所抱持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意識形態色彩的揭露與馬恩所描述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中“真正人的道德”之間可能存在的爭議。他回應了以艾倫·伍德為例的反道德主義者的觀點,即:馬克思是“一位道德批判者或反對者,他不僅批判或反對虛假的道德信念,而且批判或反對全部道德。”[ 《歷史唯物主義何以能兼容道德——從凱·尼爾森的“馬克思主義道德觀念”談起》 符海平]通過馬克思主義對“道德就是意識形態”所做出的合理闡釋,將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意識形態與道德進行了一定的區分。強調意識形態必定是上層建筑,但是并不一定上層建筑全部屬于意識形態,尼爾森指出“并不是所有的道德都是反映和辯護階級的利益從而成為意識形態的道德”[ 《馬克思主義與道德觀念》尼爾森 P8],以上表述中的道德都是指意識形態的道德,而不是指全部的道德。
在此基礎上,通過對道德本身的來源與社會功能的探究,確立了道德理念的客觀性,并展開了馬克思主義倫理觀研究的科學性與意義。“語境主義承認道德具有被決定性或依附性,但這種被決定關系或依附關系卻不是空穴來風。并且,它們的來源之處也不是主觀的、任意的層面,而是經驗的、物質的社會語境。”[ 《道德之爭與語境主義——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初始問題與凱·尼爾森的回答》李義天]在厘清道德本身的客觀來源之后,為馬克思主義倫理觀尋找到了客觀物質環境的基礎,使得對道德的探討擺脫了相對主義的窠臼。正是由于此,評判道德體系本身的歷史正當性以及不同道德體系之間的比較具有了客觀的標準,將一直以來對道德體系的概念到概念的空談拉回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傳統語境當中,在倫理學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尋找到了新的結合點。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應當具有的其中一個特征就是論證資本主義社會基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的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不正當性。通過批判使得生活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公民至少可以認可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可選擇的一種社會模式,并且其本身相較于資本主義社會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換而言之,在同一語境下(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為基礎),人們能夠經過比較資本主義社會道德與馬克思主義道德觀,認可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合理性甚至將馬克思主義道德觀作為“最正確”的道德觀理解。而這一點對語境主義提出了挑戰,由于道德體系本身所具有的的被決定性和依附性,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的上層建筑,即使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揭示出其本身思想的階級來源,依舊是一種描述性的闡述,不能夠指出其在道德倫理的層面上的不正義性,至多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描述,激起人民對極大不平等的厭惡,對大量赤貧人口的同情,這種公民義憤是基于人民的道德直觀但是并沒有多大程度上是超出直觀本身的。
尼爾森自身對語境主義中對道德優劣的比較進行了一定闡述,但是這種闡述,或者說至少在低限度的解讀內不足以完成在同一語境下兩種道德觀的比較。語境主義“通過對語境的實證分析比較而對各種道德的高下優劣作出大致判斷”[ 《道德之爭與語境主義——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初始問題與凱·尼爾森的回答》李義天],“語境主義者所堅持的基本原理,與相對主義者是完全不同的。對語境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已然改變的客觀情境在證明著改變; 而對相對主義者來說,是態度,是社會的、階級的或個人的信念體系,是一組特殊的承諾,或是一些特殊的概念框架,在證明或至少在解釋不同的道德信念或評價機制。”[ 《馬克思主義與道德觀念》尼爾森]“如果人們必定生活在語境中,只能從每個時間點和語境的內部視角出發,那么他們就總會發現其中有一種道德原則是‘(最) 正確’。”文本中所出現的對道德優劣的比較主要是側重于回應道德上的主觀主義,回應“沒有什么最好的道德主義”的觀點,事實上語境主義對相對主義的主要回應并不在于道德體系的優劣排序上,根本上依舊是從為道德找到客觀來源和客觀標準的層面上進行批駁,攻擊的是相對主義認為的由概念體系解釋和論證道德的觀點,但是要從這種論述中推出語境主義能夠在資本主義語境下推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更具有可欲性還是太快了。
如果能夠將科恩的“自我所有”論證與“語境主義”相關論證結合起來,或許能夠在維持“自我所有”這一由于與自由主義理論傳統可能重合的理論基點而受到一定爭議的概念的情況下,對資本主義社會做出有力的批判。道德公理這一概念本身留下的合理闡釋空間指明了社會主義道德與資本主義道德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存在這一可能,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中,某些資本主義的道德理論依舊作為道德公理存在并且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中得到進一步的實現。正如《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指出的“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 《哥達綱領批判》]“自我所有”這一概念依舊會受到爭議,但是如果在語境主義的領域內,“自我所有”“按勞分配”可以通過樸素的道德直觀以及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維度得證其作為道德公理存在的意義,并且這種存在在《哥達綱領批判》當中有明顯痕跡,并沒有超出文本合理闡釋的范圍。基于語境主義本身的客觀性,即其“是隨著客觀情境的變化而變化,道德的對或錯是由人們的實際需要來決定的。道德的存在和變遷并不是人們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對于它們的時代來說是必然的和正確的’。”
尼爾森在回應“反道德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中得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存在且應當存在倫理學的結論以及倫理道德具有客觀依據的結論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將論證的成果之一——語境主義歸結為馬克思主義倫理觀依舊跨步太大,還需要經過與馬克思主義倫理觀應當具有的特征進行參照方能確證自身。這種特征表現在較低的道德功能的層面上指作為馬克思主義倫理觀應當是能夠完成對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筑的批判以及完成對資本主義社會倫理道德和社會主義社會倫理道德的一定層面上的比較。如果語境主義在對資本主義批判的維度上失效或者表現不佳,那么這一理論的魅力將大打折扣。
綜上所述,在目前的語境主義倫理框架下,對馬克思主義拒斥倫理學這一論斷的反駁已經較為充分。但是語境主義倫理觀能否被定義為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基礎框架還有較大疑點,在對道德評級體系上的“阿基米德點”的探索也必將經歷合法性,可用性等等的探討,這一框架是遠未完成的理論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