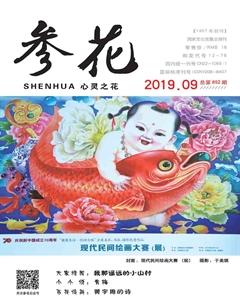散文二題
但遠程

趕海
七月二十三日這天,農歷是六月二十一,大暑。
這天,驕陽似火。上午十點鐘,車從老姨家啟程,沿著文登市區的秀山路往東南行駛一小時,將乘車的老姨、我、弟弟和弟媳送到了榮成灣。
榮成灣,面積21.6平方公里,位于山東半島最東部的黃海海域,成山角的西南側,榮成市東北角。初次趕海,內心充滿好奇和喜悅。來到海邊,見海天相連,一望無際。因榮成灣屬暖溫帶季風性濕潤氣候,空氣中攜帶著濕氣,頓時感到身上有些涼爽。海水宛若初生的嬰兒,平靜地酣睡著。因為來趕海,我心急地上前詢問一位年過六旬卻身材健壯正在修織漁網的漁夫,想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趕海講究日期(農歷),最佳趕海時間一般為初一11:30至13:00,初二12:10至14:10 ,初三……”
主要須具備和把握住這三個條件——
一、時間:趕海一般選擇大潮汛為最好,海水退得又遠又快,貝類海鮮會擱淺在沙灘和泥灘上。
二、天氣:當刮南風的時候,最好別是正南風和西南風。風力大,潮水會借助風力退得比沒風時要遠得多。
三、地點:因為每種海產品的棲息地不同。
漁民指著我們腳下說:“憑我幾十年海上打魚、海邊生活的經驗,這地方就是貝類出現最多的地方,不信你們沿著海邊肯定能找到上次潮汐趕海人留下的貝類。”他仰望西北的天際,又俯瞰海面上騰飛的水烏,“今天十二點十分有潮汐”。我由衷地佩服他告訴我這些關于大海的豐富知識,可看著晴朗的天,望著不動的海,我半信半疑,但內心依然期盼著潮汐的到來和落去后給我帶來的驚喜。在離海岸較遠的沙灘上,我認真地尋覓,果然發現少量的牡蠣、小蟹和海草。當看見弟媳手里拿著像女人裙子一樣的海草,卻不知道這是什么的時候,一位漁民上前說:“這是裙帶菜,營養豐富,含有很高的蛋白質。”聽他這么一說,我們趕海的信心就倍增了。
榮成灣距威海百余里,雖然不像威海名氣大得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但這里大都是成山鎮的漁民、喜歡清靜的休閑人或是附近區域趕海的人。從海邊織網、修船忙碌的身影中;從亭臺唱紅歌、唱情歌、吹口琴、放音樂的人群中;從站在海邊,望著大海,期待變化的目光中,都可以看出人們對這片海的熱情。海邊沙灘北岸數千米都鋪墊著木棧道,木棧道中設有幾處亭臺。沙灘上,搭建起許多小帳篷;帳篷外,有孩子們最喜歡的露天秋千;遮陽傘下,戀人們面朝大海訴說著愛情的浪漫;海岸上,還有開放式的濱海公園。公園分為明珠廣場、觀演廣場、榮武廣場、漁家樂廣場、南擴公園和燈塔公園。公園里各處綠樹成蔭,花開似錦,噴泉在陽光的照射下如一串串閃閃發亮的珍珠。
從海邊到沙灘再到海岸濱海公園,意猶未盡地環繞一圈后又回到了來時的海邊。我心潮起伏,不由追憶起中日甲午海戰(1894),日寇于榮成灣龍眼嘴以西,落風崗以東的龍須島鎮的海面登陸,占領成山衛,攻陷威海的那段屈辱的歷史。一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榮成灣十幾里外有機場,威海擁有強大的海防力量,能夠為安邦定國貢獻力量,榮成灣的人民可安居樂業地奔小康。隨著榮成灣礦產、水產等天然豐盛的資源被科學化開采,榮成灣揚名海外。不僅國內,就連相隔一百多海里外的韓國的投資者也紛紛前來激活市場經濟,現在的榮成灣可謂前途無量了。
海上起風了,是南風。把一朵朵傘狀的白云牽來,一層又一層奔騰的浪花隨著越來越強烈的風,將太陽遮擋,向海岸綻開,正應驗了漁夫的話,“十二點十分,有潮汐。”“潮汐了。”這是漁民的提醒。“潮汐了!”這是游客的歡呼聲。“潮汐了!!!”這是趕海人躍躍欲試的興奮的聲音。這些聲音伴隨著海浪“嘩!嘩!嘩!”的翻滾,回蕩了很遠很遠。
常回去看看
七月,去文登探望老姨,突然想回到母親當兵前生活過的汪疃公社王家產故居看看。這種想法很強烈,似海水般洶涌。于是,隔天我便催促老姨和老姨夫陪我回了一趟母親在世時曾朝思暮想的老家。
到了老家,鐵門大開,二百平方米的院落還算干凈整潔。記憶中,原先平整的地面已變得凹凸不平。從東邊走廊外往里行走二十多米,便是庭院。庭院內,矗立著一堵三米高的白墻,墻中央鐫刻的“福”字,由黑漆描摹,清晰可辨。只是墻上的白顏色不均,深一塊淺一塊的。房舍的墻有很多裂紋,頂端的紅瓦都是年久失修的痕跡,門、窗、房檐,恰如現在骨瘦如柴、步履蹣跚、臉上爬滿皺紋的主人一般,透露著滄桑。
聽老姨說,三十年前,姥爺去世前移居文登市,老宅被這位闖關東歸來的本家親戚,死乞白賴地以低價購買,看著母親的故居變得這般模樣,雙眼濕漉漉的。好在主人很熱情,還有庭院內那條看家犬汪汪汪地叫著,不停地搖著尾巴,歡迎老姨和我這個遠道而來、和這老宅有歷史淵源的小家雀。
進入正房,水泥地面大塊剝落,房內家具稀少,只有一件褚紅色的雙開柜。這是所有房屋中最有價值的,也是現在的主人乞求老姨留下的唯一的物件。我細細觀察,木材質地堅韌,花紋清晰,幽香四溢。老姨說這是我太姥爺那一輩留下的東西。沒承想,雖然新主人生計窘迫,卻依舊善待,使得衣柜至今都完好無損。
步入東、西廂房,每間廂房都沒有一絲現代化的氣息,還沿用著那寬大的土炕。土炕能睡下四到五人。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同弟弟頭一次來,請求老姨,希望能被安置睡在母親那年探親時住的西廂房。那時表弟還未出世,表妹妮妮剛半歲,老姨既要關心我們的生活,又要照顧表妹,非常辛苦。老姨的地瓜烀得倍兒甜,花生炒得脆兒香,做出的菜,色、香、味俱全。我和弟弟食欲陡增,那時正值春節,小桌放在炕上,姥爺、姨夫盤腿而坐,我跟弟弟起初坐在小板凳上,后來也習慣了盤腿而坐。
當年冬季比較寒冷,喝酒時,講究先溫。所謂溫酒,就是把酒放在器皿中用水加溫到不冷不燙為止,從早上吃喝、聊天到晚上,老土炕燒得很熱,我常常會坐在老土炕上打起呼嚕。
時光如梭,一去不復返,可思念母親的心事更加濃了。重返母親的故居,撫摸著飽含幾代人歲月變化的土炕,我真正地捕捉到了母親四十多年前,那種不顧交通不便、帶著四弟回來的感覺。
我撫摸著這老土炕,猶如撫摸到母親寬厚、溫暖的胸懷;撫摸著這老土炕,我似乎又感受到母親慈眉善目的臉上露出祥和的笑容,記憶猶新的是她老人家對故土眷戀的神情。自打我記事起,母親一說到故鄉便滔滔不絕,可為了軍人的職責、使命,為了工作,為了她的孩子,僅回過一次,就再也沒有機會。如今母親的兒子在她老人家精心呵護培育下都茁壯成長。雖然老宅物是人非,但是我們兄弟依然追隨著母親的足跡。
那天,出了老宅,上山祭祀姥爺、姥姥后回到老姨家。夜里我難以入眠,開燈拿出紙筆寫下——
母親:
您的兒子很想您,還將繼續實現您老思念家鄉的意愿,并建議本家新主人善待老宅,加以修繕,必要時兒子會給予幫助……
寫到這里,我恍惚中聽見“常回去看看”。幾十年不變的那熟悉濃重的膠東口音,那是母親的聲音,我抬頭,母親的音容宛在。“媽。”我起身失聲哭喊,淚水劃過我的臉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