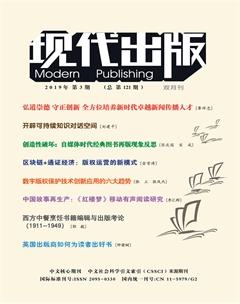西方中餐烹飪書籍編輯與出版考論(1911—1949)
郭毅
摘要:20世紀初西方出現英文中餐烹飪書籍。從追尋“純正”、強調食材的不可替代性和方法的唯一性,到西菜中烹、突出中餐作為一門可調適的“藝術”,近代西方中餐烹飪書籍的誕生與發展是特殊歷史語境下的產物,體現社會文化和閱讀興趣的變遷。近代英文中餐食譜也是一種文化雜交現象,分析這一現象對今天我國出版業踐行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也有資鑒意義。
關鍵詞:書籍史;閱讀史;美國;食譜;文化
食譜的編輯與出版正成為西方書籍史、出版史的研究對象。①食譜誕生于13世紀末的西歐,起初為手寫,僅供皇室和貴族使用。15世紀以后,作為印刷書籍的食譜不再是精英階層的專屬,它使飲食文化在更廣泛的閱讀社群中傳播與交流。作為印刷書籍的英文中餐食譜在20世紀初才進入西方家庭,成為異質文化的傳播載體。這些面向西方主婦的中餐書籍反映了西方社會對中餐文化的想象與認知,其編輯出版也體現了特定時期西方社會文化與閱讀興趣。
美國是當時西方承載華人移民最多的國家,因而是英文中餐烹飪書籍的主要出版地,出版于1949年以前的約有23種。本文使用現存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紐約州立大學“杰奎琳紐曼博士特藏”中的原始英文文獻,結合當時英文報刊中有關書評和讀者反映,力圖勾勒20世紀前半葉西方中餐書籍的編纂與出版,及其與特定時期社會文化的互動面貌。
一、英文中餐烹飪書籍的誕生
1.移民潮與“中餐熱”
伴隨“淘金熱”,1849年起大量中國勞工涌入美國,舊金山成為19世紀“各國貿易總匯之區”。當時北美華人所需日常食材多從香港通過輪船運到舊金山,再由鐵路分銷至北美各地。這些物資除供華人日常飲食之需,也為開設餐館提供了便利。據當時《紐約論壇報》記者記載,1849年舊金山就有三家中餐館。②
19世紀西方社會對華人普遍存在抵觸情緒,但中餐館卻出人意料地獲得許多白人的喜愛。即便在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后,北美中餐館也并未受影響。19世紀末開始,中餐館不斷根據西方文化需求和想象運營餐廳。③為滿足西方對中國的視覺想象,業主們選用金箔內飾、紅色燈光、豪華掛毯裝飾餐廳。為扭轉西方對“骯臟的中國人”的刻板印象,以及迎合當時風靡北美的衛生意識,中國餐館紛紛推出透明廚房,以使餐廳看上去整潔衛生。
這些做法為中餐館招徠了更多西方食客。雖然中餐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仍非主流,甚至還招致一些人的懷疑,但中餐館越開越多,越來越受到白人追捧。④1900年1月28日美國西部的《洛杉磯時報》寫道:“隨著中國餐館在各地出現,毫無疑問消費中國美味的美國人比中國人還多。”⑤1901年7月7日美國東部的《圣保羅環球報》評價道:“中國烹飪正在廣大的紐約州成為潮流。曾經只在唐人街有幾家中餐館,但現在全紐約有上百家中餐館。”⑥
2.追尋“純正”
西方在16世紀形成印刷出版食譜的習慣。伴隨北美中餐熱,報刊讀者對中餐食譜產生需求。但既無現成的菜譜可供翻譯,也無中國大廚愿向外國人傳授機宜,因此編寫中餐食譜對西方人來說困難重重,許多專欄作家只能靠想象炮制。⑦這些中國菜主要是炒面、炒飯、芙蓉蛋,以及如今被稱為“炒菜”的“炒雜碎(chopsuey)”。由于缺乏中國烹飪知識,美食專欄推出的食譜并不盡如人意。直到1932年,北美報刊的美食編輯仍然抱怨“獲得地道的中餐食譜幾乎是不可能的”⑧。
1911年3月,芝加哥《洋際報》婦女生活版編輯JessieLouiseNolton假借“中美出版公司”名義,自費印刷了《北美廚房中餐》,這是西方現存最早的由外國人用英文編寫的中餐烹飪書籍。全書共四章,計148頁,介紹了炒飯、炒面、炒雜碎、燕窩湯、芙蓉蛋等19世紀末西方流行中餐的烹飪方法。Nolton在當時以“海麗夫人”為筆名撰寫報紙婦女專欄。她的報社靠近芝加哥唐人街,因而常到那里用餐,并有機會向金燕樓的老板秦風(ChinF.Foin)請教中餐烹飪。
《北美廚房中餐》是對北美日益增長的中餐食譜需求的回應。書中寫道,“東方飽受歡迎的菜肴逐漸在西方受到歡迎。中餐的起源和烹制方法之謎增加了中餐的魅力”。由于中餐“具有其他菜式無法匹敵的無形力量”,人們常常疑惑這些美味究竟是怎么做出的。作者承諾,書中已對所有工序進行了細致描述,“只要在烹飪過程中不遺漏任何細節,每道菜都會如中國廚師做的一般”⑨。
Nolton要克服的是以往報刊食譜中存在的“不純正”的問題。她在書中首先說明地道食材之于純正中餐的重要性:“中餐不允許使用美國食材代替,所以本書不提供美國化的中餐菜譜。美式模仿缺少地道中餐的獨特口感,消解了東方烹飪技藝的魅力。”她還專門開辟一章,向讀者介紹中國食材的特殊之處。例如,中國土豆不像西方土豆那樣容易保存,香氣也易揮發。相對于西方將土豆整顆烹煮,中國土豆應削皮后切成細絲。
上菜亦要講求地道。“中式晚餐通常以果脯、米糕、果仁和茶作為前菜”,隨后才是主菜。一席地道的中餐,餐具擺放極為講究。肉脯和果仁放在小碗里,每客桌前擺放高級筷子、茶杯和瓷勺,并置一小壺醬油、食鹽和其他佐料備用。“傳統美式(用餐)供應食鹽、胡椒和黃油的方法在中餐里不被允許”。Nolton還開辟章節教讀者營造純正中餐的用餐環境,例如用百合、竹子、孔雀羽毛、中國刺繡等營造氣氛;在座位牌上繪制持傘的中國男孩或手持扇子的女傭;餐巾隨每道菜上桌,餐巾圖案必須不同。
盡管主要在美國中部地區流通,也盡管其提供的食譜在今天看來有失“純正”,但當時讀者的反應是很好的。1911年3月一位美國主婦給底特律一家報紙寫信說:“多年來我一直渴望做出炒雜碎、芙蓉蛋、蛋炒飯,以及其他我和我丈夫的鐘愛,直到發現《北美廚房中餐》,一切才成為可能。”⑩
3.“純正”的祛魅
不過,許多西方美食專欄作家堅持認為追尋“純正”的中餐是不可能的。1914年姐妹作家SaraBosse和OnotoWatanna出版了《中日食譜》。她們的父親是英國商人,母親是上海人。姐姐Sara在紐約長大,當時已憑借在《哈勃周刊》和《女士居家雜志》上刊登的一系列中國菜譜而小有名氣。?OnotoWatanna是妹妹Winnifred的日文筆名。
Bosse姐妹認為“美國所有中國廚子做的中餐,都是中國本土菜的改良版”,因此追求“地道”毫無必要。她們收入書中的食譜,“都是符合西方味覺的,也都能在西式廚房里用西式廚具烹飪”?。
有趣的是,Bosse姐妹宣稱書中食譜來自一位叫傅靈(VoLing)的廚師后代,其家族掌管上海道臺高偈(GowGai)的后廚。她們還強調“這些人物都是真實的”。但1730至1911年間的蘇松太道道員(上海道臺)中并無高姓者。有學者指出,高偈和傅靈均是虛構人物,而“作者宣稱他們真實,是以戲謔的方式顛覆了維多利亞式的對于‘地道中國文化元素的盲目崇拜”?。也有人指出,這些來路不明的食譜可能是作者編造的。事實上,Winnifred自己的廚藝十分糟糕,其丈夫總是拒絕享用她烹飪的中餐。?在北美地區很有影響的《芝加哥論壇報》美食版主編CarolineMaddocks也評價《中日食譜》:“僅供參考,并不實用。”?
20世紀初來華的西方人人數有限,對早期食譜是否“純正”缺乏評價標準,不少作者只是打著“地道”的幌子招搖過市。例如,現藏美國國家圖書館的小冊子《制作中餐的可靠菜譜》由WilliamGarner編纂,1914年出版。盡管名為“可靠”,但Garner本人對中餐佐料的認識似乎并不準確。如他認為,生抽類似英國喼汁,老抽類似新奧爾良糖漿。?
編寫中國食譜對20世紀早期的多數西方作者來說,只是中餐熱帶來的好生意。1917年伊利諾伊州食材批發商VernonGalster曾出版《通俗英文中餐食譜》,借以推銷其亞洲食品原料。以此為先聲,亞洲食品供應商考浪公司、芝加哥的明星公司(MinSunTradingCo.)、太平洋商貿(PacificTradingCompany)、哥倫比亞的東方壽友食品(OrientalShow-YoCo.)、底特律蔡氏食品(LaChoy)、伊利諾伊的比特麗斯食品(BeatriceFoods)等也紛紛編輯出版了《考浪雜碎》(How LongChineseChopSuey,1924年)、《炊食記》(MandarinChopSueyCookBook,1928年)、《中餐藝術》(TheArtandSecretsofChineseCookery,1931年)等中餐烹飪小冊子。
二、編纂理念的變遷:從中餐西傳到西菜中烹
1.“一戰”與《中菜指南》
1912年美國家庭主婦協會主席JulianHeath提倡主婦節約運動,呼吁女性“控制食物花銷、控制食物質量”?。一戰期間,其理念進一步成為流行的政治口號。這并非因為美國食物短缺,相反,美國本土的食物供應并未受到任何影響。節食是為了人道關懷,以向歐洲盟友輸送食物、救濟難民。大量美國主婦在愛國主義感召下簽訂了《國家食品公約》,但如何為家人烹制好吃、便宜又衛生的料理,成為擺在她們面前的一道難題。
在此背景下,1917年紐約華人陳肇煌(ShiuWongChan)出版了《中菜指南》,這是20世紀早期北美最著名的中餐烹飪書籍。出版商FrederickStroke為宣傳圖書,與新英格蘭地區幾乎所有報紙合作,連載書中部分食譜,以倍增其知名度。?直至1930年代,此書仍被美國報紙援引為權威中餐指南,以在家政版的讀者來信中回答有關中餐問題。?
在陳肇煌的描述里,中餐不僅菜品豐富,且營養衛生又節約成本。這部印有黑白圖片、手繪插圖的中餐書籍介紹了上百道中式美食,其中包括鹽酥雞、五柳魚、淮山乳鴿等主菜,也有馬蹄糕、揚州拉面等主食和點心;不僅介紹了高湯、豉油、麻油、腐乳等湯料、佐料的做法,甚至還清楚標注了銷售各種食材的商鋪名稱、地址和平均價格。
陳肇煌始終強調中餐的衛生。如針對西方人質疑中國臘味不衛生,陳肇煌寫道:“東方人和西方人一樣喜歡以衛生的手段保存食物。如果臘肉不凈,就不會被進口到美洲。所有食品都經醫生檢驗,因而可以自證其衛生。”?
陳肇煌通過數據展示了中餐在營養方面的高明之處。他詳細羅列出每種食物的熱量和消化時間,又列出常人每日所需攝入的熱量,進而指出肉類和菜類都不宜多食,只有比例均衡才最有益健康,而“中餐恰是菜與肉的有機結合”。且中餐味道鮮美,促使人分泌唾液,其含有的酸性成分能幫助消化。
將衛生、營養而廉價的美味帶進美國家庭,迎合了一戰期間的讀者興趣。書評稱贊:“對掙扎于飲食問題的美國主婦來說,此書的出版太及時了。那些不知如何以有限食材做出美食的人,特別是那些簽署了胡佛先生食品公約的人,那些掙扎于愛國主義與貧窮之中的婦女們,無不渴望尋求既不至家庭破產、又能吃好喝好的新點子。”21很快中國烹飪被美國人視為戰時節省日常花銷的良方。22
2.作為“藝術”的中餐
《中菜指南》還為后來的中餐食譜開辟了范式,即在介紹烹制工序的同時,講述飲食文化與歷史。書中常有類似這樣的表述:“偉大哲學家孔子教會人們科學飲食:不撤姜食,膾不厭細。如今,中國人潛意識里仍遵循古法。”書中還介紹了一些菜肴的歷史。如魚翅菜譜中寫道:“有位中國帝王在南海發現了擱淺的巨鯊。隨后廚師偶然發現魚翅可以食用,且十分鮮美。那一年是公元前50年。”《中菜指南》的這些做法被時人視作“第一次主動將中國烹飪藝術帶進寡淡無味的美國廚房”。23
中餐作為藝術是由于其蘊含的歷史文化。1932年《檀香山星公報》編輯區文勝(ManSingAu)在出版《中國烹飪》時寫道:“兩個世紀前中國作家袁枚曾說:吃飯和飲食是兩件事,飲食是一門藝術。”24因此相比分解烹制工序,他更重視介紹中餐文化。
首先,書中每頁下方都用中文、英語和韋氏拼音寫有中國飲食諺語,如“野雀無糧天地寬”“物可充腸皆美食”等。其次,在介紹每道菜的做法時,都先介紹菜肴背后的文化意涵。如在“面”大類中介紹“面寓意壽命,吃面意味著長壽”,所以人逢每十年的生日都要吃面。在“飯”大類中寫道:“中文里,米象征生命。中國客人認為燒糊的米飯或夾生飯是一種羞辱,因此主人十分重視煮米飯。”
40年代的西方中餐烹飪書籍開始強調中餐作為“藝術”的可調適性。1941年位于夏威夷的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中國分會出版了《美味珍饈》。書中寫道,“中餐是藝術而非科學”,因為“中餐沒有絕對的配方。相反,它允許廚師根據自己的口味和家庭的喜好調配”。因此書中的所有菜譜不僅是“按本地口味調適的中餐”,而且任何人都可根據自己的設想進行改造。25
3.“二戰”與西菜中烹
可調適的中餐才是烹飪的“藝術”這一觀點在二戰期間的英文食譜中得以普及,這與二戰期間的社會文化和讀者興趣有關。二戰期間,美國家庭普遍面臨可支配收入銳減和食材短缺。1943年,卷入二戰的美國再次施行食品定量配給制。每個家庭每周只允許購買4盎司黃油和28盎司肉類,每周二、五是無肉日。按一戰做法,美國主婦大可在家中烹食中餐。但問題是,中國食材的供應隨中國抗戰形勢的發展變得很不樂觀。于是,主婦們期待用美國市面上的食材烹制中餐。
1942年美國德州的西湖餐廳(SaiWooCafe)經理榮佛萊(FredWing)和家政咨詢師MabelStegner的《新中國菜譜》在紐約出版。一方面,這些菜譜既營養又省錢。“中餐講究肉菜均衡,食材過火快,鍋中用水少,有效保存了食物中的礦物質和維他命。鮮美的醬汁,增強了原料的味道。很顯然,中國人幾個世紀以前就憑直覺發現了如今我們的營養學權威通過科學研究得來的結論”。從省錢角度,“一磅痩肉搭配一兩磅蔬菜混合醬油翻炒,就能做成令人滿意、營養、足夠4人分享的主菜”26。
另一方面,該書又承諾讀者可以“用美國市面唾手可得的食材做出地道廣東菜肴”。每道菜都由榮佛萊制作,Stegner觀察記錄,將工序翻譯成英語。不僅使用“美國家庭主婦都能理解的科學烹飪詞匯”,而且對食譜作了改造。例如,在一道叫作“黃瓜蝦湯”的菜肴中,美國廚房中的西班牙雪莉酒被用來取代中餐里常用的料酒。
西菜中烹的食譜滿足了美國主婦的戰時烹飪訴求,一經出版就從美國本土銷到夏威夷,并在一年內七次重印,廣受好評。27隨著《新中國菜譜》大獲成功,1946年二人又出版了姊妹篇《舊中國菜譜》,并在其后幾年出版了增訂本,菜譜從80個增加到169個。紐約《每日新聞》的美食編輯NancyDorris贊揚榮佛萊的食譜“全部釆用美國市場上可買到的食材”,并經過Stegner的“現代化改造”28。美聯社的美食編輯CharlotteAdams則評價他們的菜譜“是最適合美國家庭的異國食譜”29。
1942年經哈佛大學教授WilliamHocking夫婦提議,楊步偉完成了296頁的《中國食譜》。全書由楊步偉撰寫中文稿、長女趙如蘭翻譯成英文、丈夫趙元任校對潤色并題寫書名、胡適和賽珍珠分別作序,賽珍珠丈夫RichardWalsh擔任出版人。由于賽珍珠夫婦在美國媒體的影響力,幾乎所有主流報紙都登出書訊,使之成為公認的中餐權威指南。
書中不僅涵蓋叉燒肉、白切雞等西方人早已知曉的廣東名菜,也有瓦片魚、酸辣湯、八寶鴨、鍋貼豆腐等川湘、江浙、河南、安徽地方菜。還有一些當時西方中餐館并不供應的中國家常菜。許多菜譜體現西菜中烹,如“美國白菜炒肉末”“香炸美國鳳尾蝦”“中式烤火雞”等。楊步偉坦誠所有菜譜都經過了自己的發揮。烹飪中餐必須“開放思想”。
《中國食譜》還新引入了一些中國烹飪概念,客觀上為西菜中烹提供了可能。這些概念包括紅燒(red-cooking)、清蒸(clear-simmering)、鹵(pot-stewing),以及最著名的熗炒(stir-frying)。其中“熗炒”一詞最終取代“雜碎”成為英文詞典中的通行語。誠如胡適在序言中所說:“如果不是趙元任引進了這些新的烹飪詞匯,中國烹飪的藝術是無法充分傳入西方的。”
三、結語
從追尋“純正”、強調食材的不可替代性和烹飪方法的唯一性,到西菜中烹、突出中餐作為一門可調適的“藝術”,近代西方中餐食譜的誕生與其編纂理念的發展是特殊歷史語境下的產物,體現20世紀初北美社會文化和社群閱讀興趣的變遷。
更進一步講,近代英文中餐書籍也是一種文化雜交(culturalhybridity)現象。文化雜交理論否認征服者的主導性文化可以完全改變被征服者的本土文化,認為兩種文化相互接觸之后往往造成雙方的改變,在交往與混雜后最終產生一種“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新的文化形態。英文中餐書籍并不只是中國食譜的簡單羅列與英譯,還是一套有關20世紀早期西方世界對中餐和中國文化的認知與想象圖式。在具體的話語實踐上,英文中餐書籍迎合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閱讀興趣,試圖以印刷媒介的形式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上植入純正而異質的中餐文化,卻在二者協商與調和中最終結成“西菜中烹”的雜交果實。
從文化雜交的角度來看,近代英文中餐書籍編纂理念的變遷生動反映了中西文化在話語層面的微觀權力運作。正如霍米·巴巴指出,當外來文化試圖以征服者的姿態改變被征服者時,常不自覺地陷入與被征服者的對話中,進而使征服者想象中自我的完整性迅速瓦解。3020世紀早期英文印刷媒介未能順利將純正的中餐帶進美國家庭,中餐話語在西方社會的文化滲透過程中,影響了本土生態,更為本土語境規定和描述。特定時空的政治經濟、社會情緒等結構化因素迫使作為外來征服者的純正中餐做出讓步,以至于令身處其時空之中的華人都不得不以編寫雜交式的食譜為榮。作為文化雜交現象的西方中餐書籍恰恰反映出在出版文化領域,一種二元對立的征服與被征服似乎是不可能的。這對今天出版業踐行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應有啟示意義。
注釋:
①HenryN.AHistoryofCookbooks: FromKitchentoPageover SevenCenturies[M].Oaklan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17.
②BayardT.Eldorado:Or,AdventuresinthePathofEmpire[M].NewYork:G.P.Putnam,186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