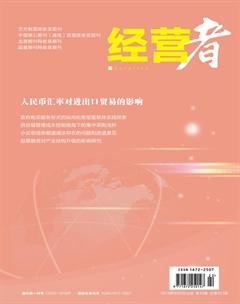論審計監督對國有企業高層腐敗的抑制作用
陳華麗
摘 要 政府審計以及內部審計能夠有效抑制國有企業高管貪腐事件的發生。審計監督通過監督和檢查國有企業的財務信息和重大事項,能夠發現企業中存在的腐敗問題。通過嚴懲腐敗高管,能夠對存在腐敗動機的高管形成威懾效應,同時也通過審計發現企業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漏洞,完善企業的內部控制和提高企業管理水平以預防高管腐敗行為。本文分析國有企業高管腐敗的現狀,尋求審計監督抑制國有企業貪腐,希望通過本文的研究,能夠為國家反腐倡廉運動貢獻一份力量。
關鍵詞 國有企業 內部審計 抑制 高層貪腐
腐敗問題不僅體現在政治權利中,企業高管腐敗問題早已存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國家開始狠抓腐敗問題,大力推行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新政風,降低了權利的舒適度,以零容忍的態度嚴懲腐敗,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還開啟了“獵狐”行動,抓捕潛逃海外的腐敗高官。其取得的成效是顯著的,2013年至今,有100多萬名黨員在反腐行動中被懲處,抓捕了150多只“老虎”,20多萬只“蒼蠅”,還有800多只“狐貍”被緝拿歸案,一大批腐敗高官在反腐敗的高壓下落馬。反腐敗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不斷打破的“禁區”和“慣例”,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反腐力度,說明“反腐”成為我國的新常態,腐敗問題成為全民的視線聚焦點。
一、前期研究回顧
王杏芬等(2017)通過研究近幾年來公布的企業高管腐敗事件,發現高管腐敗的特點。
Eric Avis等(2016)通過研究發現已經實施了的審計行為將未來的腐敗事件減少了8%,同時也將腐敗案件接受法律監督的可能性提高了21%,說明審計監督確實能夠懲治和預防腐敗。
李妍(2016)提出當前審計在腐敗治理中主要發揮以下作用:一是通過審計的威懾效應預防腐敗;二是通過審計流程的實施揭露腐敗;三是通過審計結果的公告和運用懲治、抵御腐敗;四是通過聽取審計意見完善企業的內部控制和管理制度,從源頭上遏制腐敗;五是通過審計機關和審計人員的良好自律,做表率,促進形成廉政文化氛圍。我國目前的對國有企業的審計監督形式主要有政府審計、內部審計和社會審計這3種。
二、我國國有企業高管腐敗現狀分析
(一)貪腐金額大
國有企業多為我國的壟斷行業,有國家資金的大力支持,行業競爭少,并且一般以集團公司的形式開設,集團下屬的子分公司眾多,機構龐大,部門眾多。相應的,其企業高管也擁有較大的權力,能支配更多的資金。由于我國的審計監督機制并不完善,雖然會定期開展各種類型的審計,但是審計執行到下屬層級的子分公司時,往往力度比較弱,企業高管也就有更多的尋租的空間,腐敗的金額也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僥幸逃脫積累得越來越高。
(二)國企腐敗犯罪數量多,占全國企業高管犯罪比例大
在各年度的《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統計出的各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案例匯總中,我們可以看到,相比我國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數量,國有企業高管腐敗案件數量較多,占中國企業家犯罪案件總數的比例較大。在2015年,國有企業企業家犯罪案例多達456件,占比達75.37%之多。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在2016年和2017年,國企犯罪案件占比下降到了16%左右,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在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后,全國上下開始狠抓腐敗,發現了許多隱藏的、以前未被發現的腐敗案件。而在之后,隨著各項法律法規和監管制度的完善,對國企高管有了更多的權力約束機制,使腐敗高管數量下降,腐敗預防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三)腐敗罪名多為受賄、貪污、挪用公款
在國有企業腐敗高管觸犯的罪種中排名前三的依次是:貪污受賄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財產罪。從2011—2017年的腐敗案例罪名分布中我們可以看到國企高管腐敗的罪名最多的為受賄罪,所占數量遠超其他腐敗形式,有幾年里受賄罪所占比例超過了50%。其次為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
(四)腐敗行為多集中在壟斷領域
腐敗行為多發生在權力集中型、資金密集型和資源富集型的企業,比如金融保險業、交通運輸業、能源業、化工業和新聞媒體業等。
以能源業為例,能源業包括電力和燃力兩大方面,基本上處于國有壟斷的局面。電力燃力覆蓋了生活生產的方方面面,影響整個國家的順利運轉,關系重大。能源企業分布在我國的各個省市縣中,其子分公司和相關聯的企業遍布全國,這其中企業高管掌握的權力之大、企業管理中存在的尋租空間之廣是難以想象的。同時,由于企業中存在各自的利益團體,利益鏈條錯綜復雜,想要通過制度規章明確每個人的權力、保證工作的效率和效果,是非常困難的。
(五)腐敗行為多集中在關鍵環節
腐敗行為多發生在財務管理、采購、招標和業務承攬等關鍵生產經營環節。以2016年的國有企業腐敗案件為例,在發生的109件國有企業高管腐敗案件中,腐敗環節處于日常經營過程的最多,有49件,占比為47.12%;處于財務管理過程的有18件,占比為17.31%;處于工程承攬過程的有12件,占比為11.54%;處于物資采購過程的有10件,占比為9.62%。這幾個環節存在共性,都涉及資金的流向問題,且其負責人掌握著決策的權力。
三、審計監督抑制腐敗的途徑分析
審計監督抑制腐敗的途徑可以被大致分為兩種:一是通過事前的審計監督和嚴厲處理腐敗事件,對企業高管形成威懾作用,預防腐敗事件的發生。薛健等(2017)提出,如果企業高管認為腐敗行為被發現和懲處的成本高于腐敗的收益,企業高管就會相應減少腐敗行為。二是通過審計監督發現現存的腐敗行為,利用審計結果查處腐敗,懲治腐敗。
政府審計是由政府審計機關,也就是審計署,檢查國有企業的會計賬目和重大事項,對國有企業會計信息是否準確全面、重大事項決策是否合理、資金運用是否合理等開展事前和事后監督。政府審計具有獨立性,因為審計署是獨立于國有企業之外的審計機構,接受政府部門的委托對國有企業進行審計,不受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影響,與國有企業不存在利益關系,故政府審計能夠保障其審計的客觀性。國有企業由國家擁有控制權或所有權,政府審計相當于國有企業的上級部門對其的監督審計,并且政府審計有一套較為全面的審計體系,能夠定期地或針對性地對國有企業進行審計,參與國有企業各個方面的審計,其權威性和綜合性會對企業高管產生威懾力。政府審計的獨立性、審計權威性和審計結果公開會使企業高管提高預期的腐敗機會成本,從而減少腐敗行為,起到預防腐敗的作用。政府審計的獨立性、權威性和綜合性也增加了審計發現高管腐敗行為的可能,并且政府審計通過審計結果的公開,可以引起相關行政司法部門如法院、監察委的重視,對腐敗問題展開更深層次的調查,懲處腐敗行為,懲治腐敗。在目前的國有企業高管腐敗行為的揭露中,政府審計發揮了比較大的作用。此外,由于國有企業的內部審計參與了國企的日常經營管理,國企一般會每年請會計師事務所對其進行審計,不太好區分某年內部審計和社會審計是否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審計,三種審計方式對高管腐敗的威懾作用和治理機制是相似的,只是在審計實施主體上有區別。
四、研究建議
(一)加大審計力度
從思想上提高對審計的重視程度,避免審計浮于表面、流于形式,也避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情況發生。可以通過公開審計流程和審計結果,提高審計的透明度;還可以以查處腐敗涉案金額較大的審計項目為突破點,大力宣傳,吸引媒體和公眾關注審計監督,讓大眾認識審計的重要性,共同參與審計監督。
(二)合理分配審計資源,避免審計盲區
加大審計力度需要精準施力,合理地配置審計資源。目前我國各地區的審計力量是不均衡的,審計力度之間存在差異。經濟發達地區通常比較關注、重視審計,這是必要且有效的。而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我們也不能忽視審計監督的重要性。貧困地區往往由于人財物力的不足而缺乏審計監管,存在比較嚴重的腐敗情況,因此要加大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審計力度,合理分配審計資源,避免審計監督存在空白區域。對于腐敗高發的重點領域如金融保險業、交通運輸業、能源業等,重點崗位如財務管理、采購、招標、業務承攬等,也要相應加大審計力度,有針對性地審計,避免審計資源的浪費,從而提高審計的效率和效果。此外還要提升審計人才專業素質,提高審計執業水平。
(三)建立審計協同機制,提高審計結果利用率
審計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出具一份審計報告,而是通過審計確保財務信息和重大決策的正確性,同時發現問題并及時改進,以幫助企業更好地發展。除了要加大審計力度,還要加強對審計結果的利用。這就需要審計部門與政府相關行政和司法機關如監察局、中紀委和法院等協調配合,實現信息的共享和互通,這不僅能幫助審計工作更好地開展,更有利于專職的部門及時處理和解決審計結果中發現的問題,防止類似問題再次發生。協同機制中不僅包括政府審計,還應重視內部審計和社會審計的成果。相關政府機關也要關注國有企業的審計報告,抓住問題的線索,及時處理問題。比如審計人員在工程項目審計中發現存在虛報工程款、重復計算等問題,工程項目負責人可能存在貪污行為,但審計人員并沒有直接處置項目負責人的權力,可以通過協同機制,將這一審計結果報送監察局,協同監察人員展開調查,搜集證據,讓腐敗人員得到應有的懲罰。
(四)建立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勵制度,抑制高管腐敗動機
國有企業高管腐敗的內在動機之一就是受到金錢和利益的誘惑。在審計監督制約了高管腐敗的外在條件的情況下,也要加強對高管腐敗內在動機的制約。可以適當地提高高管的薪酬,使其保持比較高的生活水平,金錢的誘惑就會顯得不那么大了。高管在衡量腐敗的成本與收益時,考慮到現有的薪資水平和較高的生活水平,考慮到腐敗行為被揭露后需要面對的嚴厲的懲處,會有得不償失的感覺,從而拒絕腐敗。國有企業可以建立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勵制度,減少政府對國企高管薪酬的管制,建立以業績為導向的市場化薪酬制度,把高管薪酬與企業業績掛鉤,高管為了獲得更高水平的薪酬就會努力工作以提高企業業績,而非尋求腐敗。
參考文獻
[1] 王杏芬,金鑫,曹茹玥.審計視角下企業管理層腐敗治理路徑探索[J].會計之友,2017(13):97-102.
[2] 李妍.我國政府審計和腐敗治理[J].商業會計,2016(03):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