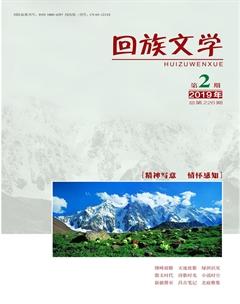推拿師的主持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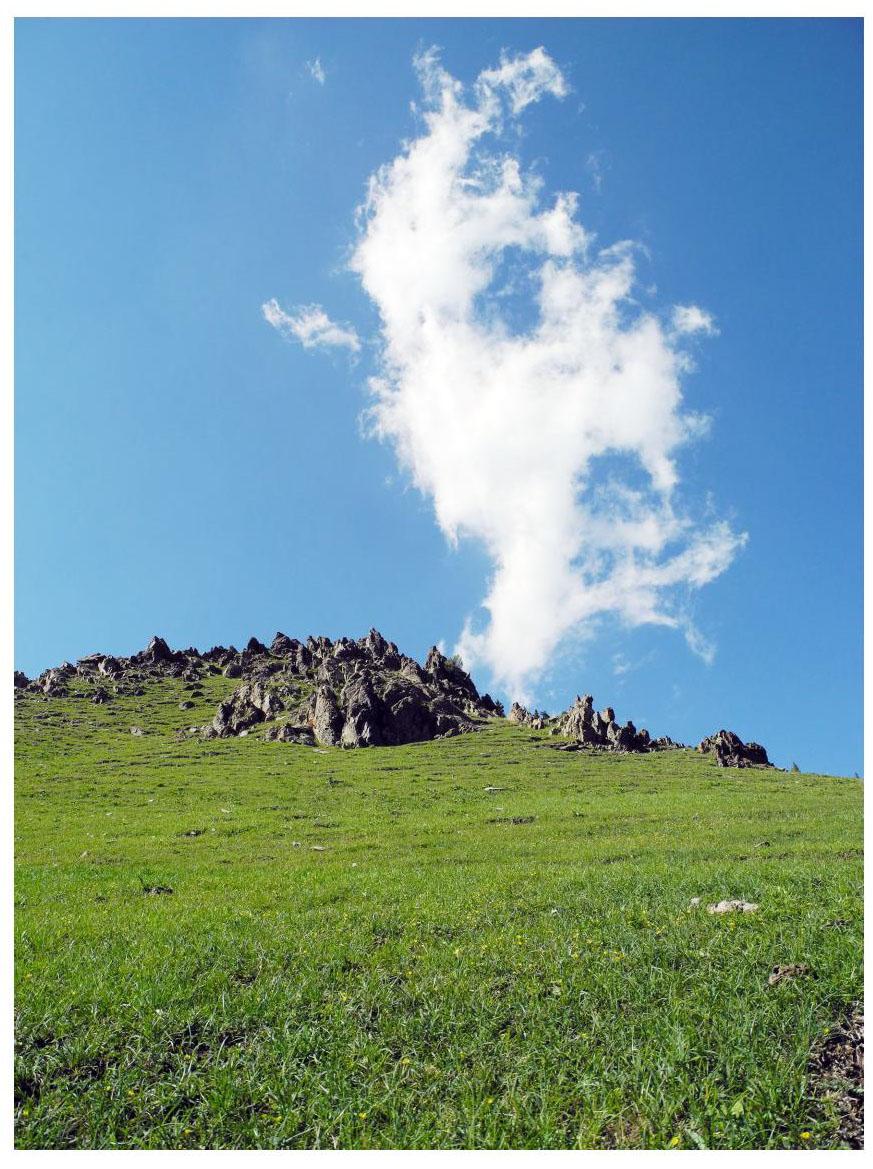
一
他越來越安靜了。
每當他出現在人們的視線里時,人們總是這樣小聲地嘀咕著。可不嘛,以前聽到別人和他打招呼,他總是笑瞇瞇地尋聲迎上去,并與之握手、攀談。他笑起來的樣子,很迷人,兩只小眼睛似兩彎月牙,清澈明亮;小酒窩淺淺地印在臉上,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渾身散發著一種天然的親和力。盡管他什么也看不見,但是,他表現得大大方方的,像個健全人一樣。相反,跟他打招呼的人卻時刻賠著小心,有點唯唯諾諾。
他叫趙靖,巷子里的人都叫他趙醫生。趙醫生三歲前的世界是明亮的。三歲時,他發高燒,家里沒錢,耽誤了治療,導致他的視神經被嚴重損壞。從那時起,他的眼睛便蒙上了一層霧,看什么都霧蒙蒙的,而且越來越模糊,家人為此四處籌錢,為他的病奔波,可還是沒趕上他視力模糊的進度。最終,他陷入了黑暗,那一年,他六歲。
六歲的趙醫生,每晚臨睡前,總是做同一個夢,夢見自己第二天早晨,睜眼看見了躺在床上的玩具狗熊,看見做飯的媽媽,還看見擱在窗前的那盆開著黃色小花的雛菊……可是,第二天,他依舊什么都看不見。他把自己的上下眼皮使勁往兩邊扯,眼前的黑暗仍然嵌在眼睛里,紋絲不動。直到進入盲校后,他才慢慢地習慣黑暗的陪伴。
二
在盲校讀中專時,趙醫生選擇的專業是播音主持。播音主持可是個出風頭的好專業,每天傍晚,趙醫生的聲音鉆進教室、溜進食堂、穿過宿舍,響徹學校的各個角落。他的聲音有點與眾不同,聽著很舒服,很溫暖,很柔滑。每一個聽過他聲音的人都說這是他(她)聽過最特別的聲音。趙醫生就這樣成了學校的“風云”人物。
與他一起主持校園廣播的還有他的好哥們李平。說起李平,趙醫生不得不感慨緣分。他倆是在中考的考場上認識的。那天,趙醫生的盲文尺不小心掉到地上,鋼與地板碰撞出清脆的響聲瞬間淹沒安靜的教室,趙醫生慌忙循聲彎腰去撿,李平聽到聲音后,也俯身去撿,兩雙手就在摸到尺子的一瞬間,觸碰了。趙醫生激動地連聲說:“謝謝,謝謝……”盲人就是這樣,最怕的就是掉東西,可不嘛,東西像個調皮的孩子,一撒手,就拼了命地四處撒野,有時候,找都找不回來。幸運的是,趙醫生掉的是個不怎么撒野的孩子,可是撿起它總得費工夫吧,這么緊要的關頭,時間就是救命的水,容不得一丁點兒的浪費,他能不激動嗎?李平則輕輕地拍了拍趙醫生的手,平撫道:“快答卷吧。”
答完試卷,趙醫生和李平像商量好似的,同時挪動桌椅,并先后交了卷。他倆走出教室后,不約而同地問了對方一個問題:你叫什么名字?問完后,兩人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是那種相見恨晚的笑,是那種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笑。那個下午,他倆聊了足足四個多小時,從天文到地理,從北京到烏魯木齊,從主持到推拿,從螞蟻到公雞等等,等等。
讀中專第一天,巧了,趙醫生和李平被分到了一個宿舍。這個喜人的炸彈,在他倆心中猛地炸出一朵花,他倆激動地擁抱、尖叫、狂笑,這舉動驚著了同宿舍的每一個人,可是他倆已經管不了那么多了,驚就驚著吧,日后再解釋,反正有的是時間。
中專一年級第二學期,他倆同時選擇了播音主持這個專業,并在校園廣播站為同學們服務。他倆的聲音,一個柔和,一個剛硬;一個綿長,一個簡短。各有千秋,不分伯仲。在校園里,他倆一起吃飯,一起讀書,一起鍛煉身體,似乎日子可以一直這樣持續下去。
可是,中專三年級開學第一天,李平卻換了專業——推拿,這讓趙醫生一時無法接受。怎么能接受呢?他倆說好的,要學好播音主持,后面還要到電臺實習呢,怎么一個暑假結束,就全變了呢?就算要換專業,你李平也提前跟我說啊!你這樣一聲不吭地把事情辦了,把我當什么了?趙醫生想不明白,很不明白。他知道消息后,震驚和火氣同時涌上心頭,一上午都沒和李平說話,說什么呢?有什么可說的,說了也沒多大意義!
午休時分,同為上鋪的趙醫生和李平頭對頭躺著,趙醫生就覺著他倆中間隔著一塊巨大的黑幕,他很想把這塊幕掀開一探究竟,但是他忍住了,他在等,等李平把這塊幕掀開。
晚飯過后,趙醫生一個人在校園里恍恍惚惚地走著,不知不覺,他來到了操場的一處角落,這兒曾經是他和李平一起談天說地的伊甸園,可是此刻,卻只有他一個人,一種說不出的落寞和憂傷頓時襲上心頭,他禁不住長長地噓出一口氣。突然,他的肩膀被人輕輕地拍了一下,是李平,他心頭一喜,剛準備轉身和李平說話,腦海中閃過他轉專業的事兒,心頭那股驚喜的火焰瞬間熄滅,他決定不搭理李平。這時,李平像在自言自語地說:“當我的身體接觸到一位盲人推拿師的手時,一種從未有過的真實撞擊著我的心臟,我知道我這輩子只能選擇它了。”
趙醫生一聽,心撲通一下,滑進了一個看不見底的冰洞。過了許久,他開口了,一開口,就顯示了他骨子里與生俱來的執拗,“我想試試。”
李平什么也沒說,只是拍了拍趙醫生的肩膀。李平的確也沒什么可說的,在這個世界上,他還沒見過有哪個行業非需要他們這種人不可。
三
雖然趙醫生理解李平,可是隨著專業的不同,他倆的心也漸漸地遠了。
這一學期,正是中專三年級學生的實習期。趙醫生一心想去電臺實習,他把自己的簡歷發給電臺后,開始了漫長的等待。這等待是折磨人的,趙醫生早晨一睜眼,腦海中就閃出關于電臺應聘的事,晚上,也是遲遲不睡,生怕一不留神錯過電臺的錄用消息,可結果卻總是遙遙無期。萬般無奈下,趙醫生打通了電臺的座機,工作人員告知他,他們不接受盲人實習生。趙醫生聽到這個答復,感覺自己光溜著身子,站在評委們面前,接受他們的評頭論足,尷尬死了。
晚上,趙醫生問了李平一個嚴肅的問題,他說:“你覺得我們瞎子有必要活在這個世界上嗎?”
這個問題聽起來嚴重了,都提到生死的高度了。李平不知道該怎么回答這個問題,但是他丟給趙醫生一個哲學命題,“存在即合理。”
第二天,趙醫生像撒網一樣,把自己的簡歷投給三十余家電臺、網絡公司、盲校等五花八門的單位。沒過幾天,趙醫生的魚居然上鉤了。一家網絡公司主動給他打電話,同意他去實習。這個消息,著實讓趙醫生高興了好幾天。
實習第一天,趙醫生把自己可勁捯飭了一番。他上身穿一件白色襯衣,下身搭一條黑色西褲,外蹬一雙锃亮的皮鞋,精精神神地上班了。
對于上班的路線,趙醫生已經在前一天下午踩過點了,所以早上九點五十,他已穩穩當當地站在了他上班的地方,還早到了十分鐘呢。早到的他,發現自己并不是第一個到單位的,他聽見大廳里打電話的聲音、敲鍵盤的聲音、人們交談的聲音,還有高跟鞋發出有規律的聲音。
“請問你是趙靖嗎?”趙醫生聽見他對面傳來一個溫柔的聲音,頓時就是一陣緊張,連連結巴地說:“額,是的,是的。”說完后,他感覺那人一直在盯著他看,從頭到腳地看。他的血唰地全沖到臉上,自卑感也瞬間充盈全身。
“跟我來吧。”溫柔的聲音說完,就扶著他的胳膊走。
“謝謝,我自己可以的。”趙醫生有點不自在了。
“沒事兒。”溫柔的聲音依舊堅決地扶著他。
到了錄音室,溫柔的聲音把趙醫生安排到一張椅子上坐下,順手遞給他一份錄音稿。
“你先熟悉一下這篇稿子,待會我……”溫柔的聲音說到一半,好像突然意識到什么,戛然而止。
趙醫生手里摩挲著稿紙,額頭上急出一層汗。他在盲校,學的是盲文,是由一個個凸出的點構成的字。在校園廣播站,每次播音前,他總是先用盲文寫好稿子,然后才開始播音。可是現在,手里的這張稿紙,對他來說,就是一張廢紙!他突然意識到,這個由健全人構成的圈子,和他所處的圈子壓根就不是一個天地。他坐著也不是,站著也不是,感覺整個身體的筋骨瞬間錯位。
“你先坐會,我出去一下。”溫柔的聲音為他解了圍。
溫柔的聲音帶著她的皮鞋聲消失后,趙醫生的眼淚不爭氣地流了出來,他趕忙用袖頭擦掉。在趙醫生看來,眼淚是弱者的標簽,他怎么會把弱表現在一個健全人的面前呢?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當皮鞋聲再次響起時,趙醫生做好了決定。
“對不……”溫柔的聲音剛一發出,就被趙醫生打斷了。
“不好意思,我最近學校里有點事,不能在貴單位實習了,抱歉。”趙醫生努力從臉上擠出一個笑,然后,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這棟大樓。
在后來的日子里,趙醫生總是不自覺地想起這一天。這的確是一個讓人難忘的日子,因為這一天,趙醫生做出了一個關乎他命運的決定——學推拿。他是半路“出家”的,學起來自然要比別人多付出成倍的時間和精力,才能跟得上老師和同學們的進度。一開始,趙醫生像只老鼠,把自己埋在黑暗的角落里,死記人體的各個穴位。等到了實踐課時,趙醫生的問題來了,他連最基本的穴位都找不準,同學的后背,寬,還厚,和書本上的人體圖壓根就不是一回事兒,趙醫生傻眼了,無從下手了,只好在同學的后背上一陣亂揉,同學和他笑作一團,打鬧起來。等笑夠了,實踐課也結束了,趙醫生的心里卻生出了許多惆悵,眼瞅著就要畢業了,自己卻沒有學到一個養得活自己的手藝,這算怎么回事嘛!趙醫生像孤魂一樣,一個人游蕩到操場,坐著,“看”遠方。不知什么時候,李平坐到了他跟前,什么也沒說,只是靜靜地坐著,像是知道他的全部心事。
“下節實踐課,我和你一起練吧。”李平不經意地說著。
趙醫生有點不好意思了,但終究是自己的哥們,他沒有做任何的扭捏之態,也輕描淡寫地“嗯”了一聲,兩人便隨著黑夜,進入了長久的沉默。
結果終究是如人所愿的,趙醫生和李平一起從推拿專業順順利利地畢業了。他倆因推拿分道揚鑣,又因推拿和好如初,世上的事,大抵都是如此,冥冥之中,總有一根線,在牽扯著對方。
四
五年后,趙醫生用他給別人揉背捏腳掙來的錢,在一個巷子口,開了家推拿所,并大大方方地起名為“趙靖推拿中心”。開業那天,來的人很多,包括李平以及后來讓趙醫生一想起就心疼的邢小影。
說起邢小影,話匣子就打開了。 她的失明來源于一場意外的車禍。當時,她正準備市里的一場主持人大賽而背誦著解說詞,由于背誦得太投入,竟忘記了紅燈的提醒,徑直朝馬路走去。突然,一陣尖利的汽笛聲灌入耳中,她一回頭,巨大的車頭已到她的眼前,然后,她就什么都不記得了。當她從醫院醒來時,醫生告訴她,雖然她的眼睛看不見了,但是她能活下來,已經是個奇跡了,所以好好珍惜吧。可是,對于邢小影來說,眼睛都看不見了,這算哪門子奇跡!簡直就是硬往自己臉上貼金嘛。邢小影剎那間就胸口噴火,簡直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你哪怕是斷胳膊斷腿也行啊,至少還可以看得見,這眼瞎了算怎么回事嘛!她把自己的憤怒一股腦全發泄到醫生那頭,就連父母都牽連進去。一連鬧了兩天,她把自己弄得疲憊至極,最后在母親的懷里睡著了。睡著的她,夢見母親跪在醫生的面前,求醫生救救她的女兒,那一聲聲凄厲的哀求,刺痛著邢小影,她跌跌撞撞地跑過去,跪在母親面前,攬著母親,哭著說:“媽媽,我不治了,不治了,瞎了挺好的,這個世界我已經看夠了。”母親的眼睛紅腫著,眼淚布滿溝壑縱深的面龐,她一把拉過邢小影,死死地抱住她,扯著嘶啞的嗓子說:“影兒,影兒,把媽媽的眼睛拿去,把媽媽的眼睛拿去……”母親的頭埋在邢小影的脖子里,眼淚全打在她的脖子里,溫熱溫熱的。醒來后,邢小影摸著母親濕漉漉的面龐,開始了號啕大哭。哭過后,她咬了一口自己的嘴唇,對母親說:“媽媽,沒有眼睛沒關系,我還有你們呢!”
邢小影是個倔強的孩子,老天讓她失去眼睛,想毀了她的生活,可她偏偏就不讓老天得逞。她進入盲校后,學習盲文,閱讀大量的經典書籍,同時,也學習推拿,她想,沒有眼睛怎么了!我一樣可以看書寫字做推拿。可是,她倔強的背后,卻有一種說不出的疼,她從此與出鏡主持人無緣了,因為她從來就沒有見過有哪個盲人出鏡主持節目的。試想一下,如果一個盲人主持節目,那節目嘉賓和觀眾心里是個什么滋味?還是現實一點,安心做推拿吧。
時間是一場春風,“潤物細無聲”。邢小影的傷口在不知不覺中,被一點點治愈,她漸漸地習慣了做一個盲人,喜歡一連幾個小時,靜靜地坐在窗前,或讀書,或冥想,或憧憬。總之,一切都靜了下來,慢了下來。
畢業那天,邢小影想讓自己在學校的最后一天和其他時候不一樣。她大膽地走出學校,沿著校外那條被她走了無數次的路,慢慢地往前走著。六月的清晨,陽光灑在臉上,暖暖的,很舒服。晨風挑逗著邢小影,時而將她的長裙掀起一角,想一探內里究竟;時而把她的一縷頭發吹到天上,然后再輕輕地落到她的面頰上,如此這樣,三番兩次。小路兩邊開滿了郁金香,邢小影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香味隨著呼吸道慢慢地進到身體內里,她忍不住說了聲“好香”。這時,邢小影聽到,四只腳,兩個人,從她身邊經過,一個小女孩奶聲奶氣地說:“媽媽,這朵郁金香好漂亮呀!”邢小影的身體突然被什么東西扎了一下,就一瞬,但很疼。同樣的場景,曾經也出現在她的身上,只是,今非昔比,她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女孩。她印象中的郁金香是模模糊糊的黃,她都快忘記郁金香長什么樣兒了,她嗅著郁金香的香味,手忍不住慢慢地尋著,想摸一摸郁金香的樣子,她的手摸過扁扁的花葉、長長的花枝,終于,她的手摸到了郁金香的花瓣,那是怎樣的動人心魄啊,邢小影就感覺自己的心已經準確無誤地落到了郁金香的花瓣里,變成了花蕊,火紅火紅的,還能一跳一跳呢。她的眼淚突然就成串地落到郁金香的花瓣上,然后流進花蕊里,整個花蕊頓時顯得眼淚汪汪的。
突然,邢小影的右邊隱隱約約傳來一陣噼里啪啦的鞭炮聲,緊接著是一段講話。這講話的聲音有點特別,很清新,又很纏綿,雖說是講話,卻有種念情書的感覺。邢小影忍不住朝發出聲音的方向走去。原來是一家推拿中心舉行開業儀式,邢小影剛走到門口,講話就結束了。無數只腳開始朝不同的方向邁去,不一會兒,嘈雜的人聲也漸漸遠去。邢小影站在門口,想尋找剛才講話的聲音,但轉瞬一想,找著又怎樣呢?她禁不住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準備原路返回。
“您好!您是我們老板的朋友嗎?” “趙靖推拿中心”的前臺小張見門口站著一個人,便走出來問,見邢小影沒有回答,這個急性子的東北小妞便盲目地認為她肯定是老板的朋友,于是二話沒說,上來就親熱地挽著邢小影的胳膊往店里“請”,嘴里還說著“開業儀式都結束了,你怎么才來呀?”好奇心真是個奇怪的東西,它可以讓一個從不說假話的人說假話,邢小影就是如此,為了再一次真切地聽聽那個特別的聲音,她對小張閉口不言,既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剛一進門,一陣清幽的音樂如沐春風般滲進邢小影的體內,她感覺自己的身體好像不受自己控制,有點肆無忌憚地飄了。
“老板,您的朋友到了。”小張說著,把邢小影拉到趙醫生面前。此時,趙醫生正在和李平以及其他三個朋友聊天,聽小張這么一說,有點懵了,怎么回事?我的好朋友都在這兒啊,難道是把誰落下了?趙醫生在腦海里快速過了一遍,沒錯啊,都在呢,會是誰呢?
“歡迎歡迎,”趙醫生按照以往的習慣,客氣地對這位不明身份的朋友說著,靜靜地等她自報家門。等了半天,還是沒有動靜。“額,您看,我的腦子不好使,把您給忘了,是我的錯,我自罰一杯,啊。”說著,拿起面前桌子上的茶杯就要喝。
“我不是你的朋友。”邢小影尷尬地說,但還是被趙醫生的聲音吸引住。
“額?”趙醫生舉著茶杯,“那請問您是來做推拿的還是應聘的?”
“應聘的。”邢小影鬼使神差地說出這句話,把她自個也嚇了一跳。
趙醫生仿佛松了一口氣,他放下茶杯,說:“咱們推拿中心看重的是技術,就讓我見識一下您的手藝吧。”趙醫生說著,就朝最近的一個推拿房走去。邢小影剛上中專一年級,就學習推拿,所以她的推拿技術自然不在話下,于是也大大方方地隨趙醫生去了。
正式上班后,邢小影還是覺得像做夢一樣。出個學校,散個步,竟然把工作的事兒解決了,人生真是不可預測。
五
趙醫生發現邢小影的秘密,是在邢小影來推拿中心八個月后的一天下午。
那天下午,整個天空低沉沉的,陰著臉,像受盡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淅淅瀝瀝地下個不停。推拿中心沒有生意,所有的推拿師都在休息區休息,趙醫生也在,他和別的推拿師們閑散地聊著天。過了一會兒,他發現邢小影不在休息區,大雨天的,她不在休息區,又在哪呢?這個邢小影,平時休息的時候,就只是安安靜靜地坐在休息區,極少說話,遇到非說話不可時,也只是吐出簡短的幾個字,但是與客人聊天時,她的話匣子卻一下子打開了,談論的內容涉及范圍很廣,大則天地哲學,小則吃喝拉撒,無所不談,無所不扯。有一次,趙醫生意外地聽到邢小影竟然與客人討論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同性戀題材的長篇小說《孽子》,著實把趙醫生吃了一驚。你聽聽邢小影是怎樣與客人討論這本書的。
“白先勇先生的這部唯一的長篇小說,是他在同性戀題材書寫的一個高峰,他大膽地集合了過去在同性戀題材中所關注和思考的所有焦點。”
“為什么這樣說呢?”客人有點不解。
“因為它是第一篇以同性戀生活為主題的小說,他之前的作品只是表達一種難以言傳的同性戀情緒罷了。《孽子》這本書,在具體的生活里,摻雜著邊緣人的苦痛與無奈,寫得哀婉凄美。”
客人像聽懂了一樣,仰起脖子,長長地“哦”了一聲,然后陷入無限的沉思。
趙醫生走出休息區,打開一間間推拿房,尋找邢小影的身影。不知為何,趙醫生一見不著邢小影,就有點心慌,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是什么時候才有的這種感覺呢?也許是看完深圳衛視播出的《溫暖在身邊》這一檔欄目里的主人公盲人主持董麗娜之后吧。那是去年離春節兩天前的一個夜晚,店里沒有生意,他和推拿師們在休息區里隨意翻“看”電視,無意中發現這期節目。看完節目后,所有盲人的臉上都掛滿淚水,他們哽咽著,用袖頭一遍又一遍地擦著不斷涌出來的淚水。這時,一個聲音回蕩在一片淚水中,“趙老板,您以前學的專業就是播音主持吧?”趙醫生心頭一顫,思緒一下子拉到那棟網絡公司的大樓里。在那個青澀的年紀,他的確沒有像董麗娜那樣執著,自我放大的自尊心活生生地把他拋出了主持人的位置。現在,再次接觸到主持人這個身份時,他除了從身體掠過一絲若隱若現的疼之外,剩下的也只有慚愧了。“額,以前的事還提它做什么,人呢,還是要往前看的。”趙醫生說這句話的時候,是笑著的,然而,他的心里到底是難受了,有種被人揭了傷疤的感覺。邢小影卻在這個時候有點不識時務了,她說:“為什么放棄了?”她對趙醫生此時的處境感同身受,可不嘛,當年的她,學的也是播音主持,只是飛來橫禍,迫使她選擇了推拿,主持這個缺憾則成了她心里的一塊疤。隨著推拿的學習以及工作之后,疲憊和生存早已擠滿她的內心,而這塊疤也早已被自己封存在心里的某個角落,并落滿了灰塵。而今,這期節目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這塊傷疤擦得明晃晃的,疼得她不敢呼吸。當得知趙醫生以前也是學播音主持后,她想他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樣,此時,正接受一場傷疤的擦洗呢?趙醫生沒有回答她的問題,緩緩地走出休息區,留給她一串失落的腳步聲。邢小影在這個晚上來勁兒了,她追出去,抓住趙醫生的胳膊,說:“你現在是不是很難受?因為我很難受。”這是什么邏輯,趙醫生就覺得這丫頭魔怔了,反問她:“你為什么難受?”邢小影說:“因為我以前學的也是播音主持。”趙醫生被這句話怔住了,他不知道該如何接邢小影的話。邢小影被這個節目徹底刺醒了,她覺得自己這一輩子還長,不能只活在疲憊與生存之間,她應該還有另一種可能,而趙醫生也應該如此。“我們繼續學播音主持吧?”邢小影鼓足了勇氣,說出了這句話。“怎么可能!”趙醫生說,“那是一個完全和盲人不一樣的群體。當我置身其中時,我仿佛被無數雙眼睛拉到了天的盡頭,在那里,我看不見一個人,聽不見一個聲音,我被世界拋棄了!”
趙醫生走到最里面的一間推拿房,握住門把,剛準備推開,卻聽到邢小影斷斷續續的聲音,像是在打電話。“是的,是的,我報名了。”“嗯,我曾經參加過市里舉辦的主持人大賽。”“好,我下周一去面試,謝謝您。”
“她到底還是要走。”趙醫生的眼淚在眼里打圈,他仰起脖子,努力把眼淚咽下去。可他哪里知道邢小影的心思,自從看完那期節目,并與趙醫生談話后,邢小影死心眼了,我就不信,她董麗娜從來沒有學過一天播音主持,最后都能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主持節目,憑什么我就要在這里給別人揉背捏腳!還有你趙老板,以前也是學播音主持的,我就不信你看完這節目,能無動于衷?笑話,說白了,你現在只是恐懼,怕再一次失敗,因為你身邊還沒有這樣一個成功的案例,那就讓我心甘情愿地做你的炮灰吧,如果我不被炸死,那你就能開啟新的人生了。
六
邢小影走了,她走得那樣突然、決絕。盡管趙醫生知道她的離去是必然的,可是當邢小影真真切切地離開后,他還是有點傷感和失落。
一個月后,邢小影來電話了。“趙老板,我已經成功通過面試了。后面如果順利的話,我可能會做電臺主播!”邢小影在電話那頭熱情洋溢地講著她到新單位后的種種新奇事兒,趙醫生則走神了,她怎么就那么大膽呢?她就不怕孤獨嗎?她就不怕被健全人當作異類嗎?趙醫生有點惶惑了。
大約半個月過后,邢小影的電話又來了,她告訴趙醫生,她已經開始為一家電臺錄制節目了,后面將會出鏡主持活動。這番話,聽著有點蠱惑人心了,趙醫生重新把六年前的那個早晨拿出來,仔仔細細地捋了一遍,他開始懷疑自己當初所做的決定,難道我真的錯了嗎?難道盲人真的能融入健全人的圈子里嗎?趙醫生就這樣反復地問著自己。
邢小影的來電,像一陣寒風,每吹過一次,都讓趙醫生打一陣寒戰,即使寒風已經遠去,寒氣依然長久地留在趙醫生的心里。后來,邢小影這陣寒風迷失了方向,再也沒有吹進趙醫生的心窩。趙醫生緊抿著嘴唇,右手拿著手機,兩眼盯著手機屏,右手大拇指不住地摩挲著手機屏,像撫摸邢小影的身體。也許邢小影現在已經主持了很多次活動了吧,說不定此時,正在和新交的男朋友約會呢,趙醫生想到這兒,心像被誰撕了一下,很疼。他去推拿中心旁邊的超市,買了生平第一瓶白酒,然后像做賊一樣揣到懷里,偷偷摸摸地鉆到最后一間推拿房里。趙醫生打開酒瓶,聞了聞,一股辛辣刺鼻的酒味全灌到他的鼻子里,他的身子本能地顫抖了一下,他想,人為什么就這么作賤自己呢?這么難喝的東西,還要當寶貝供著,但轉念又想,不!我要喝,我要放縱,我已經兢兢業業地活了二十八年了,可還是一無所有!趙醫生突然悲從中來,端起酒瓶就往嗓子里灌,這一灌不要緊,差點把他岔過氣,他就感覺自己的嗓子里剛剛漫過一股滾燙的辣椒水,所經之處,都已是千瘡百孔,可這肌膚之痛與他整天被邢小影和主持糾纏的撕裂之痛相比,實在也算不了什么。喝,喝死算了,趙醫生像為自己加油似的,又是一陣猛喝,可是這一次,卻好像沒有之前那么難喝了,反而還有點若有若無的酒香味。
酒喝到一半,趙醫生的身體有點晃悠了,腦袋卻清醒了,為什么要干巴巴地等著邢小影的電話呢?為什么自己不打呢?真是傻到家了,趙醫生邊說,邊拿出手機,撥通了邢小影的電話。等了半天也沒人接,再一看手機,他大爺的,沒有打出去。再打,這一次,電話通了。
“趙老板?”
“嗯,嗯?您是?”趙醫生聽到一個老人的聲音。
“我是小影的媽媽,您是趙老板吧?謝謝您對我們家小影的照顧,我們家小影生前就一直念叨您的好呢。”
“什么?生前?”趙醫生像彈簧一樣,彎著的身子一下子拉直了,腦袋里運轉的機器轟的一聲,坍塌了。
“您不知道?小影上個月出了車禍。”電話那頭的老人已是泣不成聲。
奎國芳,女,漢族,90后,甘肅古浪人,新疆作家協會會員,大地生長·新疆中青年作家班學員。作品散見于報刊、文學網站等,評論《解析<鑿空>中的焦慮意識》《多面李娟及其困境》《牙印,一個命運的符咒——解讀劉慧敏短篇小說<牙印>》發表在《昌吉學院學報》(文學藝術研究版)、《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文學期刊《伊犁河》,多次負責、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