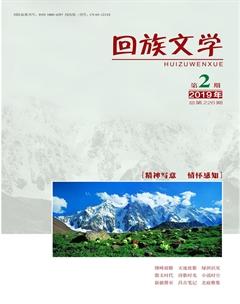四十年前向《博格達》創(chuàng)刊號問好
蔣永軼
歲末年初,回顧改革開放成果時,突然發(fā)現(xiàn)了四十年前本土文學刊物《博格達》(《回族文學》前身)的創(chuàng)刊號,頓時使人思緒萬千,這不也是改革開放在我州文化方面顯現(xiàn)出的成果嗎?創(chuàng)刊四十周年,恰是早到的春訊,使人倍感親切與溫暖。除了為當時的組織策劃者點贊外,又有幾分羞怯與陌生。特別是看到四十年前有幸刊在創(chuàng)刊號上拙文的標題,就像見到了久違的孩子,更多的是親切與歡欣。回顧這四十年刊物發(fā)展的漫漫修遠路,除了感慨之外,也想就當時親身經歷與刊物息息相關的點滴碎片寫下只言片語,供更多參與者、老師、朋友們共勉。
《博格達》的催生會
四十年前,兩次部門間的協(xié)調會,在行政機關當時或許只是個小小的插曲,可是對于《博格達》,卻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1979年,庭州大地也和全國一樣沐浴著改革的春風,醞釀著千樹萬樹含苞待放的梨花。地方各級機構逐步走向規(guī)范化。兵地體制嘗試性地進行了一些整合,經濟要發(fā)展,社會需要安定,政策亟待落實,各種矛盾相對突出。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人們的思想相對比較活躍,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如何將大家的積極性凝聚起來,形成合力,為經濟發(fā)展提速,為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而奮斗,是黨委和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文化這面旗幟形成合力,凝聚人心,這是那時整個社會的共識。社會需要文化引導這面旗幟與平臺,特別是本土文化平臺,必須要真實地反映人民群眾的心聲,這樣就可能產生零距離效應。《博格達》的誕生是時代的產物,是黨委和政府的正確決斷,是隨著改革春風成長起來的有一定群眾基礎的本土文學刊物。
穿越時空的隧道,讓我們一同走進當時的那個部門協(xié)調會吧。那是1979年五一過后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丁零零”,桌子上那部黑色的老式電話響了。接起電話,還沒等我說“喂”,對方的聲音就急促地傳過來了。
“部長讓你們陳主任五點去宣傳部參加部門協(xié)調會!”
“陳主任去天化了,還沒回來。”
“那你去給部長匯報一下!”
辦公室施主任掛斷了電話。時間馬上到了,我非常著急,正準備出門,看到部長張尚信從常委樓向這邊辦公室走了過來。我便迎了上去,報告了陳主任出差的事。他用同等的頻率繼續(xù)向前走著,好像根本沒有停下聽我說話的意思。張部長是來自兵團農六師的領導,雖是帶了個“農”字,但潛在的軍人作風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事業(yè)心強,行動速度快。盡管五十多歲的人了,給人的感覺就像年輕人一樣。作風嚴謹,工作效率高。對部下要求非常嚴格,但生活上非常關心。現(xiàn)已年逾八旬,不管兵團還是地方曾經與他共過事的同僚與下屬,都常提起他,至今非常想念他。
我正在不知所措時,他回過頭看了我一眼:“那就你去吧!”我的頭好像被什么擊了一下,頓時有點懵了,“我……”本意是我去不合適,除了什么都不知情,我的手續(xù)還沒辦呢!嚴格來說我還不完全算組織部的人。但當時的確人少事多,也沒有辦法。他回過頭,“本來就是你們科室的事,你不去還有誰去?”我回過神來,發(fā)現(xiàn)他已經進了辦公室。為了慎重起見,我還是硬著頭皮走進了部長辦公室。他正在批閱文件,頭也沒抬。
“請示部長還有什么指示?”
“會還沒開,我知道有什么事?有什么問題,回來告訴我就是。”
州宣傳部距組織部不到百米,在那幾乎正方形的四合院里,組織部在東南角,宣傳部在西南角。我?guī)Ш霉P記本,不到兩分鐘就到了宣傳部。來到蔚德部長的辦公室,會議剛開始。記得參會人員有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蔚德,宣傳部副部長張世亮,文聯(lián)主席陳剛,文聯(lián)副主席孫濤,計委的馬科長,人事局副局長、編委主任徐寧,還有不認識的,共有八九個人吧。由孫濤匯報,刊物擬名《博格達》。博格達峰位于準噶爾盆地南緣,昌吉州境內,在北天山也是最高峰。“博格達”,史學界公認為蒙語,為高峻雄壯之意,本土刊物就以“博格達”冠名是比較合適的。與會部門沒有提出不同意見。下面就辦刊的宗旨、開設的欄目等諸項進行了詮釋,基本上全部獲得了通過。因為時間已晚,最后蔚德部長要求,業(yè)務部門抓緊時間籌備,這次沒有來得及上會的,力爭盡快再開一次部門間的協(xié)調會,這次就到此吧。
半月后的一個下午,又開了一次部門間的協(xié)調會。地點仍然在宣傳部領導的辦公室,不同的是下午一上班就開會,一開始部領導就講:州黨委和州政府對辦好本土刊物非常重視,從人力、財力都給予了極大關心和支持,力爭七一向黨的生日獻禮!后來領導就規(guī)格、編制、人員等相關問題提出了補充意見,各部門有的做了說明,有的認真做了記錄,所需人員的調動、編輯部門的建制,以及經費等問題都進行了認真討論。人員主要從宣傳文化系統(tǒng),主要是報社、文工團等相關部門選調。相關部門立即進入準備階段,組織人事、財政物價等部門都積極表了態(tài)。
這就算是本土文學刊物《博格達》的催生會吧。自然,這次會議后還有許多的工作,也許相關部門早已在做準備工作了,但我所經歷的僅此而已。
扶我前進的首本文學刊物
開過部門協(xié)調會之后,我將部門形成的共識寫成了匯報材料,也就是相當于會議紀要,請科長審閱后送交了辦公室,覺得這項任務就算完成了。誰知在周末的組織生活會要結束的時候,支部書記問大家還有什么要說的。張部長說:“審干科就把部門協(xié)調會議的情況說一說,一是通報,二是配合做好工作。既然黨委政府都重視,涉及組織人事部門的我們要全力以赴!”陳主任簡單地說了一下相關內容,基本是書面匯報內容,而后就看著我。希望我有所補充。“會上還有新的要求嗎?”部長見沒人吭聲便問道。“沒有,就是要求各部門能夠支持刊物,積極投稿。”我有點緊張地說。“好!那咱們就給下面都打個招呼。有能力的可以積極投稿,眾人拾柴火焰高嘛!”然后就散會了。在出門時,部長看了看我說:“你不是喜歡寫點東西嗎?也可以利用業(yè)余時間寫寫稿嘛!”還沒等我“嗯”出聲來,他已經出門走了。
人總是有惰性的,當時上班,除了接待來訪人員外,還有大量的申訴材料需要看,一天下來,至少眼睛是很累的。半個月過去了,漸漸把這件事兒給淡化了。坦率地講,在部隊報道組是寫過點豆腐塊文章的,但多是以新聞報道為主的。記得篇幅過三五千字的也就是發(fā)表在新疆日報的《一片熱心育新苗》、新疆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的《各族戰(zhàn)士親又親》,其余的都是豆腐塊兒的。小的沾點“文藝”邊的,從未在正規(guī)的純文學類刊物上買到過“站票”!
不知不覺又到了月底,那晚我在宿舍給戰(zhàn)友回信,陳科長進來我竟然沒發(fā)現(xiàn)。“寫稿子了,明天你去趟芳草湖吧,信訪辦車走得早……”我“噢”了一聲不覺臉紅了,其實寫稿子的事我還沒開始,一個字都沒動。時間的確有點緊張了,寫什么、怎么寫成了問題。當時的主要文學刊物,好像總的趨勢是傷痕文學比重較大。在我們接觸到的落實政策的工作中,當時下鄉(xiāng)知青返城高峰基本已過去,遺留問題基本也得以妥善解決。而六十年代中葉,幾個大城市知青回城問題又比較突出,特別是南疆一些地區(qū),一時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焦點。當時昌吉州情況較穩(wěn)定,也出現(xiàn)過扎根農村、農場的典型人物。如當時農墾系統(tǒng)103團的天津知青周春山等,芳草湖農場、奇臺縣吉布庫公社涌現(xiàn)出早年支邊青年不少典型事跡,不少知青在農村做出突出貢獻的事跡,有的還擔任了大隊的會計等基層干部,有的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任了領導,發(fā)揮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們可以走,但他們沒有走,在艱苦的生存環(huán)境中做出了突出業(yè)績,深受群眾的歡迎。這不也代表一種精神嗎?一種扎根精神,奉獻精神。這類題材當下能不能寫?怎么寫?自己有沒有能力寫好?寫了有人看嗎?我反復問自己,感到非常猶豫和困惑。可是他們又是實實在在存在的,而且非常受當地群眾的歡迎,基層群眾離不開他們,他們也像馬駒戀著綠地那樣依戀著這塊熱土。
對我觸動最深的莫過于那次由阜康到昌吉經過團場農村穿沙漠越戈壁頂著沙塵返回的經歷,我又一次被感動了。
調閱了相關的資料,會見完當事人,簡單地吃了午飯,我們就準備抄便道返回。下午起風了,并有沙塵,有時沙塵如浪。為了節(jié)省時間,我們需要穿過一截沙漠路段。當我們快走出沙漠時,感覺風并沒有降級,但沙塵卻明顯減弱了。周圍除了沙漠的植被外,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的紅柳。那針狀的葉、谷穗狀的花在沙丘上擺動,在沙海中仿佛搖曳著希望,綻放著笑容,同時也鎖住了沙漠的腳步。
出了沙漠,銜接著的就是戈壁。除了矮小耐堿的灌木外,還有在夕陽中向我們撲來的一簇簇的戈壁紅柳,那綠的葉紅的桿紅的花紅的芯,讓人產生無限遐想。
遠處可見農場扛著生產工具的社員,與團場的老“軍墾”渾然一體,是何等壯觀的畫卷啊!他們不就是那種扎根精神的象征嗎?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屯墾戍邊的一批批“志在四方”的支邊青年,沒有他們的奉獻就不可能有《邊疆處處賽江南》的樂章和畫卷。千百年來,有多少仁人志士奔赴邊疆,青春年少,一腔熱血。只不過當時不以知識青年稱謂罷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那批老“軍墾”,他們?yōu)榱诉吔慕ㄔO,冬去春來,歲歲年年,無怨無悔,真是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這種情懷,這種精神,驚天地泣鬼神。這也可以稱之為一種紅柳精神吧!
這一夜,我許久不能入睡,感悟頗多。想到了我的老師上海知青張國榮,小學體育老師天津知青張樹華……他們有的只比我們大幾歲,當年為了支邊能報上名,據說瞞著父母偷出了家里的戶口本。他們的事跡和形象,幾乎占據了我的思維空間和全部,我想寫他們,必須寫他們!
那幾天也許是思緒清晰了,總覺得有東西想寫,只想一吐為快,標題就定為《紅柳》了。包括周日,大概用了三四個晚上的時間,潦潦草草基本脫稿了。那時白天上班也很緊張,好在我以往從事宣傳工作時采訪過一些知青扎根農村的先進事跡,有相當的素材積累。
就這樣完成了初稿,但寫完只是完成了部分工作,抄寫占據的時間比寫稿長了許多。那時需要標準的方格紙,下面拓好復寫紙,認真地一筆一畫地謄寫。稍有不慎,不是爛了,就是看不清了,就得重來。我的字本身寫得就很不好,這對我來說真是件鬧心的事。這期間我又到縣上出了一次差,回來請朋友幫忙完成抄寫后,通過郵局寄出,才算完成了《博格達》發(fā)稿任務。
《博格達》伴我一路走來
《博格達》在改革中誕生,一路發(fā)展壯大。四十年來,雖是三易其名,但在我的心中,更多的則是親切與神圣。它像巨人那樣舉起過我們,陪伴和引領過我們。無論何時,我們都懷有一份感恩的心情。這塊平臺,激勵著我們在這漫漫而修遠的文學之路上不斷耕耘,不斷前進。
創(chuàng)刊號的影響是深遠的。很快東至木壘草原,西到瑪河兩岸,行政村以上的單位幾乎都收到了《博格達》這本季刊。一時間,它成了州機關食堂飯桌上必談的話題之一。各縣鄉(xiāng)鎮(zhèn)的許多單位食堂恐怕都有這種現(xiàn)象。除了某市政項目啟動了,某案平反了,本土人文文化也就成了自然的話題。當時消息傳播之快、影響之大是空前的,這激起了廣大文學愛好者的創(chuàng)作熱情,他們渴望通過文學刊物表達自己的心聲。在很短的時間里,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本土作家與詩人,特別是農民作家和詩人,這在當時的瑪納斯尤為突出。其中有農民詩人王凌云老師,有較大影響的農民作家俞敬元老師,等等。群眾喜歡,自然也就有了主動參與的積極性,群眾性是本土文化的生命線。《博格達》當時辦得風生水起,在社會上也很受關注。
有了平臺的孵化和文友們的激勵,后來我又在這本刊物發(fā)表了《晨讀》《冬游天池》《卡子門的清泉》等散文和一些詩歌,同時也得到了陳剛老師、孫濤老師、孟丁山老師的幫助和指導,受益匪淺。
后來我由組織科調整組建昌吉州黨員電化教育工作站。我們從自治區(qū)組織部領回設備后,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就拍出了黨員電化教育片《新的嘗試》,屬全疆地州之首,編導基本由我完成。我的抒情散文詩藝術專題片《塞外紅柳》在行業(yè)參賽中獲新疆一等獎。后來我還陸續(xù)在《西北軍事文學》等疆外媒體發(fā)表過文學作品。我撰寫的報告文學《人民公仆劉向陽》曾在《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領導科學》《中國法制報》《新疆日報》等媒體刊載和播出,我獲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宣傳部、組織部、紀檢委頒發(fā)的二等獎。后來,我又獲得新疆昌吉州文藝“奮飛獎”。
作為一名曾經為本土文學寫過一些作品的作者,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感慨萬千。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水平的成長與這本本土刊物休戚相關。這本刊物給了我很大的關懷,但由于自己的努力還不夠,所以我的文學成就是非常渺小的,總感覺到有負這本刊物對我的托舉,有負多年來眾多編輯老師的指導和關愛。
感謝《博格達》,本土的“文學孵化基地”,感謝編輯部春天里的問候!
蔣永軼,新疆奇臺縣人,曾在新疆昌吉州黨委系統(tǒng)工作,現(xiàn)已退休。新疆作家協(xié)會會員,在《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領導科學》《中國法制報》《新疆日報》《西北軍事文學》等發(fā)表作品,曾獲新疆昌吉州文藝“奮飛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