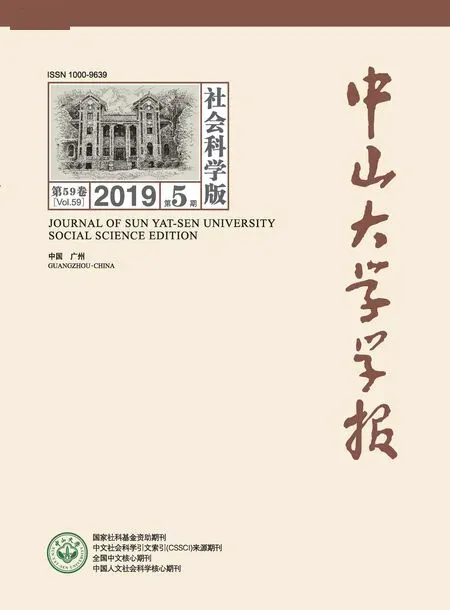鎖喃嚷結的真相*
——《六研齋筆記》所載“梵僧”行記辨偽
曲 強
一、鎖喃嚷結行記概況
明末文學家、書畫家李日華(1565—1635)所著《六研齋筆記》中收有一篇詳細記述“梵僧”鎖喃嚷結從“東天竺”來到大明的文章,全文兩千余字。首先記載李日華與鎖喃嚷結于嘉興真如塔附近偶遇,時在“天啟甲子九月九日”,即天啟四年(1624)。“深眼微須”的鎖喃嚷結“能為漢音”,當李日華問及其東來緣由時,鎖喃嚷結取出一篇記述其途中經歷的文章,被李日華抄錄下來,這就是本文所說的“鎖喃嚷結行記”(1)《六研齋筆記》的版本情況及本文討論的“鎖喃嚷結行記”全文,詳見后文第三節及本文附錄。。
行記大致可分成五部分:第一部分記述鎖喃嚷結出家之地“主活”的佛教勝跡,并提及其師承;第二部分記述其東來的原因及同行者;第三部分詳述鎖喃嚷結在“天竺”和今中亞地區的行程、經歷;第四部分記述其在今新疆、甘肅等地的行程、經歷以及當地風土人情;最后一部分寫鎖喃嚷結在明朝受到的優待以及宗教活動。
由于行記中有大量似乎關于明代西域宗教、歷史、地理等的記載,遂被學者應用于研究之中,大部分引用該文本的學者將其作為信史。但向達在《兩關雜考》一文腳注中質疑該文的可信度,認為:“其所云略似《慈恩傳》,而錯亂不可究詰,述玉門關,且逕取《慈恩傳》語。疑此是李氏故弄狡獪,虛構此僧,復刺取故書以相渲染。小說家言,不可據為典要也。”(2)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391頁。案:本書有1933年、1957年兩個版本。有關鎖喃嚷結行記的意見并不見于1933年版,而是最初出現于向達的《玉門關陽關雜考》(《真理雜志》1944年第1卷第4期),后易名為《兩關雜考》收入1957年版。總之,有關鎖喃嚷結行記的價值,存在較大分歧,卻沒有學者對此進行過專門研究。
鎖喃嚷結行記所述的經歷和路線與玄奘西行極為相似,唯方向相反。部分情節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文字雷同。其所記述的路線忽東忽西,繆亂百出,不合常理;其所記述途經地區風土人情不符合史實。總體來說,鎖喃嚷結的經歷疑點重重,應當出自拼湊與編造。鑒于許多學者把鎖喃嚷結的經歷當成信史應用于西域史地、宗教研究中的狀況,本文試圖揭出其中疑點,結合其他史料對當時的歷史文化特征記述進行分析,揭開鎖喃嚷結的真相。
二、鎖喃嚷結行記的疑點
(一)大量雷同、極度夸張與方位錯亂
鎖喃嚷結行記最大的破綻就是其中大量內容與《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雷同。下文將其雷同之處一一列舉,可見鎖喃嚷結行記抄襲屬實。
1.紫金函供佛牙一,長一寸廣八分,黃色,常放光明。后林懺播樓供佛掃帚一把,乃迦舍草作成。長三尺,圍七寸。帚柄雜寶裝飾,玉石匣盛。(“鎖喃嚷結行記”)
伽藍內……又有佛牙,其長寸余,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凈。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馀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此段出自鎖喃嚷結對于“主活國答辣法藏寺”的記載,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關于縛喝國中納縛僧伽藍所藏圣物相似。
2.東南臨至特伽國,聞說多暑,十月時如別國八月之熱。(“鎖喃嚷結行記”)
師不須往印特伽國。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此言出自西突厥葉護可汗之口,鎖喃嚷結抄襲并加以篡改。
3.跋祿迦國,名小沙磧……唯有一寺,名阿奢埋兒寺……又東三千里,過屈支國。(“鎖喃嚷結行記”)
(屈支國)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從此西行六百余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大唐西域記》)
鎖喃嚷結將屈支國的阿奢理貳寺張冠李戴到跋祿迦國,又將跋祿迦國與小沙磧這兩個不同的地點混淆在了一起。
4.屈支國,王號木文麴多。(“鎖喃嚷結行記”)
入屈支國界……王與群臣及大德僧木叉鞠多等來迎。(《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屈支國王“木文麴多”應當抄自屈支國僧人“木叉鞠多”,或由其形訛而成。
5.又東行千里,乃古高昌國。先高昌王有妹,被主活國王取去,亦名高昌國。(“鎖喃嚷結行記”)
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國,即葉護可汗長子呾度設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鎖喃嚷結筆下的古高昌國與主活國的姻親關系,正與玄奘記載的高昌國與活國的姻親關系相似。但是鎖喃嚷結所處的晚明時代,“高昌國”早已不存,應是抄襲篡改而成。
6.東行三千里至流沙河,即砂漠磧是也,寬八百里,上無飛鳥,下絕走獸,地不出水,土無莖草……十日方出,至野馬泉安歇取水。(“鎖喃嚷結行記”)
可于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更取水,從是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鎖喃嚷結行記中的“沙漠磧”應該來自“莫賀延磧”,但后文中鎖喃嚷結又杜撰一“賀延磧”,使得這段記載違背了實際地理位置,造成混亂。
7.東行千里,至五烽。從西烽取進有一山,王乃五隴之后代,名王侖卜。山下一泉,方圓丈余,清徹甚美,有達官看守。凡取水者,通報王知。王見五僧,甚生歡喜,留住數日,與書一封寄東烽王。使人引出界,指說路逕,付水皮袋盛之……行五日至東烽,遠見山上城墻,止有一門,對列器械弓箭,看守達官了見五眾,方要放箭,急呼西烽王有書,見書方許進見。細說西來之事,王亦甚喜,留住一月,付水甘糧,指路從賀延磧行,才有水。(“鎖喃嚷結行記”)
經八十余里見第一烽……有一箭颯來,幾中于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為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自送至十余里,云師從此路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骨肉,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既去,夜到第四烽……至水未下間,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來。入烽,烽官相問,答欲往天竺,路由于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過。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鎖喃嚷結在五烽的經歷與玄奘幾乎一模一樣,但是晚明時西域已無五烽,亦不可能有漢人為王,為抄襲的鐵證。
8.有葫蘆河一道,上廣下狹,洄波迅急,深不可渡。西岸多梧桐林。(“鎖喃嚷結行記”)
從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蘆河,上廣下狹,洄波迅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傍有梧桐樹叢。(《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上廣下狹,洄波迅急,深不可渡”十二字完全相同。
晚明西域政治、宗教狀況與初唐有天壤之別,可仍出現大量雷同和混亂之處,可見其并非簡單抄襲,而是經過了篡改,這才使得很多記載似是而非,錯亂百出。
鎖喃嚷結行記還有一大特點,就是涉及建筑、里程等數字時極度夸張。如主活國佛教勝跡:
西域東天竺國有國名主活,近名高昌。統二十聚落,城高十二丈,方圓百里,四門三層,四角有十二窣堵波,文武二樓高二十五丈……大乘寺立像高十五丈……大殿睡佛長十六丈,赤袈裟,白玉石佛像,澡瓶綠琉璃,高三尺圍三尺五寸。
鎖喃嚷結記述下的主活國城墻超過36米,文武二樓高度超過75米。不論對照類似的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料,這樣的數據都顯然過分夸大。
另外,鎖喃嚷結記載,從恭御城走“三千里過白水城”,但是根據《大唐西域記》記載,從白水城到恭御城只需要“西南行二百余里”(3)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0頁。。鎖喃嚷結還記載從白水城“東行五千里過呾羅斯”,但從白水城往東五千里已經到了今天居延海北方的蒙古國境內,這簡直是信口開河。這樣的記載在行記中屢見不鮮,如“東行三千里,至蔥嶺山”“又東三千里,過屈支國”“又東行千里,乃古高昌國”“東行三千里至流沙河”“東行千里,至五烽”等記載,可見其記載不僅夸張,而且隨意,很難使人相信其確有長途跋涉、親臨其境的經歷。
以上是從文獻學的角度對鎖喃嚷結行記中的材料來源進行分析,可見其抄襲屬實,且加以篡改、夸大。不僅如此,其內容本身也不合邏輯,疑點頗多。下文將其分為身世、經行路線、西域政治宗教狀況三大部分,一一剖析并揭露其不實之處。
(二)語焉不詳的身世
原文記載“梵僧鎖喃嚷結者,深眼微須,能為漢音”,梵僧一般泛指來自西域的僧人,“深眼微須”無助于確定鎖喃嚷結的族屬。從名字來講,“鎖喃嚷結”為藏語,“鎖喃”即bsod nams,意為福德;而“嚷結”應為rnam rgyal,意為勝利。同樣,行記里還提到了與鎖喃嚷結同行的四人:鎖喃陸竹、鎖喃堅剉、展陽喃渴、朵而只懺,均為藏語名。鎖喃陸竹當為bsod nams lhun grub;鎖喃堅剉當為bsod nams rgya mtso;展陽喃渴當為’jam dbyangs nam mkha’;朵而只懺當為rdo rje ’chang。雖然鎖喃嚷結等人的名字為藏語,但不能據此認定他們為藏人。明清時期蒙古族等信仰藏傳佛教的民族均有起藏語名的習慣,根據名字只能認定鎖喃嚷結等為信仰藏傳佛教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成書于清乾隆年間的《日下舊聞考》中亦引用此文,并說“梵僧索諾木納木結能為漢音……按:索諾木納木結,蒙古語‘有福人’也,舊作‘鎖喃嚷結’,今譯改”(4)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20頁。。事實上,“索諾木”即是蒙古語的sonom,多見于蒙古人名,是藏語bsod nams的蒙古語對譯,此外亦可譯為sodnam。“納木結”為蒙古語namjil,或寫作namjal,同樣借自藏語,多見于人名。由此可知《日下舊聞考》將“鎖喃嚷結”改成“索諾木納木結”只是將bsod nams rnam rgyal改成了蒙古式的譯法而已。而注解“索諾木納木結,蒙古語‘有福人’也”則是錯誤的,應為藏語“福勝”意。總之,《日下舊聞考》解讀有誤,對于確定鎖喃嚷結的身份意義不大。
關于鎖喃嚷結的身世,行記詳述其出家之地——“東天竺國”的“主活”。東天竺為五天竺之一,漢文典籍屢有提及。如《通典》卷193“天竺”條云:
天竺,后漢通焉。即前漢時身毒國……其中分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5)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040頁上。
可見 “東天竺”此名有具體所指,即今印度東部。另外《舊唐書》等史料還記載了東西南北天竺國各自的朝貢記錄,可知諸天竺不可混為一談。
那么“主活國”在哪里呢?“主活國”不見于記載,倒是有一個“活國”見于《大唐西域記》(6)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第963頁。《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7)慧立、彥悰著,孫毓棠、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1頁。,其位置大致位于今阿富汗昆都士附近。若主活國就是活國,那么它的地理位置與東天竺毫不相干;假如確實存在一個主活國,那么它不見于其他任何歷史記載,為何偏偏被鎖喃嚷結記錄下來了呢?
不僅如此,關于鎖喃嚷結師承的記載同樣撲朔迷離。行記云:
后建法王殿說法臺,高昌國王麴文嘇哆所施,封一高僧無上法王,號圓通至勝佛。所度法子名嘛喝實利,正鎖喃嚷結之師。俗居恭御都宮,是高昌王第七弟之遺宗,名播利鎧。厭王宮幻有之軀,欣菩提無生之果,遂投實利,修習禪定,指示要路。
可知鎖喃嚷結的師父是“嘛喝實利”。“嘛喝”,梵文作Mah,意為“大”;“實利”寫作rī,一般用于對于神的尊稱;而“俗居恭御都宮,是高昌王第七弟之遺宗,名播利鎧”直至“指示要路”,似乎指的都是鎖喃嚷結,那么他為何又“名播利鎧”(8)“播利鎧”或為突厥回鶻語Bilg?,唐代譯音為“毗伽”,意為“智慧”。此承王丁先生垂教,謹致謝意。呢?且從時間角度而言,高昌滅國到鎖喃嚷結所處的晚明,已逾千年,更不可能有此種師承關系。另外高昌王“麴文嘇哆”或與麴氏高昌王麴文泰有關,但從字形來看,似非形訛。另一種可能是,“麴文嘇哆”是麴文泰這個名字的某種西域胡語發音,姑存疑待考。總體而言,關于鎖喃嚷結師承的記載十分模糊,且存在不實之處。

(三)錯訛百出的經行路線

至于“大雪山”,在鎖喃嚷結經過的地域范圍內,喜馬拉雅山脈與興都庫什山脈都可以被稱為“大雪山”。從文獻角度而言,《大唐西域記》多次提到的“大雪山”都是興都庫什山。有意思的是,《大唐西域記》提到大雪山時順便提到了附近的國家揭職國(今阿富汗巴爾赫省附近),而巴爾赫省省會馬扎里沙里夫西北約19公里處的巴里赫舊城就是《大唐西域記》記載的縛喝國首都,又叫“小王舍城”(12)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第726,115,79頁。,和上文提到的“活國”位置十分接近。因此對這段行程的解讀就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大雪山并非興都庫什山,可是靈鷲山、王舍城都位于恒河平原上,附近并沒有什么大雪山,這段行程便不可能連貫起來;第二種可能是,大雪山就是興都庫什山,鎖喃嚷結可能將王舍城和小王舍城弄混了,從而以為王舍城附近的靈鷲山和小王舍城附近的興都庫什山也相距很近,因此寫到一處。如果是這樣,就證明鎖喃嚷結編造了他的行程,而他并不熟悉東天竺的地理情況,鎖喃嚷結恐怕根本就不是東天竺人。
接下來鎖喃嚷結一行“發站東過囀蒭河,此河阿耨達池之源也。進茄赤建國,換牒掛號,一月方行”。囀蒭河史無記載,但從字形來看或為唐代史料里常見的縛芻河的訛誤。縛芻河即今噴赤河,在阿姆河上游,為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邊界的一部分,位于興都庫什山脈和帕米爾山脈之間。至于茄赤建國,文獻無載,當是笯赤建國的訛誤。笯赤建國大概在今天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地區附近,屬于錫爾河流域,距離噴赤河很遠,因此渡過噴赤河到達笯赤建國是不可能的。另外,我們有必要再次回顧鎖喃嚷結的第一段行程。如果那些地點均位于“東天竺”,那么從東天竺無論如何不可能“東過囀蒭河”;如果那些地點如筆者的推測,均位于興都庫什山以北,那么可以滿足“東過囀蒭河”的地理條件,但是恰恰又可以證明鎖喃嚷結對這片區域的陌生,進而可以懷疑其自述的真實性。
而后,鎖喃嚷結一行“經喝捍國,行一月至恭御城……三千里過白水城……東行五千里過呾羅斯城……東行至羯霜那國……東行三千里,至蔥嶺山”。喝捍國就是唐朝所稱的中安國,大致位于撒馬爾罕西部。恭御城即后世的訛答剌,位于錫爾河邊,在喝捍國的東北方向。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玄奘先過恭御城,向南到達笯赤建國,再輾轉到達其西南的喝捍國,而鎖喃嚷結竟然從錫爾河流域的笯赤建國向西南走到了阿姆河附近的喝捍國,又轉向東北走回了錫爾河流域的恭御城,這樣的行程實在令人費解。接下來鎖喃嚷結又從恭御城過白水城,抵達呾羅斯。白水城就是后代記載的“塞蘭”,故址在塔什干東北,呾羅斯則在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到達呾羅斯后,鎖喃嚷結“東行至羯霜那國”,羯霜那國在古書里也叫史國、竭石等,位于烏茲別克沙赫里薩布茲,在前文提到的喝捍國以南。羯霜那國在呾羅斯西南方向,山川阻隔,極為遙遠,鎖喃嚷結的記述可謂天方夜譚。而后,鎖喃嚷結一行從羯霜那國向東走到了蔥嶺,方位雖然無誤,但恰恰坐實了鎖喃嚷結此段行程的混亂和荒謬。從蔥嶺的苦寒環境中走出之后,鎖喃嚷結一行“東南臨至特伽國……向東北,行至馬蟻院……又東行,過殑伽河,即恒河”。關于至特伽國,史料未載,筆者懷疑是《大唐西域記》中“印特伽國”的訛誤,印特伽(Indika)國即指印度。馬蟻院不詳何地,但鎖喃嚷結稱此地是“佛在世時使阿難教化之所”,再結合鎖喃嚷結接下來到達恒河,可以證明確為印度。然而蔥嶺的東南是喜馬拉雅山脈,距離印度極為遙遠,鎖喃嚷結不可能過了蔥嶺之后向東南走到印度,更別提向東渡過恒河。鎖喃嚷結的記載可謂自相矛盾。

鎖喃嚷結行記所述的經行路線:從笯赤建國到蔥嶺(箭頭編號為路線順序)
渡過恒河后,鎖喃嚷結一行“木筏而往,一月至跋祿迦國,名小沙磧。王名碧多,都城高廣,人物阜盛。唯有一寺,名阿奢埋兒寺,寬廣僧多,專學禪定,多游天竺”。此段行程謬誤最多。首先,位于印度的恒河與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緣的跋祿迦國相距遙遠,不可能一月而至。另據《大唐西域記》,屈支國有寺廟名叫阿奢理貳伽藍,為“奇特的佛寺”之意。鎖喃嚷結提到的“阿奢埋兒寺”應該就是“阿奢理貳伽藍”,但是史料沒有記載跋祿迦國也有這個寺廟。另據《大唐西域記》,“從此(阿奢理貳伽藍)西行六百余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可見跋祿迦國到屈支國要經過小沙磧,而鎖喃嚷結竟然說“跋祿迦國,名小沙磧”,跋祿迦國是姑墨,和小沙磧豈能混同?至于“王名碧多”,于史無征。但顯而易見,鎖喃嚷結的記載是把《大唐西域記》中屈支國和跋祿迦國的記載雜糅在一起,結果驢唇不對馬嘴,導致錯漏百出。
接下來,鎖喃嚷結一行經過屈支國、阿耆尼國、高昌國、流沙河、野馬泉等地,最終到達五烽。五烽的長官“指路從賀延磧行”。這里的“賀延磧”似乎就是“莫賀延磧”,而莫賀延磧位于五烽與伊吾高昌之間,玄奘就是過了五烽,穿越莫賀延磧才到達伊吾的。鎖喃嚷結既然已經過了五烽,就不可能再回到莫賀延磧。如果上文提到的寬八百里的“沙漠磧”是莫賀延磧,為何此處又出現了“賀延磧”?如此混亂的行程讓人很難不產生懷疑。
而后,“東行五日至磧,乃西番境界,名小西天。昔如來傳法于此,號烏思藏。地面寬廣,乃四家達王供奉之所,多出高僧。大殿內列法床五百張,有佛子法王蓮花上師所傳番經番咒,出滲金佛、人頂骨數珠、氆氌、容金鈴。云昔漢班定遠超住此,鎮定西域,本朝劉馬太監征西入界處,地氣多寒。參禮蓮花上師,留二載余”。接著上一段行程,從五烽東行,進入“賀延磧”,鎖喃嚷結竟稱此地為“西番”“烏思藏”(今西藏的前后藏地區),這顯然是荒謬的。另外,此處的描寫明顯具有雜糅的痕跡,“云昔漢班定遠超住此,鎮定西域,本朝劉馬太監征西入界處”明顯指的是五烽附近的邊塞地區,而其余記載則符合藏區的特征。至于“本朝劉馬太監”,萬斯同《明史》云:
劉馬兒太監,馬兒本名永誠,以帝掌御馬監事。后歷鎮西陲有功,故邊人呼馬兒太監云。為人性忠謹,善騎射,三扈成祖北征,皆為偏將。宣宗朝……帥師征兀良哈……再奉命監鎮甘涼,數出兵鏖沙漠間。(13)萬斯同:《明史》第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4頁。
可知鎖喃嚷結所說“本朝劉馬太監征西入界”確有此事。但劉馬太監鎮撫的也是西北邊塞,并非烏思藏。

鎖喃嚷結行記提及其在西域、漢地行經之地
最后,鎖喃嚷結一行“東至玉門關……有葫蘆河一道……作筏而進。從上稍至東北,行東南七十里,是玉門大路,封王進貢,悉由此行。隨喜岷州秉靈寺、雅州紅花寺。山西一路而來,上五臺山羅喉寺法王處,住二年,遇欽差御馬監太監劉潤上山,引五僧至北京雙林寺住”。其中“東至玉門關”與前文的“烏思藏”自相矛盾。而接下來一筆帶過的岷州秉靈寺、雅州紅花寺、五臺山,彼此相距遙遠。前文行程的詳細與此處的簡略形成鮮明對比,可見鎖喃嚷結不過是想突出其異域與邊地的行程,這恰恰是晚明士人最陌生的,而一旦進入漢地,便一筆帶過。再結合鎖喃嚷結行記中漏洞與自相矛盾之處,筆者認為鎖喃嚷結對自己行程的記述具有相當明顯的投機性、迷惑性,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鎖喃嚷結自述經歷的真實性。
(四)時空錯亂:鎖喃嚷結行記中的西域政治宗教狀況
鎖喃嚷結等人的經行路線錯亂百出,其中對于西域地區政治宗教狀況的描述更不可信,以下舉幾例加以分析。
1.主活、高昌與古高昌國的關系
傳記云:
西域東天竺國有國名主活,近名高昌……又東行千里,乃古高昌國。先高昌王有妹,被主活國王取去,亦名高昌國,古高昌國亦名伊吾國,人物清秀。相傳玄奘法師化道之所,時有漢僧駐錫。
這里有幾個疑問:一是此處提出了兩個高昌國,一個位于東天竺,又叫作主活國;另一個就是吐魯番地區的高昌國。前文提到,主活國不見于其他史料,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大唐西域記》中只有關于“活國”的記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云:
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國,即葉護可汗長子呾度設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呾度設又病,聞法師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止。(14)慧立、彥悰著,孫毓棠、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31頁。
《大唐西域記》說活國是“睹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國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15)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第963,964,964頁。。“睹貨邏國”即吐火羅,指臣服于西突厥阿史那氏葉護可汗的吐火羅國。這個“活國”,有學者認為是Warwlīz的音譯,又譯為遏換、阿緩等(16)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第963,964,964頁。;有的學者認為是嚈噠人(Hephtalites)所建“滑國”的異譯(17)[日]森安孝夫:《唐代における胡と仏教的世界地理》,《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3號,第12頁。。其都城在今阿富汗東部的昆都士(Qunduz)附近(18)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第963,964,964頁。,符合玄奘的路線。按照行記的內容來看,這就是鎖喃嚷結出家之地。但是通過上文論證可知,這個地方根本不可能稱為東天竺國。
又,“古高昌國亦名伊吾國”明顯不合史實。依文意此處的古高昌國當指麴氏高昌,伊吾并不在其控制范圍內。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提到:“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敕伊吾王遣法師來……于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由此可見,伊吾和高昌并非一體,有明確界限,豈能說“古高昌國亦名伊吾國”呢?
《日下舊聞考》將此處的主活改作“卓哈”,并注:“卓哈,舊作主活,照三史畫一改正。”(19)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第1620頁。乾隆年間,乾隆帝命令將《遼史》《金史》《元史》中的譯名進行改譯,但是由于三史中語言來源十分復雜,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語言的語音發生了變化,改譯過程中出現了非常多的錯誤,使得原來的文獻面貌受到很大的破壞。至于“主活”,還可以和玄奘所記載的活國對應,改成卓哈,依據不明,更加無從確定其位置,并且無法與其他文獻印證。因此這條記載無助于對所謂主活國的考證。
2.關于屈支國王“木文麴多”
鎖喃嚷結記載“屈支國,王號木文麴多”,更是暴露了鎖喃嚷結編造經歷的事實:首先,木文麴多的名字不見于其他任何記載;其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明確記載,玄奘在屈支國遇見僧人“木叉鞠多”,并與他辯經(有的版本作“木叉毱多”)。“鞠”“麴”形音俱近,因此鎖喃嚷結所說的木文麴多很可能就是抄自木叉鞠多,發生了以“叉”為“文”的形訛,鎖喃嚷結依照玄奘的記載編造了自己的經歷,此又是一明證。
3.“五烽”遭遇
唐朝玉門關外有“五烽道”,作為重要的邊防關卡,五烽是由漢地到西域的必經之地。玄奘就曾經在五烽面臨九死一生,而鎖喃嚷結竟然有著和玄奘幾乎一模一樣的經歷。更可疑的是按鎖喃嚷結記載,西烽、東烽都有王,且為漢人名字。此時吐魯番地區為葉爾羌汗國所據,漢人占據此地為王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王名“王侖卜”與玄奘所記第四烽校尉王伯隴名字接近(侖卜疑為伯隴的倒文,再置換以近音字),應當系根據玄奘的記載篡改而成。
以上列舉了鎖喃嚷結關于西域形勢記載中的疑點,接下來分析文中涉及的政治和宗教內容,特別關注西域地區的政權變化以及佛教衰落與伊斯蘭化進程。
關于西域地區的政治形勢,可供參證的材料是永樂十三年(1415)出使西域的陳誠撰寫的《西域番國志》。陳誠從洪武到永樂時期多次出使西域,對于東察合臺汗國、帖木兒帝國的情況有詳盡的記述。由于《西域番國志》是陳誠根據親自出使的經歷寫作而成,因此可作為信史。永樂年間與萬歷年間大約相差二百年,政治形勢雖有變化,但較之于近一千年前的唐代,政治與宗教上的情形畢竟更為接近而具有連貫性,因此這是本文選擇《西域番國志》與鎖喃嚷結的經歷進行對比的原因。
陳誠出使時的西域主要處在帖木兒帝國和東察合臺汗國的控制之下,即便到晚明時葉爾羌汗國占據南疆,此地也絕非鎖喃嚷結所描述的獨立綠洲小國。另外,鎖喃嚷結記載的各地名稱幾乎全部沿襲玄奘時代的名稱,但通過閱讀《西域番國志》可以發現,明朝初年這些地名就早已經換了另一副模樣。比如鎖喃嚷結記錄的白水城,在陳誠的筆下已經變成了塞藍;羯霜那國在陳誠筆下已經成了渴石;至于鎖喃嚷結記述的高昌等地已經變成了吐爾番、火州等名字;伊吾的名字也不再使用,變成了哈密。陳誠親自出使西域,他所記錄的名字都是按照當地語言記錄下來的發音,而鎖喃嚷結竟然還使用一千年以前的舊名,顯然不合情理,在史學上屬于年代錯亂(anachronism)。
再說宗教形勢。鎖喃嚷結自述中涉及的各地宗教狀況,可列表如下:

主活國名剎大院百所、大乘寺、小乘寺、答辣法藏寺等、佛舍利。恭御城人民烏黑,多習波羅門種。白水城多外道幻術,不敬僧。呾羅斯城其人圓晴黑面,短發長須,多習小乘。羯霜那國民敬三寶。跋祿迦國寬廣僧多,專學禪定,多游天竺。屈支國人民男婦赤色,敬重三寶,多幻術。
上文已經提到,主活國大概位于今阿富汗昆都士省,陳誠雖然到過附近,但是沒有留下風土人情的記載。但在其西南部,就是帖木兒帝國首都,今阿富汗赫拉特,陳誠明確提到“酒禁最嚴”(20)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8,69,78,81—82,106,108,110,111頁。,“有通回回本教經義者,眾皆敬之,名曰滿剌。坐立列于眾人之右。雖國主亦皆尊之”(21)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8,69,78,81—82,106,108,110,111頁。,。滿剌就是波斯語Mullah的音譯,是伊斯蘭教學者、神學家的尊稱,今譯毛拉。“惟不養豬,亦不食其豬肉,此最忌憚之。凡宰牲口,非回回宰殺者不食。”還記載了做禮拜的大土屋。種種習俗,都是伊斯蘭教的明顯特征,卻沒有關于佛教的任何記載。陳誠還提到各種術語,比如米爾咱、刁完、撒力馬力、撒藍等,都是波斯語音譯(22)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8,69,78,81—82,106,108,110,111頁。,。再參照陳誠對于其地服飾、建筑等的描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當地不論是上層統治者還是普通民眾都普遍伊斯蘭化,這一點也可以從《拉失德史》等波斯文、察合臺文史料中得到印證。而昆都士以北的撒馬爾罕,亦有“禁酒”習俗,其地還“有回回拜天之處 ”(23)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8,69,78,81—82,106,108,110,111頁。,。我們很難相信,處于赫拉特和撒馬爾罕兩大城市之間的昆都士還會有佛教欣欣向榮的景象。
至于鎖喃嚷結所說的高昌國“有漢僧駐錫”,陳誠確實記載了附近的佛教情況。他說吐魯番“信佛法,僧寺居多”,“近山有土臺……臺畔有僧寺……房中有小佛像”(24)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8,69,78,81—82,106,108,110,111頁。,,可見明初吐魯番還是存在佛教的,這一點也可以從波斯文史料《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中得到印證(25)《沙哈魯遣使中國記》為永樂年間帖木兒帝國派往明朝的使臣所記,其中記載吐魯番“大部分居民都是事奉佛陀的不信仰天主的人”。見《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年,第38頁。。可是到了位于吐魯番西的崖兒城,當地佛教卻是一副衰敗的景象,“舊多寺宇,有石刻存”(26)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8,69,78,81—82,106,108,110,111頁。,。而吐魯番以東的火州“城方十余里,風物蕭條,昔日人煙雖多,僧堂佛寺過半,今皆零落……今為別失八里馬哈木王子所隸”(27)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8,69,78,81—82,106,108,110,111頁。,。附近的魯陳城“有為回回體例者……有為畏兀兒妝束者……火州、吐爾番、魯陳三處,民風土產,大概相同”(28)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8,69,78,81—82,106,108,110,111頁。,。由此可知,明朝初年大概只有吐魯番還存在著佛教,其周邊地區的佛教早已零落蕭條,完全看不到鎖喃嚷結所說的景象。一些學者輕信了鎖喃嚷結行記中“多幻術”的記載,據此以為當時西域密教還頗發達,這不符合史實。
實際上,西域地區的伊斯蘭化從喀喇汗王朝就開始了。喀喇汗王朝的第三代大汗薩克圖·博格拉汗皈依伊斯蘭教,其后發動了持續近四十年的針對佛教中心于闐的圣戰,并最終征服之,使當地居民改信伊斯蘭教。但此后幾百年間,西域特別是以吐魯番為中心的東部地區仍然盛行佛教。東察合臺汗國時期,黑的兒火者汗(約1389—1403在位)與馬哈麻汗(約1407—1415在位)均征伐過吐魯番并強推伊斯蘭教,蘇菲派頗為盛行(29)[日]間野英二:《十五世紀初頭のモグーリスターン: ヴァイス汗の時代》,《東洋史研究》1964年第23卷第1號,第21頁。。至明中葉以后,當地佛教基本絕跡,最終完成了伊斯蘭化的過程。而西部的帖木兒帝國、布哈拉汗國等均是伊斯蘭教的國家。印度的德里蘇丹國亦強推伊斯蘭教,那爛陀寺和超戒寺等著名寺院被徹底毀滅,佛教徒四散奔逃,佛教走向衰亡。12世紀末印度的佛教已經絕跡,其后的蘇爾王朝、莫臥兒帝國無一不崇奉伊斯蘭教,鎖喃嚷結所說的東印度佛教繁榮的景象根本就不會存在。
總而言之,有充分的文獻依據可以證明,鎖喃嚷結依《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文獻編造其經歷,而他所記載的沿途風土人情大多與史實相悖,不可據信。鎖喃嚷結行記的虛假性是可以完全坐實的。
三、鎖喃嚷結的身份
鎖喃嚷結的經歷確實出于編造和虛構,那么究竟是鎖喃嚷結編造了自己的經歷,被李日華記載在筆記中,還是如向達所言,這一切完全出自李日華的杜撰?由于其他文獻中沒有關于鎖喃嚷結的記載,回答這個問題就首先要從分析李日華其人以及《六研齋筆記》開始。
李日華,字君實,號九疑,嘉興人。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卒于崇禎八年(1635)。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官至太仆少卿(30)李日華:《六研齋筆記 紫桃軒雜綴》,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1頁。。精于書畫,著述甚富,如《紫桃軒雜綴》《六研齋筆記》等。從其《味水軒日記》來看,李日華亦崇信佛教,平日與僧人交游甚多。
《六研齋筆記》的刊刻、增修等情況比較清楚(31)《六研齋筆記》版本情況,李丹文《李日華年譜》一文作過詳細梳理,此書“在崇禎年間首先刻板,印出完帙,由新枝、琪枝、昂枝校勘……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年,琪枝、昂枝帶領曾孫輩含淑、含澤、含渼、含涏、含瀾、含溶、含溍、含津重修再印……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李瑂及璉、玨、珮、蕡等玄孫輩再次重印……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李日華云孫李芬周在曹勛后人曹秉鈞幫助下,再次補修重印了李日華著作”。李丹文:《李日華年譜》,上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224頁。,最早的版本刊刻于崇禎年間,這也是附錄“鎖喃嚷結行記”所據底本。其中篇目或短或長,且篇目之間沒有什么關系,可知內容為隨筆記錄,后整合在一起。其中研究書畫者居多,其余內容龐雜,有奇聞異事、方藥、出土文物、地方風俗等,一些內容帶有傳奇色彩。對于《六研齋筆記》中記載的內容我們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具體分析。
鎖喃嚷結的行記與其他奇人奇事的記載有一個明顯不同,就是李日華采取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的,在開頭明確記述了遇見鎖喃嚷結的時間(天啟四年九月九日)、地點(嘉興真如塔、長水法師子璿墓)、同行者(曹愚公(32)曹愚公為李日華之友,在《六研齋筆記》中多次提及,似為居士曹谷,曾刻佛經。此承高山杉先生垂教,謹致謝意。)等內容。而其他軼事奇聞的記載則往往不具備同樣具體的人物、時地信息,因此恐非李日華故意杜撰。向達認為是李日華虛構此人,缺乏確鑿證據。
如果這樣,我們只能認為,鎖喃嚷結可能確有其人,只是編造了自己的經歷。但由于其他史料均無關于鎖喃嚷結的記載,我們無法得知更多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袁中道《珂雪齋集》記述了萬歷四十一年(1613)他在沙市遇見的能說漢語的西天僧:
步至青蓮庵,遇大西天僧,能漢語。自本國至中國,途程凡八年。曾入京。以慈圣太后所賜千佛衣及金襕袈裟出觀。(33)袁中道:《珂雪齋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03頁。
此僧姓名未見記載,但他的經歷與鎖喃嚷結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西天僧、能說漢語、長途跋涉來到大明、曾經入京、與慈圣太后有關、被賜金佛衣等。然而由于資料的缺乏,這二人是否有關仍無法認定。
總之,筆者認為鎖喃嚷結并非來自東天竺的梵僧。由于他與他同行者的名字皆為藏語,他有可能是信仰藏傳佛教之人,當然也有可能連這些藏語名字都是編造的。但有一點筆者認為毫無疑問,就是鎖喃嚷結之所以要冒著被人識破的風險編造自己長途跋涉東來的經歷,是為了引起朝廷關注從而獲致優待和恩寵。
明廷多優待番僧,并賜以各種稱號,因此有明一代冊封番僧為法王、國師、禪師的記錄極多,鎖喃嚷結東來的萬歷年間同樣如此。《明憲宗實錄》記載,成化二十一年周洪謨等上書言事,主要問題就是佛寺泛濫,冊封過多,奢靡成風。他提到:“大慈恩、大能仁、大隆善護國三寺番僧千余,法王七人,國師禪師多至數十。”(34)《明實錄附校勘記27·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3年,第4392頁。《明孝宗實錄》記載成化二十三年“禮部疏上傳升大慈恩等寺法王、佛子、國師等職四百三十七人,及剌麻人等共七百八十九人”(35)《明實錄附校勘記28·明孝宗實錄》,第56頁。。可見當時法王、國師、禪師等人數極多。不僅如此,朝廷還予番僧重賞,《明憲宗實錄》記載,成化三年六科給事中魏元等上疏:
西番札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梭轎,導用金仗,其所奉養過于親王,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饑民……今朝廷寵遇番僧,有佛子、國師、法王名號,儀衛過于王侯,服玩擬于供御,錦衣玉食,徒類數百,竭百姓之脂膏,中外莫不切齒,特朝廷未知之耳。(36)《明實錄附校勘記23·明憲宗實錄》,第1178—1180頁。
可知番僧生活極為奢侈。這也導致邊民冒充番僧,意圖邀寵獲利之事屢禁不止。《明憲宗實錄》記載:“有中國之人,習為番教,以圖寵貴。”(37)《明實錄附校勘記23·明憲宗實錄》,第1180頁。又《明英宗實錄》記載:“有番僧短發衣虎皮,自稱西天活佛弟子,京城男女拜禮者盈衢。上命錦衣衛驅之歸其本土。”(38)《明實錄附校勘記20·明英宗實錄》,第6350頁。而“邊民見其進貢得利,故將子孫學其言語,投作番僧通事,混同進貢”(39)《明實錄附校勘記19·明英宗實錄》,第5079—5080頁。。由此可見,在明代冒充番僧獲利絕非個案。
鎖喃嚷結為了編造自己的經歷煞費苦心,他主要參考了《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記載,連編造的路線也與玄奘西行路線基本一致,并且將不同地點雜糅在了一起,把建筑物尺寸、行程里程數極度夸大。可是,玄奘生活的初唐時代與他所處的晚明已經有將近一千年的跨度,西域、印度地區的風土人情、宗教狀況早已經與一千年前大不相同。伴隨著伊斯蘭文化的影響,這些地區的佛教已經極度衰微。而政治上,玄奘時代西域林立的綠洲小國早已經不存在,其政治形勢也與千年前有了天壤之別。而這樣胡亂拼湊的經歷依然能夠騙過時人,并被記載下來,正是由于明朝中后期嘉峪關以西并不處在明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洪武、永樂兩朝頻繁的西域通使從洪熙朝開始銳減,加之東察合臺汗國與明朝之間的長期軍事沖突迫使明廷多次閉關絕貢,兩地隔絕。從明代筆記中可見明人對于西域的記述經常擺脫不了“漢唐故事”的影子,且充滿著“想象異域”的色彩;而明朝古地圖上西域各地位置也常有較大偏差,明人對于西域狀況的陌生可見一斑,這正是鎖喃嚷結的謊言未被識破的原因。
四、“鎖喃嚷結行記”辨偽的意義
鎖喃嚷結的經歷僅僅被記錄在《六研齋筆記》中,雖然這個筆記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但仍有一些著作引用、參考該文獻。可惜的是,絕大多數學者在引用時不經辨別,直接使用,不慎將偽作當作信史使用了。
前文提到的《日下舊聞考》直接轉述《六研齋筆記》的記載,還把鎖喃嚷結的譯法改變了,其后一些地方志直接照抄《日下舊聞考》的文字。《大日本佛教全書》將此文列入“游方傳叢書”之中,冠以“西域僧鎖喃嚷結傳”之題,并加上許多隨文注釋,將文中地名、人名還原為梵文。撇開真偽問題不論,《大日本佛教全書》的很多考證比較細致,有助于進一步的研究(40)如行記中“至特伽國”,注釋云“至或辛字,西域記序指天竺稱印特伽國”;行記中“木文麴多”注釋云“文或叉字”等。《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16冊(オンデマンド版),東京:大法輪閣,2007年,第428頁。。但是該本也存在嚴重問題:其一,未標注所據底本的版本信息;其二,錄文字形訛誤、句讀錯誤極多(見附錄);其三,還原、考證非漢語詞匯尚有不妥之處;最重要的是,注釋者只專注于其中的人名地名如何還原為梵文,對文中錯誤和模糊之處或視而不見,或強行考證,顯然是將其看作信史(41)如行記中“周天元”指的是北周宣帝宇文赟,注釋卻云“天元難解,元或后字乎”;行記中“麴文嘇哆”注釋云“高昌國王麴文泰曾為玄奘檀越,麴文蓋其姓也”,麴氏高昌王姓“麴”,絕非“麴文”。文末尾注云“五僧原名恐高昌方言,非純梵語也”。鎖喃嚷結對出生之地語焉不詳,怎能認定為高昌人?另外尾注中將“朵而只懺發站”當作人名,這是句讀錯誤所致,文中本有提及“朵而只懺”處,編者亦未發覺。《大日本佛教全書》(オンデマンド版),第431頁。。其后《大正新修大藏經》從《大日本佛教全書》中抄錄此文及梵文轉寫,同樣以“西域僧鎖喃嚷結傳”之名同《往五天竺國傳》《悟空入竺記》《繼業西域行程》等書列入“游方記抄”名下,收入《大正藏·史傳部》中。這本身就說明編撰者將其作為信史看待,后來很多學者使用的鎖喃嚷結行記文本正來源于《大正藏》。《大正新修大藏經索引》對此文有解題,頗為疑惑地提到書名為“西域僧”而文中卻稱“梵僧”這一現象(42)“「西域僧鎖喃嚷結伝」、書名は西域僧とするも、本文中には梵僧とある。”《大正新脩大藏經索引》第29卷史傳部下,東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昭和57年,第5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實際上此文并非一本書,連標題“西域僧鎖喃嚷結傳”也是后加的,顯然《索引》作者并未考證。更嚴重的是,《索引》認為此文記錄了高昌國和印度的佛教情況(43)“本書は彼が記した高昌國およびインドの仏教事情の再錄である。”《大正新脩大藏經索引》第29卷史傳部下,第5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這是完全錯誤的。
其他研究著作中也有很多問題。長沢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44)“これ以後の天竺西域紀行としては、元の「梵僧指空禪師伝考」、明の「西域僧鎖喃嚷結伝」等があるが、これらはいずれも東來西域僧の記錄で仏蹟についての記錄は明確でなく。”長沢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昭和54年,第582頁。、段玉明《指空:最后一位來華的印度高僧》(45)“至于明代,《西域僧鎖喃嚷結傳》尤稱:‘又東三千里,過屈支國……敬重三寶,多幻術。’鎖喃嚷結還曾在此‘停住一年’。那么,指空稱其在此受王迎請、入內演法,即不是沒有可能。”段玉明:《指空:最后一位來華的印度高僧》,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4頁。、任平山《龜茲佛教大小乘因素的史料分析》(46)“鎖喃嚷結……在高昌和五臺山等地還盤桓了至少四年,故推其路過龜茲的時間在公元16世紀末。盡管提到龜茲人敬重三寶,但描述語氣與描述跋祿迦國的佛教情況已大不相同。又云此地多幻術。龜茲佛教這時可能已經大不如前了。”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學研究》第2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49頁。等都提到鎖喃嚷結行記,并信以為真。何孝榮《明朝宗教》一書引用文,將鎖喃嚷結當作明后期印度密教的傳播者之一(47)何孝榮:《明朝宗教》,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139頁。。季羨林在《西域佛教史》中提到主活國和高昌的關系時,認為“這兩地的關系是中印關系史上過去鮮為人知的一段公案,將來當另為文探討之”。還說“此時龜茲的佛教還頗發達,而國王名字仍用梵文……‘多幻術’也可以視做千年前密宗流行的延續”(48)《季羨林全集》第16卷,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156—157頁。。后來季羨林在《玄奘時代及其后兩地的佛教信仰》一文中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對于文章中的一些細節提出了質疑,但行文中仍存在不少錯誤(49)季羨林引文來自《大正藏》,未對照《六研齋筆記》,錯誤頗多。又云“麴文是高昌王國的國王的姓,長達數百年”,這也是錯誤的,麴氏高昌王姓“麴”,享國約140年。《季羨林全集》第16卷,第241—243頁。。徐文堪在《從漢文古籍看古代西域(新疆)的人種問題》一文中列舉了鎖喃嚷結的相關記載,特別強調其“深眼微須”的特點,最后連同其他史料一起得出結論:“反映了古代塔里木盆地民族在人種學上的特點。其中最明顯的是‘深目高鼻’,說明以歐羅巴人種為主。同時,也有包括漢人在內的蒙古利亞人種存在。此外,還有歐羅巴人種與蒙古利亞人種的混合類型。”(50)徐文堪:《吐火羅人起源研究》,北京:昆侖出版社, 2005年,第143頁。以鎖喃嚷結的記載作論據是完全錯誤的,不管鎖喃嚷結的記載是否屬實,作者對于文本理解的錯誤也是顯而易見的。鎖喃嚷結自稱東天竺人,怎么能用鎖喃嚷結的體貌特征來證明塔里木盆地的民族成分呢?寬忍主編的《佛學辭典》一書中有鎖喃嚷結的詞條,將鎖喃嚷結的經歷大致復述,竟然說憲宗的國師板的答就是具生吉祥(51)寬忍主編:《佛學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香港:香港華文國際出版公司,1993年,第1300頁。。具生吉祥在洪武年間便已經去世,怎么可能成了明憲宗的國師?這些錯誤都是沒有仔細考證文本的結果。前文已提及,向達注意到了鎖喃嚷結自述中的細節,并且大膽懷疑,可惜僅在腳注中提及,而對李日華虛構的推測也有待推敲。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一書提出:“該文獻撲朔迷離,對其價值尚需作進一步的認定,作為信史利用的條件尚不成熟,故這里僅略加提及,旨在引起關注而已。”(52)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23頁。總之,使用這條材料的學者大多沒有采取懷疑的態度仔細分析其真實性,在此基礎上對西域政治、宗教、民族、歷史方面作出的推論也就沒有立足之地。本文列出了鎖喃嚷結行記一系列的可疑、矛盾、悖理之處,力圖破解鎖喃嚷結的謎團,在此基礎上推論此文為一篇向壁虛構的梵僧西域行記。至于杜撰所據的史源,除了《慈恩傳》《大唐西域記》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材料,尤其是一些非漢語詞語、事項,都還有待作進一步的考證。
附錄:“鎖喃嚷結行記”匯校
本文使用底本: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年間刻本《六研齋筆記》,八冊,其中《六研齋筆記》四卷,另有《二筆》《三筆》各四卷。半葉8行19字,四周單邊,花口,無魚尾。版心題“六硯齋筆記”,而書中題“六研齋筆記”。索書號7636。卷二,葉一至七。國家圖書館另藏有索書號為XD1368和XD10480的兩套《六研齋筆記》,與底本完全相同,應出自同一版,即目前所知最早的版本。但XD1368僅存一冊,多處蟲蛀,個別字不清。XD10480共兩冊,保存較好,但相對于底本缺《李竹嬾先生說部全書原序》《自題》,故這兩本僅作參考。
參校本:
1.《六研齋筆記》清抄本,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7635,十冊。《筆記》《二筆》《三筆》各四卷,共八冊,另含《紫桃軒雜綴》二冊。半葉11行21字,朱絲欄,四周雙邊,花口,朱魚尾。版心題“六硯齋筆記”,而書中題“六研齋筆記”。凡“玄”“弘”字皆以缺筆避諱,唯《紫桃軒雜綴》中均不避諱;
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06—509頁;
3.《大日本仏教全書》第116冊(オンデマンド版),東京:大法輪閣,2007年,第428—431頁;
4.《大正新脩大蔵経》第五十一卷史傳部第三(四),東京:大正一切経刊行會,昭和三年,第985—987頁。
案:《大日本仏教全書》《大正新脩大蔵経》本有隨文注釋,限于篇幅僅將其對勘同專名的拉丁文轉寫錄入。注釋相同的僅列《大日本仏教全書》,不同的分別注出。
為盡可能保留文本書寫原貌,本匯校本使用繁體字。
六研齋筆記卷二[1]
古秀竹嬾李日華著[2]
天啓甲子九月九日,同曹愚公侍御登眞如塔。下,禮長水法師墓,浴雪井水。遇梵僧鎖喃嚷結者,深眼微鬚,能爲漢音。與坐良久,因詰其西來緣起。嚷結袖出一編[3]相示,葢其踐歷蹤由也。今錄於此,以備遐方參覽焉。

校記
[1] 大正藏本、佛教全書本題為“西域僧鎖喃嚷結傳”。
[2] 大正藏本、佛教全書本作“古秀竹嬾李日華著,六研齋筆記卷二”;四庫本作“明李日華撰”。
[3] 大正藏本作“篇”。
[4] 底本及佛教全書本作“宰”,其余諸本皆作“窣”;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注Stūpa。
[5] 底本空白;清抄本作“約距”,其余諸本作“西北”。
[8] 底本空白;大正藏本作“常”;其余諸本作“光”。
[11]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無“成”。
[12]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哆嘇”。
[13]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寶利”;佛教全書本注:寶或室字,梵名Mah-Sri。
[14] 佛教全書本注Kūyu-shahr。
[15] 佛教全書本注Parivarman。
[16]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無上”。
[17]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要略”。
[18]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斑”。
[20] 底本、清抄本空白;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無此字;其余諸本作“我”。
[21] 底本不清,似“官”亦似“宮”;清抄本作“宮”;四庫本作“官”;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宮”;佛教全書本注:莫度達宮或指Baktra-Tarkhan乎,蓋突厥大夏使臣廳也;大正藏本注Baktra-Tarkhan(?)。

[23] 佛教全書本注Anavatapta。
[24] 佛教全書本注Nujkend。
[25]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桿”。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注Kermineh。
[26] 佛教全書本注Kūyu-shahr。
[27] 佛教全書本注Taras。
[28] 佛教全書本注Kasanna。
[29] 大正藏本作“□”。
[31]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木茂”。
[33] 佛教全書本注Pittha。
[34]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集盛”。
[36] 佛教全書本注Kucha。

[38] 佛教全書本注Agni,土語Yanghi。
[39] 清抄本、四庫本缺末筆避康熙帝諱。
[40]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朧”。
[41] 佛教全書本注Tarkhan。
[42]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蕃”。
[43] 清抄本此字被挖去;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狀”。
[44]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大”。
[45] 佛教全書本注Hu-lu。
[46]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段”。
[47] 佛教全書本注Pardita;大正藏本注Pandita。
[48] 佛教全書本、大正藏本作“善薩”。
[49] 佛教全書本尾注:五僧原名恐高昌方言非純梵語也。鎖南者或蕃名Gsod-nams之類乎。今假以梵語推之概如左者乎。鎖喃嚷結Snna-Nki;鎖喃陸竹Snna-Luttaka;鎖喃堅剉Snna-Kainsa;展陽喃渴Dhyna-nga;朵而只懺發站Darsi-Sampadin。大正藏本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