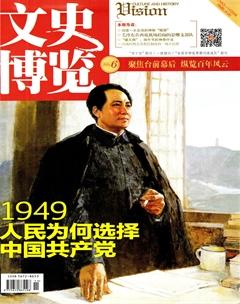湘軍將領詩文中的土洋兵器
崔建華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八里橋之戰”,清軍將領僧格林沁指揮3萬多清軍精銳騎兵對陣法軍將領孟托班指揮的1萬英法聯軍。激戰中,主要裝備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清軍器不如人,在裝備火槍大炮等熱兵器的英法聯軍面前不堪一擊。慘敗的清軍最終傷亡過半。而英法聯軍僅陣亡12人。回國后的法軍將領孟托班受到了英雄般的追捧,不但當上了參議員,還被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封為“八里橋伯爵”。
與此同時。清軍的另一支戰斗力較強的部隊——湘軍,其兵器裝備水平又如何呢?
除了史料記載,有些湘軍將領的詩文著述中也對當時的兵器裝備有所涉及,能從中一窺當時湘軍的兵器裝備水平——因為湘軍將領大多是讀書人,像曾國藩、胡林翼等均屬進士,左宗棠、郭嵩燾等皆為舉人,彭玉麟、李續賓等則是秀才。這些投筆從戎的文人大多著述頗豐,其中不乏戰爭和兵器的記錄。
舉人出身的唐訓方(湖南常寧人,曾任安徽巡撫、署理湖北巡撫),不但工詩文,而且善丹青,其留下的《從征十六圖》中有一幅《上馬袖書》圖,圖中的湘軍將領騎馬行軍時仍手不釋卷,體現了書生帶兵的湘軍精魂,同時還可見湘軍的兵器裝備主要是刀矛弓箭,火槍極少,充分反映出受國力和工業水平的制約,湘軍當時只能混裝冷熱兵器的無奈現實。可見,湘軍的兵器裝備水平并不優于僧格林沁的精銳騎兵。
唐訓方在詩作《贈鮑鎮軍春霆》中,不僅栩栩如生地記錄了湘軍名將鮑超的英勇形象,還記錄了當時運用的兵器裝秘情況:
“鎮軍崛然起鄉里,目光如電氣如虹。樊口水面賊舟列,沖冠一怒髭如鐵。手執長矛挽賊船。雷飛巨炮掃鯨穴。小池新城稱偽縣,矢石交攻如馳電。鎮軍神武奮莫當,身被重傷猶酣戰。”
很長一段時間里,唐訓方與鮑超都在胡林翼麾下并肩作戰,唐軍稱“訓字營”,鮑軍稱“霆字營”,但“霆字營”更加勇猛善戰,包括太平天國悍將陳玉成都佩服至極,不敢輕視。從詩中可見,戰斗中既用了熱兵器“巨炮”,亦用了冷兵器“矢石”,而主人公、湘軍猛將鮑超競然仍在用冷兵器長矛——這可能源于湘軍當時面臨的主要對手是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軍,畢竟農民起義軍兵器裝備水平不高,亦是冷兵器為主,熱兵器為輔。“身被重傷”仍“手執長矛”奮戰不止,既展示了鮑超的高超武功,也表現了鮑超的勇猛無畏。假設換作是“手執火槍”,恐怕鮑超在世人心目中的名將形象將大打折扣。
據岳麓書社《湘軍史》記載,到咸豐三年(1853),曾國藩訓練的湘軍人員裝備體系基本定型,其陸師參照明代“戚家軍”編制,以營為獨立戰斗單位,每營戰斗員為450人,非戰斗員250人左右,每營官兵總數應為700人左右。營下設4哨(“戚家軍”在哨下還設有小哨),每哨火器與刀矛各半,即抬槍與小槍各2隊共4隊,刀矛4隊。除抬槍每隊正勇12名外,其余小槍與刀矛每隊正勇10名。營直轄親兵6隊,其中劈山炮2隊,小槍1隊,刀矛3隊。可看出陸軍武器主要有:劈山炮、抬槍、小槍、刀、矛。
而湘軍水師在咸豐三年冬已有“各式炮船240艘,湘潭4營,衡州6營。營制如下:每營炮船21艘……每營合計425人。水師炮船。長龍頭炮2尊,重800~1000斤,邊炮4尊,各重700~800斤,梢炮1尊,重600~700斤,腰炮轉珠2尊,重40~50斤。各船均配備洋槍、鳥槍及刀矛等若干,以備近戰”。
由此可見,當時湘軍既裝備有冷兵器刀矛,亦裝備有火炮、洋槍、鳥槍等熱兵器。其中陸師差不多冷、熱兵器各半,水師則幾乎以熱兵器火炮為主,可見湘軍水師戰斗力強還是有這個物質基礎為前提的。
火炮、槍支等熱兵器的大量運用,自然對火藥、炮彈、子彈的后勤需求極大。《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湘軍史料叢刊)一書中,就收錄了唐訓方當年寫給曾國藩的一封求援信,唐在信中急切呼喚火器彈藥補給:
“訓方即于十一日回營,囑令暫為堅守。惟蒙、壽兩處賊若分竄,皆可遠擾我軍之后,殊難抽撥。現在糧食如能到齊,尚支兩月,惟軍裝、子藥俱形缺乏,懇祈吾師速飭何鎮紹彩來臨,并撥火藥二萬斤,大小炮子二萬斤,火繩萬盤,以利進攻……”
這封信收于同治二年(1863)六月十八日,所述場景應處在安徽叛軍苗沛霖圍攻蒙城的危難之際,唐訓方此時需要補給的已主要是火器彈藥了,估計此時湘軍的熱兵器裝備水平已有較大提升。
在唐訓方的詩作中,還多次提及“欃(chan)槍”,這又是種什么武器呢?
其實,唐的詩作《舟過金陵有感》中的“橇槍盡掃無氛埃,直抵黃龍快舉杯”,以及詩作《營次彌陀鎮宿河干草堂不寐有感(時李迪庵三河失利未知下落)》中的“何日掃橇槍,言歸課耕讀”,所提的“橇槍”并非武器,其與任何槍械無關,“橇”乃彗星別名。古人視彗星不吉,謂為“掃把星”。亦暗指妖魔鬼怪。唐訓方此“橇槍”實際上指的是太平天國義軍,由此可見他對太平天國是何等的恨之入骨。
(責任編輯:葉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