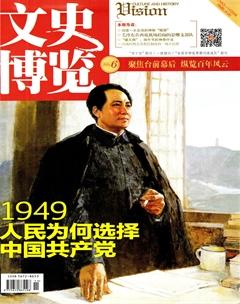我家喂過“工分豬”
沈果毅

在20世紀60年代的集體化時期,我家喂過工分豬(又稱派購豬)。
我當時是一名農村公辦小學教員,愛人在農村勞動,帶著兩個小孩,一家人的口糧全靠愛人去掙,一人掙三人口糧很有困難。我是吃國家糧的,家里美其名日“四屬戶”(軍、工、烈、干),又叫半邊戶,按規定,口糧不足生產隊應當補足。
可是要得到生產隊補給不容易,于是生產隊就安排我愛人喂工分豬,因為喂豬不耽擱出工勞動,可以利用空閑時間安排,就這樣,愛人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生產隊就不要給我家補助糧食了。
工分豬由自家購買豬苗,生產隊撥飼料糧食。別看豬由私人喂養,可是豬的所有權不歸個人,豬喂大了要送食品站收購。那時每個生產隊還要送派購豬,生產隊無力辦大型豬場,只能分解到農戶喂養以完成任務。
食品站收購牲豬后,也不放肆殺豬供應群眾要求,他們每年要完成國家調配的支援香港、澳門及廣州和城鎮工礦肉食供應任務,所以,當時盡管農村差不多家家養豬,但豬肉供應依然異常困難。
農戶送派購豬到食品站,所得收入要交到生產隊出納手里,作集體開支用。食品站發一個豬飼糧條子和一張購豬油的憑證歸私人支配,每張條可買3斤豬板油或花油,回家煎后作烹調用油,以免吃“紅鍋子”菜(指不放油炒菜)的尷尬出現。
記得有一次我用土車子推著豬送至鎮上的食品站,接過會計發給的收購豬款沒有仔細數,就直接收進腰包,回家交老婆一看,發現少了5元錢。那時收購豬款是要全數交納到生產隊的,少了錢,是要賠的。我急得晚飯都沒吃,又返回食品站,求食品站會計查對。那位會計豁達大度,任勞任怨,他把抽屜里的現金全部盤了底,再查對賬目,發現確實多出來5元錢,于是給了我這多出的5元錢,當時的我非常感動。
話又說回來,只有5元錢的虧空,我為什么這么急呢?因為我當時雖然是公辦教師,但屬于編內代課,月工資只有26元,這5元錢代表著我一個人一個月的副食開支了,能不著急嗎?
這個事情過去了幾十年,至今我還對那位會計不貪小便宜的精神深深佩服!
我家地處湖南湘鄉與韶山交界處,由于韶山屬特殊地區,私人憑條可買5斤豬油,所以那時我們這里有人不得不采取舍近求遠的方法,把豬送到韶山,由此便可多買2斤豬油。人們冒著有可能挨批的風險,違規去做,實在是出于無奈!
(責任編輯:亞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