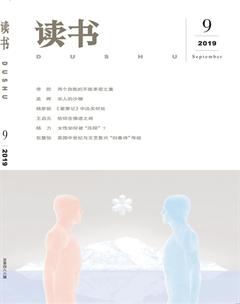為政治的尊嚴辯護
崇明
再生,或者說第二次誕生,通常是某種宗教性的或者類似于宗教性的靈魂體驗。這一體驗并不尋常,往往令人困惑。猶太官員尼哥底母在聽到耶穌談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時,就不能理解,問道:“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耶穌告訴他,重生并非身體的返老還童,而是從水和圣靈而來的生命更新。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只有從罪里悔改,歸回上帝,以耶穌為主,接受圣靈的帶領,人方能擺脫為罪捆綁的舊生命而獲得屬靈的新生命。從法國到中國的現代革命也以民族和國民的再生為目標,只不過其方式不再是水和圣靈,而是火(暴力)和意識形態。在世界去魅、革命遠去的當下,對于專注于個體的生活和職業的現代人而言,再生似乎遙不可及,無從談起。然而,我們忽視了,人們時刻都遭遇和觸及的政治本身就具備再生的內涵。對此,人們多半會愕然乃至大笑。舉目所及,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非洲還是歐洲,濫權的政客、腐敗的官員、蒙昧的公民,比比皆是。并且,在人類歷史中,正是因為政治的黑暗和敗壞,人們才試圖在宗教和革命中尋求再生。看來,與政治相關的,非但不是再生,而是墮落。今天,面對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和沖突、威權的專橫和極端力量的暴虐,疲于應對的政治正在遭遇一場普遍危機。所以,當德國知名政治學學者夏博特教授(Tilo Shcabert)以一本題為《再生:論人類存在的政治起始》的小書來提醒我們,正是政治通過創造文明實現了人類的再生,他對政治的尊嚴的辯護,是恰逢其時還是不合時宜?
何謂人類的“再生”(the second birth)和“政治起始”(politicalbeginnings)?夏博特首先區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誕生。前者是人的身體性的誕生,不過人的身體構成(constitution)的形成并非意味著人獲得了人成之為人的構成要素。只有人經歷了政治誕生,也就是第二次誕生,“人”才真正形成。人需要掌握的是自身的起始(beginning),而非使人出現或被造的初始(start)。對起始(beginning)和初始(start)的區別是本書的另外一個基礎性的區分。初始是沒有起始的存在,某種老子的“道”和《圣經》中的創造,超越了時空,是人的存在的根基和本源。然而,對于他始終身處其中并塑造其原初存在的初始,人類需要通過起始來予以彰顯,而這一起始就是人的政治創造。夏博特把人類的政治創造置于某種宇宙論當中,也就是說人的政治起始是他對宇宙初始的探尋的某種延伸。因此,關于政治的起源,他提出了與傳統的政治理論不同的看法。傳統的理論通常在亞里士多德的影響下把政治的起始理解為政治共同體的形成。在夏博特看來,亞里士多德對政治起源的論述被當成了某種規范性理論,以至于忽視了為政治共同體的建立奠定基礎的政治宇宙論和政治人類學。根據亞里士多德對自然的目的論闡釋,只有在城邦形成時才會產生政治。阿倫特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雖然她也使用了“再生”來形容人的政治起始,但是她認為這一起始是人通過言說和行動插入到人的存在中,從而形成政治共同體。與亞里士多德和阿倫特不同,夏博特認為應當在人的誕生和政治共同體的形成之間理解政治的起始。人天生被賦予的能力(pre-given power)使得政治隨著人的誕生而發生,正是因為這一與生俱來的政治性使得人類走向共同體和文明。這并不意味著否定共同體的建立所具備的關鍵性意義,而是要去思考在人類的創生中哪些因素使得人傾向于政治生活。
在夏博特看來,從初始出發,首要的事實是人類創生時的“一”和人在其數量上的“多”構成了人類存在的正反兩面。在“一”和“多”之問,人首先是身體并因而是個體的存在。作為絕對的“一”和作為分散的“多”如何能夠統一起來?這需要人能夠發現彼此之間的關聯,而正是絕對個體性的身體成為這一關聯的基礎。作為身體的存在,人占有空間并在空間中移動,并從而與其他身體相遇。在這種相遇中,身體作為力(power)的承載者的事實呈現出來。力與力的碰撞和組合構成了政治。作者強調,政治源于人的身體性這一基本特征。換言之,正由于人是身體的存在,政治才成為必要。身體的保存成為政治的最初動力。所以,當政治走向身體的毀滅時,譬如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政治也就消亡了。需要注意的是,夏博特并非因襲霍布斯、洛克從自然狀態和自我保存入手理解政治起源的做法。在他看來,自然狀態只是某種虛構。他關注的是身體如何讓人走出了身體性,而不是政治如何通過實現自我保存而強化了身體性——這是他與霍布斯、洛克的根本差異。在身體的接觸、沖突、聯合與由此形成的權力安排以及秩序架構中,人需要在社會性和差異性中理解共同生活的可能。
作者引用詹姆斯·麥迪遜,指出沒有身體的天使不需要政治。天使生活的地方是伊甸園,而有身體和政治的地方不可能是伊甸園。人的身體性注定排除了烏托邦的可能。人通過身體學習政治和政治科學,因為需要統治權力把人的身體的“多”聯合起來。身體存在的政治性讓“一”和“多”在小范圍的共同性中走到了一起。由此,人開始發現其創造力(creative power),進入文明。所謂身體的政治性,指的是身體的存在首先暴露了人的孤立和困境,人的不充分性和不自足性,但也因此引導或迫使人走到一起致力于實現充分和自足,從而拓展了人性(humanity),或者說把人進一步人化(humanization)。人在這一過程中掌握了政治和政治科學,因此政治科學成為文明的奠基。夏博特引用十四世紀阿拉伯哲學家伊本·卡爾敦(IbnKhaldun)恰切地說明了這一點:“這是‘政治的科學,也就是建立政治的科學,因為它關乎到把人類塑造為人類的文明的奠基和建立。這是起始的科學,因為它在人性起始時為人類的存在提供了藍圖。”人在政治中開始了人性和文明的起始。
作為身體性的存在,人在本性上也是行動的存在。作為行動者,人及其所處的世界因而始終處于變動當中。夏博特引用帕斯卡:人處在不斷飄移中,無法停在堅固落腳之地,大地裂為深淵。他也借助《淮南子》來說明人事變動不居的道理。在這里夏博特并未考慮帕斯卡的看法背后的古今之變,而是把人事的變動作為人類存在的本性。在這一變動當中對行動的意義和目的的追問和決定至關重要。在行動中,人類自身成為開始。在一與多、在身體的存在、在行動當中,人的政治起始在人的靈魂和意識中逐漸確立。政治與靈魂的關聯乃至對應是本書的重要主題。事實上,身體的移動和人的行動在意識中形成的善惡及是非的判斷是人性的根本特征,所以只有在意識中人才能實現并發揮其人性。政治同樣在靈魂中發生。作者提出了柏拉圖主義的論點:“人是城邦的動物”,在人和城邦之間存在某種對應。人在靈魂中為其中的各種力量建立統治秩序,否則靈魂會走向混亂,而靈魂的秩序是城邦的秩序的前提。不過夏博特并沒有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強調的理性對靈魂的統治展開論述,沒有設專章討論理性,而是轉入了對恩典的分析,在這一分析中我們會更好地理解他對靈魂與城邦的關聯的理解。
正如夏博特提到的,他在書的前半部分依次對數、身體、行動、意識的論述呈現出一種“上升”的運動,從意識和靈魂進入恩典顯然是這一上升的繼續乃至飛躍。他這樣做顯然是為了避免人們把他的政治理論視為一種人文主義。雖然他一直談到人在自身當中包含了政治和文明的起始,但人們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認為人是自我的絕對主宰。這里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理解他區分初始和起始的用意:人固然能創造起始,但他身處其中的初始不是他創造的。夏博特提醒人們:“人不能把他們自己放在一切起始的起始,或者讓他們自己成為所有存在的起源和終極的根基、太陽下面發生的一切事物的最初的推動者。”然而,人的問題恰恰在于會把自己當成上帝或者試圖成為上帝。《圣經》開篇的創世敘事就記載了人的僭越或反叛,而人的歷史也是自我成神的歷史,而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一《圣經》敘事的宏大上演。夏博特指出,人可以成神這樣的承諾是十七世紀以來歐洲和西方思想的終極主題。在現代性的背景下審視人的歷史,我們會意識到人尤其需要光來看到人的邊界,而理性自身不能成為這樣的光。這是因為,“驕傲、傲慢和嫉妒獲得了勝利,驅趕了控制狂想的理性,把狂想設置為人類努力的主人”。其次,理性的最終極的發現是存在一個先于理性的基礎。因此,在夏博特看來,恩典才是人看清自己和世界所需要的光,“它使人從狂想的枷鎖中擺脫出來……它是人類的自由”。在恩典的引領之下,人以上帝之愛作為靈魂和城邦的根基,進入上帝之城。在拒斥上帝的人之自愛的支配下,人及其建立的城邦也在這一自愛的支配下走向對權力的貪欲。在人的政治起始中,人既可以創造也能夠破壞,創造的力也可能轉化為破壞的力,或者說力本身兼具創造性和破壞性,蘊含有破壞的種子。因此,政治是創造性的,但是政治的創造力(creative power)可能墮落為赤裸裸的力的政治,甚至最終造成對生命的踐踏和毀滅,走向政治的反面,而政治的本質本應該是生命的完成。因此,恩典的介入是為了遏制人本的潛在狂妄。夏博特提醒人們,在政治中進行創造的人需要恩典,不是因為政治本質上是敗壞的,而恰恰因為政治具有某種“神性”。他引用西塞羅和麥迪遜表明,建構和保存政治社會和共同體是某種具有神圣性的行動。正如他的導師沃格林指出的那樣,一個政治共同體也是某種宗教團體。政治共同體所肩負的對人進行照看(care)的職責是人所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使命。這一照看是神對人的照看的延續。柏拉圖在《政治家篇》里講述了神對人的照看如何轉化為人的自我照看的故事,這個故事所講述的正是政治所具備的神圣性。
正是以對人本主義的現代性的反思為背景,夏博特重構了作為人之特性的“思考”的意義,把思考(thought)與人性并列為人的再生的“初始”(start)。也就是說,思考不是哲學家眼中超越人世、矚目永恒的最高貴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種社會性,一場宴會。思考的起點恰恰不是人所能掌握的起始,而是一種先于人的初始。思考和神性一樣邀請人們進入到共同體的建構當中。思考被賦予人,使人獲得在一與多之問來完成自我的創造力,從而在創造、愛欲和時間中來理解人的力量與破壞、缺乏與渴求、變動與不朽。在創造中,上帝是創造的邊界,上帝通過創造讓每個個體呈現出其創造。人的創造性是其自身的愛欲的運動的結果。但是,在夏博特看來,只有對神性的愛欲,而非出于自我的缺乏而無休止尋求和占有的愛欲,才能讓人不斷延展從上帝那里獲得的創造。人的創造和愛欲所面對的是時間的流逝對一切政治和文明的沖刷、侵蝕、淹沒。如何在時間的永久流動中獲取和維護人的創造的持久,成為政治科學的重要主題。夏博特指出,正如人往往不能把某種牢固的身體和靈魂的構成賦予自己,建造持久的政體也非常困難。雖然如此,或者正因為如此,人必須致力于克服政治遭遇到的重重艱難和危險,讓政治成為實現人的再生的持續創造,而非人的囚籠。在書的末尾,夏博特通過對政治學的兩個基本主題法律和自由的思考來探究政治持續的可能性。
夏博特指出,身體存在的困境迫使人進入共同體,但是人的自我中心會讓人陷入到政治秩序的混亂中。無政府和反政治的社會性生存比孤獨性的生存更為危險,因為后者意味著人的不完全,而前者則是對人的破壞和毀滅。因此,人的政治創造必須建立法的統治,因為只有讓法成為每個人的主權者,從而阻止每個人聽任自我任由自己或他人的欲望和激情的擺布,共同體才能存在并延續。夏博特闡發了亞里士多德和英美憲政傳統對法治和人治的辨析,認為統治權力不應該是人的權力。他引用柏拉圖指出治理國家的人不應該被稱為統治者,而應該是法的仆人。法具有超越人的絕對性,因為其根源于神性、自然和理性。因此,人們對普遍的正義具有某種預知(foreknowledge);它雖然含混,并不明確,但正是這種預知引導人們在立法中進入他們的政治起始。法律的統治是為了讓人在自由中實現人性。作者區分了自然自由和統治自由或者說政治自由。自然自由是個體對自我掌握的主權。這一主權可能是孤獨的和破壞性的,然而在法律和政治帶來的連接中可以獲得友誼和創造性。但這一連接必須在對權力的約束制衡中形成,否則將是扭曲的。在對權力的憲政約束中形成的公民連接就構成了統治自由或者政治自由。只有控制了權力的破壞性,才有可能實現權力的創造性。
夏博特教授的書雖然篇幅不大,但卻涉獵廣泛,密集探討了諸多常規政治理論通常不會處理的問題,如數(number)、意識、恩典、思想、創造、愛欲、時間等。這樣做的目的是讓我們看到政治是人類文明的整合性力量。超越人和構成人的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政治的發生,也在政治中創造了人性,使人從身體的生走向靈魂的生。因此,作為人的再生,政治不只是建立了共同體,而是促成了靈魂的生——這并非宗教意義上的生命更新,而是人性意義上的自我發現。政治的全部尊嚴和意義就在于政治在人性上的巨大創造性。因此,進入政治生活、運用政治權力會提升和擴展人的心靈。作者在本書的跋中講述了自己有限卻寶貴的政治參與的經歷。當他當選為代表和其他代表一起共同議事時,他們的行動表明他們經歷了某種轉化(transformation)。公共性的責任為他們的職責和他們自己賦予了一種高貴的尊嚴。正是因為政治可以帶來偉大的創造和神圣的尊嚴,政治的敗壞必然造成巨大的破壞乃至毀滅,招致人性的扭曲和敗壞。缺少了實現并完滿人性的良好政治,人性如何能得到安頓和提升?如果沒有政治帶來的人的再生、靈魂的生,人的身體性的“生”也受到威脅。所以,在今天的重重政治危機中人們所遭受的敗壞和苦難,恰恰最深切和最迫切地揭示了政治的尊嚴和意義。為了實現政治的尊嚴和意義,人類需要在維護自由的法律架構中遏制權力的破壞性而發揮其創造性。同樣重要的是,人需要拓展其視域,在人類所處的初始創造中尋求恩典和神性來建造和維護靈魂,因為靈魂的構成與政治的構成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