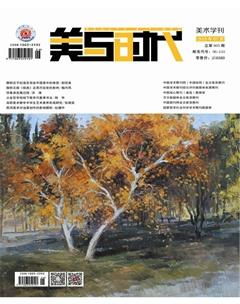探析王微《敘畫》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楊丹鳳

摘 要:宗炳的《畫山水序》作為我國第一篇正式的山水畫論,其在畫論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和他同時代的王微接著寫出了山水畫論《敘畫》,其美學思想同樣值得我們關注。他在《敘畫》中提高了繪畫的社會地位,提出山水畫應該作為一門獨立的繪畫學科,同時,他的“明神降之”指出了藝術創作過程中構思活動以及精神思考的重要性。其思想觀念對后世文人畫的影響也是值得我們探究的。
關鍵詞:王微;山水畫;明神降之
早在六朝時期,中國就已經有了山水畫。經過初步的創作實踐,文人對山水畫藝術進行了理論總結。早期畫論以宗炳的《畫山水序》和王微的《敘畫》為代表,這兩部畫論初步道出了山水畫的美學價值。后世的大多數研究者都更關注宗炳的《畫山水序》,而對王微的《敘畫》研究卻很少,《敘畫》中所揭示的山水畫的創作和欣賞規律被認為是對《畫山水序》的補充解釋。雖然兩者出現的時間相近,在同一時代背景下產生,但也應該關注到《敘畫》的藝術價值。
一、圖畫應與《易》象同體
在現在,藝術作為上層建筑,其地位是很高的。然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它被視為“雕蟲小技”。東漢時期的士大夫都說:“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可以看出,當時繪畫的地位非常低下,被認為是奴隸才做的事。漢以前是沒有文人士大夫從事繪畫行業的,漢末有少量的文人開始參與繪畫。魏晉時期,大量的文人開始繪畫,將繪畫的社會地位提高了。
王微在《敘畫》的第一句中指出:“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他認為繪畫不屬于技術行列,其地位應與圣人所作《易》相同。此時的“藝術”不同于我們現在所說的“藝術”,而是“技術”的含義。當時的畫家地位是很低的,被認為是畫匠。正是因為有些人在“藝術”行列中加入了繪畫,王微明確反對并駁斥了當時的流行說法,聲明繪畫不屬于技術行列,而應與《易》形象相同。《易》是古代文人必修的課程,將之前被認為是“技”行列的繪畫等同于《易》,這就大大地提高了繪畫的地位。
王微對繪畫社會功能的討論,對后世畫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張彥遠說“畫者……與六籍同功”,與王微的“與《易》象同體”有異曲同工之處,又說“豈同博弈用心,自是名教樂事”,也和“非止藝行”的意思差不多。
二、山水畫是獨立的畫科
雖然魏晉山水畫已經萌芽,但實際上是指軍事指示地圖或其他地形圖。地形圖是實用的,一般用作軍事、行政或經濟建筑中的地形指南。而且,地形圖的排列非常嚴格,不能隨意繪制。山水畫屬于藝術的行列,山水畫是藝術家對生命本質的情感理解后的一種生活再現,而不應該是實用的。
王微指出“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這一不正確說法,排除了繪畫作為地形圖的實用功能。繪畫“非以案城”,山水畫既然是一門藝術,它應該與地形圖分開,各自發揮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山水畫的地理發展有正確的目標,否則,它與地形圖混淆,難以擺脫其實用性,難以獨立成為一門藝術。王微認為,如果山水畫要獨立,首先必須與人物畫分開,人物、亭臺、鳥獸只能用作景觀裝飾,以增加山水畫的情感。
王微的很大功勞是將山水畫與地形圖分開。他強調:“披圖案牒,效異《山海》。”《山海經》是戰國和西漢初期的地理相關方面的著作。效異《山海》是說山水畫對人們的精神享受與《山海經》給人的感受不相同。這也是因為兩者的社會功用不同,山水畫偏向于精神享受。山水畫應與軍事地圖分開,按照藝術規律發展,并獨立成為繪畫門類。王微的主張也使他成為山水畫的功臣,使后來的山水畫得以發展。
三、將“傳神”引入山水畫
顧愷之是第一個提出繪畫的“傳神論”,但他的“傳神論”指的是人物畫。宗炳和王微將“傳神論”應用于山水畫。宗炳所說的“嵩華之秀,玄牝之靈”中的“秀”“靈”指的就是山水之神。又說:“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也就是說,應把山水的面貌看在眼中,景觀的風格記在心中,從而上升為“理性”,如果畫得很巧妙的話,那么觀眾在畫面上看到和理解的東西應該和畫家一樣。“應目”和“會心”都源于景觀中體現的神靈。這是因為它與景觀之神相連,只有這樣,山水畫才能起到“觀道”的作用。所以畫山水要體現山水之神。
王微提出,“本乎形者融靈”。宗炳的“質有而靈趣”是將神和形狀分為兩個體,這與他的思想是一致的。王微認為形神是一體,不可分割,“止靈亡見,故所托不動”。“形”、“精神”、“移動”和“心”這四個類別在以下文本中得到了回應。這四個范疇有著一定的交互關系。王微認為,形是精神的載體,而運動則是融化精神在心中所產生的反映。在這個時候,形狀是基礎,它是攜帶神靈的容器。一個是精神的形狀,另一個是沒有精神的形狀。王微認為,畫面上顯示的山水畫需要“融靈”,所以使用“本乎”這個詞。無論是“止靈亡見”還是“靈無所見”,都表明繪畫形狀中沒有精神存在。如果精神不能在畫作中體現,那么“所托不動”,這里是承載精神的形狀,既不是精神也不是運動。這樣無靈的形則是前文提到的“案城域,辨方州”的地形圖了。地形圖哪里會引導人們“思浩蕩、神飛揚”。
心靈被靈魂所感動,繪畫也被靈魂所感動。四個范疇構成了“形—融靈—心—動”結構關系,這里,形是基礎,精神、心、動,彼此不和諧,這四個關鍵點不是遞歸過程,而是一種理論形式的整合。形式是基本要素,融化是過程和方法,心是主體,運動是在主體的狀態下呈現的。形式與精神融合,出現在心中,產生情感。添加詞也不能打破這四個類別之間的關系,并且關系是明確的,那么重點是每個類別的含義。
“靈”是神明的同義詞。這兩個概念可以互換來表達相同的意思。精神是萬物山川的精神,是人眼中所見萬物的精神,是一切生命的源泉。這種精神是靜止的,當人在畫面中展示它時,它會產生運動。這是畫面所產生的運動,運動所引起的變化在人心中綻放。
四、明神降之
王微首次提出繪畫要“明神降之”的思想,它是對宗炳的“以形寫形”這一理論的修正和重要補充,表明了藝術觀念和精神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作用。“明神降之”是對山水畫創作過程中審美心理特征的概括描述。山水畫的審美趣味必須通過“明神降之”來實現,而不是依靠藝術家的繪畫技巧。
王微用宗教修養的道路作為藝術經驗的這種經歷可以追溯到老子的“抱一”思想和莊子的“守一”思想。“抱一”的境界是通過對形而上學的清空而達到的,這是一種絕對空虛、靜止的審美態度。“我守其一”的具體方式是“心齋”和“坐忘”。因此,“神明”或“明神”是審美活動主體的審美心理特征。具體地說,主體在沒有欲望和無知的狀態下,要充分打開心靈對審美客體的澄清和統一,以獲得對客體的審美把握。經過對老莊的發掘和《太平經》的發展,這種審美體驗方式逐漸被藝術家所接受。兩晉時期,王微并無當官的意思,而且是“寒食散”的愛好者。他經常處于瘋狂和癲癇的狀態。他在道教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所以他將宗教修道之路作為一種藝術體驗也就不奇怪了。
簡而言之,王微認為山水畫審美對象的創建不僅是創作主體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在模棱兩可的情況下類似于宗教體驗達到“神”結果:審美不僅是一個認知畫家使用筆墨的技能或顏色,還應實現“明神降之”。它類似于佛教獨特的“頓悟”禪修方法的審美體驗。這也可以看作是審美主體心理體驗與宗教體驗相似性的又一佐證。王微從道家經典中汲取營養,結合自己的山水畫創作實踐,用“明神”一詞概括繪畫審美活動中藝術思維的特點。與宗炳的“暢神說”相比,王維的“明神降之”有其自身的特點。宗炳的“暢神說”,來自于欣賞山水畫的精神愉悅。正如王微所描述的,“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的審美心理,更注重對積極的認識。“澄懷味象”清楚地反映了宗炳對主體對畫面感知的審美態度的關注,而王微注重畫面的特色形式如何通過自己的操作調動主體的情,不再強調主體本身應有的審美條件。主體意識直接反映在畫面中,是不以繪畫為中介、傳達主體與自然的過程。雖然王微和宗炳都強調山、水、人的統一,都強調藝術的“感性”審美效果,但,王微顯然更傾向于表現人類主體的情感。最后一段“此畫之情也”,符合后來文人畫家的審美情趣、審美情趣和藝術精神,這就達到了他“愉悅性情”的目的。
參考文獻:
[1]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2]陳傳席.六朝畫論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3]凌繼堯.中國藝術批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