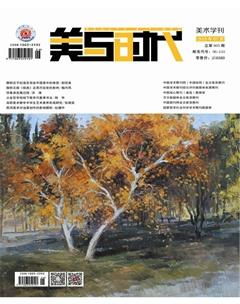從顧愷之《洛神賦圖》看藝術的自覺
孫麗媛

摘 要:魏晉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蕩的時期,也是民族融合和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人們的社會意識、倫理準則、價值觀念、審美品味等方面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魏晉玄學與人物品藻風氣的興起,促使人們超越了既有的社會倫理規范,發現和肯定了自我,并且對當時審美文化和審美意識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為這一時期美學的發展提供了形而上和方法論的基礎。在繪畫藝術中,這一時期人物畫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繪畫精神上尤其注重人物精神氣質(即“神”)的刻畫,這在顧愷之的名作《洛神賦圖》中有著最集中的體現,這足以表明了繪畫在藝術上的徹底覺醒。
關鍵詞:顧愷之;《洛神賦圖》;藝術自覺;魏晉時期;人物品藻;人物畫
一
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魏晉南北朝時期,王朝更迭快,社會動亂,民族矛盾突出,士人們深陷政治漩渦,一些士大夫成為統治集團斗爭的犧牲品。連年的戰爭徹底打破了人們現實生活的正常秩序,政治危機與生活危機交織,加劇了士人們對現實的憂患、恐懼等,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必然引起人們對于生命的傷感與依戀,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嘆彌漫于整個時代。種種面對這生死的哀傷、錯愕,不僅僅是社會動蕩的反映,更是士人對生命價值的反思,他們渴望在精神上得到慰藉,顯然在漢代意識形態上占統治地位的兩漢經學已經不合時宜,士人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轉向內心世界,由對現實人生的關注轉向對抽象玄理的探索,開始重新思考生命、宇宙、人生與社會的本原。由此,研究“玄遠”之學的魏晉玄學應運而生,魏晉玄學通過討論有與無、體與用、本與末、形與神、性與情、名教與自然等天人之際的各種問題,第一次明確提出并區分外在與內在、現象與本體、有限與無限的關系。士人們擺脫綱常名教的束縛,帶著自己對歷史與現實的真切感受投入討論,他們任酒使氣,縱情享樂,論道談玄,窮理盡性,詩懷哲思,這顯然是對漢儒“發乎情,止乎禮”的背叛與超越。李澤厚指出這個時期意識形態領域內文化主題就是“人的覺醒”。其中一個重要體現便是主體人的美以空前的規模進入品藻的視野,人物品藻成為魏晉玄學的一個重要內容。魏晉之后,漢代注重的德行、操守等不再是人物品評的重點,轉而表現為對人物才情、個性、氣質的激賞,對人物精神氣質的褒揚和人格美的提升。這種品藻人物的特質,在《世說新語》中有集中而豐富的體現:
時人目王右軍,飄若游云,矯若驚龍。
時人目夏侯太初,郎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我們可以看出其中主要強調對于人物的體貌、儀容、姿態、神采、氣度的品賞,通過大量使用“神”“情”“風”“韻”“姿”等贊美人物,充滿了人性觀照,對人性美的注重就是對精神的注重,表現出一種富有濃郁審美意味的情致。這時期對于人物的品鑒不再是實用的、功利的、世俗的、表面的,而是直率的、真切的、本質的、審美的,不再是基于倫理道德上的善惡褒貶,重要的是真率曠達的人物真性情的流露與展示。人的性靈、才情超越了既有的倫理規范,蘊含在內的是人格美的發現和主體意識的覺醒,這種從政治倫理到人物精神審美的轉變,自然萌生出富有內在精神審美意味的生命情調與生命自由,以及整個精神氣度所散發出來的曠達、蕭逸之感,它意味著一種審美人格的自覺。這種新的人生哲學對美學和藝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極大地促進了審美意識的自覺與普及,直接廣泛地影響到藝術的創造與欣賞。此后,這種神情超逸、胸襟闊達的人格之美、神韻之美,成為當時中國美學和藝術中的獨特內容,“以至于中國美學竟是從‘人物品藻之美學演變而來”。在繪畫藝術當中,人物畫的創作達到了空前的解放和發展,人物形象的表現深入到表現對象內心的精神世界,畫家開始強調人物超脫的個性和精神氣質。東晉顧愷之明確提出的“傳神”是人物畫表現目的,其重要貢獻就是將用在人物品藻中的“神”移在藝術創作中來,把“神似”看作藝術創作的最高標準。畫家運用審美的眼光捕捉人物的風神、風韻、風姿與神態,真正將繪畫自身的審美意義提高到一個層面,表現出對藝術審美品格的追求,這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顧愷之的名作《洛神賦圖》,擺脫了繪畫的宗教、政治、社會倫理的意義,描繪了最美的永恒的藝術題材——愛情故事。
二
《洛神賦圖》是東晉大畫家顧愷之根據三國時期杰出詩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賦》一文為藍本而創作的,描繪了一個凄婉纏綿、動人心魄的神話愛情傳說。原作由于年代已久早已失傳,我們現在可以見到的《洛神賦圖》被認為是宋人的摹本,但在這摹本中我們依舊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神韻情致以及極富感染力的神秘氣氛。曹植的《洛神賦》詞藻優美華麗,情節緊湊,將人神相隔,雖可相戀卻不可相守的悵恨凄哀之情描繪得至美、至真。顧愷之以賦作圖運用浪漫主義手法極富詩意地還原了曹植原作的意境與情致,畫面是類似連環畫似的長卷形式,圖中分別描繪了邂逅、定情、殊途、分離、悵歸五個情景,將故事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按情節順序組織于長卷中,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將神話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交融,整幅畫面呈現出如夢如幻、神人交融的幻境。《洛神賦圖》最大的特點便是人物的“傳神”,《世說新語》有關于顧愷之人物畫創作實踐的記載: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何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睹中。”
顧愷之在這里指出人物的傳神主要在于眼睛而不是形體,通過人物眼睛的刻畫以體現出對象的心理特征和精神面貌。在劉劭的《人物志》中就談到:“征神見貌,則情發于目。”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人物靈魂都集中在眼睛里,應該承認,眼睛對于揭示人物的精神、氣質、個性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畫作中“子健睹神”一部分,首先呈現在觀者面前的是一行人“日既西傾,車怠馬煩”的狀態,曹植就在“精移神駭、忽焉思散”極度疲累、神思散漫的精神狀態下忽“睹一麗人”。曹植身體微微前傾,生怕驚動女神而下意識地伸出雙臂擋住侍從,目光灼灼注視著洛水河畔上的洛神,畫家巧妙地通過這一瞬間的動作將主人公又驚又喜、神情既驚訝又極為專注的目光表現得生動傳神。并且畫家在描繪其侍從的眼神時趨于程式化,眼神垂向地面,目光呆滯而相對木訥,與曹植如癡如醉的神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顧愷之不僅強調傳神的重要性,而且論述了人物傳神的具體實施策略,在《魏晉勝流畫贊》中記載了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
凡生人無有手揖眼視,而前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趣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
在這里顧愷之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悟對通神”,提出傳神的核心在于“悟對”,以“實對”表現人物的“神”,強調表現眼睛與他人、他物之間的對應關系以及人物情感、思想的交流。所以在《洛神賦圖》中畫家不僅實現對個體人物的點睛傳神,而且整幅長卷都是以洛神與曹植眼神之間的對視與交流為主軸線推進故事情節。通過巧妙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眼神的交流與呼應來制約畫中人物的空間位置及關系,不僅使得畫面結構具有秩序感,而且在人物的精神交流中更散發出情思的意味。在“定情”一部分中,曹植以玉佩相贈表達對洛神的愛慕之情,但深知人神道殊,遂以禮相待,表達出一種內心激動而外表矜持、惆悵猶豫、意態寡歡的復雜情感。在他面前的洛神婀娜多姿,含情脈脈,則表現出一種顧盼回首、進止難期、欲言未言的神情。在這樣默默相望中,二人對于彼此的愛慕、依戀與惆悵被準確地傳達出來。無論人物的距離遠近如何變化,這樣眼神遙相對望的軸線在畫中從未消失,或是洛神離開之際,或是曹植駕車追趕,二人的悵惘之情在洛神、曹植的眼神中精確傳達出來。長卷天衣無縫的場景連接,人物神情表達自然,觀者不自覺隨著二者飽含深情的對視回到曹植、洛神真摯的情境中。這樣的對視、這樣的目光,使人物內心深處對于愛情的憧憬與渴望、人物形態的內在本性與個體性被充分發掘,作品通過有限的生命形體追求無限的生命內蘊,在有限的尺幅中傳達出無限的意境,迂回曲折,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藝術張力。在此之前,繪畫藝術或是側重于彰顯社會政治穩定的圣賢,或是演繹倫理政治的忠孝節烈事跡,它固有美的形式,卻沒有美的自覺,人物形象乏于具體的細節與修飾,少個性表達,更缺主觀抒情,繪畫淪為鑒戒賢愚和道德教化的一種手段和倫理規范的工具。
三
同時,畫家已經注意到環境的描寫對于表現人物個性的重要作用,《世說新語》中的一則記載可看出顧愷之的美學思想: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里。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這表明畫家已經強調在相適應的自然環境中去表現人物的個性與精神氣質,這是借助于背景傳神。在《洛神賦》原文中,大量文字被用于描繪洛神的容貌姿態,以二人活動情節發展為故事走向依托,對山水自然景物描寫甚少,而畫家在忠于原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身的想象力與繪畫本身的特性,不僅將文章中描述的各類飛奔的靈獸如文魚、鯨鯢、玉鸞、六龍等形象具體化,且通過云、水、山、樹等自然景物的描繪與人物之間映照襯托,渲染出情與勢。在《洛神賦圖》中“邂逅”一段,曹植洛神初遇于洛水河畔,兩岸楊柳青青,在平靜的水面上,洛神手執拂塵,衣帶飄飄,風姿絕世,脈脈含情,似來又去,畫面上遠山掩映其間,水波湯湯、荷花亭亭、落日云霞、鴻雁游龍、蒙蒙云霧襯托出洛神的飄逸仙姿,一股似真似幻的浪漫氣息撲面而來,人物的神氣就這樣呈現出來,讓人沉醉其中。在“離別”一段當中,畫家極富感染力地描繪了賦中“六龍儼其齊首,載云車之容裔,鯨鯢踴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激昂熱烈、驚心動魄的場面。六龍齊首駕著云車,水面波濤駭浪,洶涌異常,鯨鯢大口張開在云車兩邊護航,動物描繪極其生動奔放且富有神采,華蓋旗幟飄揚,云車在天空中作飛馳狀,洛神依依不舍回首望向心上人。這樣盛大的場面襯托出如此令人悲憤的離別情景,將人神疏之無奈的愛情更加渲染得淋漓盡致。這樣的“借景傳神”與顧愷之提出的另一繪畫思想“遷想妙得”也是一致的,“遷想”就是發揮藝術想象,在人物畫創作過程中,只靠觀察是無法真正把握一個人的神韻風采,要設身處地地想,深入體會所反映對象的思想情感,準確地把握其精神本質及特征,突破人物的有限形體而深入地把握到人物的風采、神姿,即“妙得”。可見,為了突出人物的氣質與精神特征,為了傳神,背景是可以設置的,但其實更多是畫家發揮豐富的藝術想象“遷想妙得”的結果。在這里關于神話靈獸的描繪已不具備殷商青銅器中蘊含宗教神秘的意義,神話環境的特寫更不同于前代大肆鋪陳渲染宇宙自然讖緯瑞應的先天之兆,它在作品中為人物情思的表達而存在,為渲染曹植、洛神情感色彩而存在,與人物情感個性取得有機聯系,使得畫面意境的傳達更加鮮明突出。
四
畫中人物形象風采神氣的傳達不僅在于眉目神情、容儀風采的描繪,更體現在其特殊的繪畫語言風格和特征的運用上,顧愷之筆下的人物之所以能夠以“神”取勝,依托于筆墨運用而煥發出的格調美感。他創造出一種緊勁連綿、循環超乎的描法,線條粗細均勻,舒緩而圓轉,后人稱之為“春蠶吐絲”。他認為此能“助神”,他說:“服章與眾物既甚奇,作女子尤麗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艷姿”,“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慢之,亦以助醉神耳”。如此,服飾、衣髻有“助神”之能,而描繪其用筆線條亦有“助神”之效。洛神的形象在賦中被曹植極盡詞藻之華麗所塑造,如:“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搖兮若流風之回雪。”在《洛神賦圖》中,顧愷之發揮其豐富的想象力利用流動而翻飛的線條將洛神婀娜多姿、曼妙飄逸的形象淋漓盡致地刻畫出來。在表現洛神的形象時,其或飄忽于水面之上,或漫步于巖石樹林之間,肩部線條修長,衣袖落落垂掛,飄帶隨風飛揚,衣裙下擺夸張、線條密集以表現其優柔婉轉的態勢,在整體線條的疏密組合,以及飄逸流動的變化中不僅表現出自身的旋律美,更傳達出洛神優美的神姿容儀及柔情綽態。并且其運用各色線條的形態,以及組合關系表現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如利用寬松舒展、上下行筆的落落線條表現曹植雍容高雅的氣度,使其與周圍的侍者表現出明顯的差距。宗白華曾指出:“中國人物畫在衣褶的飄灑的流動中,以各式線紋的描法表現各種性格與生命姿態。”顧愷之春蠶吐絲般的線條不僅與他所創造的人物形象內心世界相表里,成為與內在心緒、精神面貌水乳交融般的整體。在這里,人物畫在質和妍上達到了高度和諧完滿的統一,顧愷之以出色的視覺語言效果高度詮釋了《洛神賦》中所蘊含的詩意。
從“傳神寫照”到“悟對通神”,再到“遷想妙得”,顧愷之在這里提出了一系列有層次、有深度的“以形寫神”的具體理論,建構了一個具體的“傳神寫照”的繪畫美學體系。在繪畫藝術語言的表達上,透過筆勢線條的流麗表現,傳神的人物形象,傳達出一種人性美的高度。
結語
人物品藻對個體的審美性地欣賞對魏晉六朝人物畫的成熟發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的人物品藻美學,不是臧否人倫、品議高下,而是著重于人物精神的欣賞,尊重人物的個性和情感,這樣一個不滯于物、不拘于禮的時代也成就了藝術上的繁榮。《洛神賦圖》中,無論是畫面中山水風物的描繪,還是人物眼神極致的傳達、優美靈動的線條的營造,都在為人物的“傳神”所服務,“傳神”成為這個時期繪畫表現以及品評的標準。魏晉“人的自覺”帶來“美的自覺”,藝術美學開始由漢代重視道德倫理規范轉向重視生命個性本體的觀照,繪畫藝術在功能的表現上已經發生質的轉變,其超越了實用的、功利的目的,轉而為表現美的自覺意識,完成了由社會倫理美到完全高度自由藝術美的轉型。
參考文獻:
[1]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新知三聯書店,2014.
[3]陳傳席.中國繪畫理論史[M].北京:三民書局,2014.
[4]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王毅.神韻:從漢末人倫鑒識到魏晉人物品藻[J].云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0(1).
[6]周宗亞.故宮藏《洛神賦圖》之圖像研究[D].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
[7]吳中杰.中國古代審美文化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陳望衡.中國古典美學史[M].武漢:武漢人民出版社,2007.
[9]葉朗,朱良志.中國美學通史:第3卷 [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