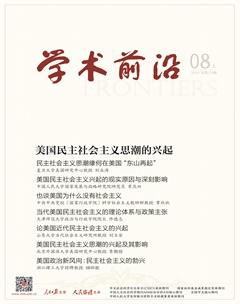我國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現實困境與對策
楊世盛
【關鍵詞】民事檢察監督 ?指導理念 ?立法對策 ?協調機制
【中圖分類號】D925.1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5.010
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設立,對于保障民事訴訟裁判結果的公正及民事訴訟程序的依法運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在2012年的修正借鑒了司法改革的成果,對民事檢察監督制度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但該制度在現實中的運行依舊存在著困難,需要我們在實踐與理論中不停地探索加以改善。
我國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修改
由于《民事訴訟法》在2017年的修正中,并未涉及民事檢察監督制度,此處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探討主要以2012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為大背景。我國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確立與修改經歷了一個漸進式的發展歷程。1991年4月9日,我國《民事訴訟法》正式頒布后民事檢察監督制度才得以確立并獲得踐行。2007年10月28日,針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申訴難”和“執行難”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修改條件相對成熟、反響比較強烈的審判監督程序作了修訂,其中涉及民事檢察監督的問題。在此之后的201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修正《民事訴訟法》,對民事檢察監督作了較為全面的規定,其修訂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是監督方式。此次修法新增了“檢察建議”這一全新的監督方式,以配合抗訴進行法律監督,進而推動檢察監督工作的開展。這一監督方式彌補了單一抗訴制的缺陷,促進相關國家機關增強內部管理,完善相關的規章制度,使得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效果能夠落到實處。
二是監督范圍。此次修法使得民事檢察監督的范圍擴張到了整個民事訴訟領域,其中包括了對民事執行活動的監督。這說明了立法者對民事檢察監督的重視,體現了民事訴訟的新理念,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同時,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調解書也被納入監督范圍之內,顯示出立法者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決心,杜絕此類不法事件的再次發生。
三是抗訴事由。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在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了檢察機關抗訴的四項事由,而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比抗訴的事由多了一項,即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2007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把抗訴事由和再審事由的規定整齊劃一了,并且在此基礎上將事由的事項增加至十三項。2012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仍然維持抗訴事由與再審事由的一致性且數量上保持不變,但對局部作了調整。立法對抗訴事由與再審事由的日漸細化,并且納入了程序性違法事由,使得檢察機關行使檢察監督權的可操作性增強了,同時反映了立法日漸重視程序性監督。[1]這是司法觀念的一種改變,更是我國法治的一大進步。
四是監督保障措施。2012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因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的需要,可以向當事人或者案外人調查核實有關情況。”由此檢察機關的調查核實權在立法上得以確立,使檢察機關的監督功能能夠得到有效發揮,保障了檢察機關的監督權威。需要注意的是,權力的行使并不是毫無邊界的,規定調查核實權的目的是便于檢察機關發現相關信息以作出相應的決定,檢察機關并不能濫用此項權力以追求其他目的。[2]
我國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現實困境
雖然我國立法已經對民事檢察監督制度進行了細化與完善,但該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運行依舊存在許多困難。為此,筆者通過立法與司法兩個層面來對現存的困境加以分析,為后文的論述奠定基礎。
立法層面的困境。如前所訴,我國立法多次對民事檢察監督制度進行修改,2012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對之修改更是史無前例,但同時也發現,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在立法上的規定都較為原則化,缺乏相關的程序性規則。此時,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顯得尤為重要,以彌補立法上的疏漏,使該制度的功能得以彰顯。通過對當前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相關立法規定的研究,筆者認為如下兩個方面亟需作為重點予以完善:
第一,民事檢察建議的立法缺失。2012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增加了檢察建議這一全新的監督方式,并且將檢察建議的具體適用情形規定在了第二百零八條與第二百零九條。與此同時,《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以下簡稱《監督規則》)對民事檢察建議所適用的效力、程序、條件等進行了細化規定,雖然看似可操作性增強了,但是依舊存在許多問題,沒法真正使民事檢察建議制度化和規范化。其中最為致命的是,民事檢察建議缺少跟進監督措施的規定。根據《監督規則》第一百一十七條的規定,檢察機關在法院對檢察建議處理錯誤以及未在規定的期限內作出處理并書面回復時,可以跟進監督。然而,到目前為止,具體規定檢察機關如何跟進監督的文件卻還未出來,這使得跟進監督被虛化,民事檢察建議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二,調查核實權的適用程序缺失。調查核實權是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不可或缺的一項權力,其對于落實好民事檢察監督有著重要的作用。[3]因此,我國2012年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正時,專門在第二百一十條對調查核實權作了規定。但這也是目前立法對調查核實權的全部規定,研讀該條文可以發現其只是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對于調查核實權的啟用方式、適用范圍、取得證據的效力等具體問題均沒有涉及,而相關司法解釋也未出臺。缺少調查核實權適用的具體程序,必然會導致將使調查核實權無法圓滿地實現,因此,亟需建立相關的程序性規則。
司法層面的困境。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在立法方面的不足,導致了該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出現了困難,主要有:
一是一些地方檢察機關的內部權力實現機制存在缺陷。一些地方檢察機關有著“重刑輕民”的傳統,刑事案件是其工作的絕對重心,這就導致了民事檢察監督工作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個別地方檢察院民行部門內的檢察干警多是從其他科室抽調而來的,往往是專業不對口,面對專門的案件會出現有心無力的情況,民事檢察工作無法有效進行。除此之外,少數地方檢察院民行部門與有關部門的協調也不夠。例如,對于案件的受理是由控申部門負責,但控申科干警往往對民事檢察監督缺乏足夠的認識,時常會出現該受理的案件而不受理,這也使得當事人會以為檢察機關是有意不作為,破壞“檢”“民”關系的和諧。[4]
二是檢察院與法院對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存在不同認識。雖然我國法律規定檢察院有權對民事訴訟活動進行法律監督,但并未規定法院有接受監督的義務。在民事訴訟中,法院控制著訴訟的進程,屬于絕對的主導者,而檢察院的監督依附于法院,相對來說屬于從屬者,由此導致了審判機關在某些情況下會拒絕檢察監督。[5]為避免這一情況的出現,充分實現檢察機關的民事監督權,有必要對審判機關的義務進行明定。
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相關對策分析
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完善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多層次多角度同步進行。筆者認為,首先,應當從轉變相關的指導理念入手,使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價值得到初步實現。其次,針對該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主要缺陷,提出相應的對策以使其更具有操作性。最后,從協調機制方面,改善檢察機關的自身條件和“檢”“法”兩院的關系,使民事檢察監督制度最終得到落實。
重構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相關理念。從制度的頂層設計來思考,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實施之所以會遇到諸多問題,主要與指導理念較為滯后有關,落后的理念導致了制度的價值難以實現。若想有效實施該制度,進行理念重構不僅重要且非常關鍵,具體可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檢察機關需要更新對監督的認知,不再推行干預型監督模式,而是調整為保障型監督模式,做到根據法律規定來實施相應的監督工作,保障民事訴訟活動的有序進行。檢察機關開展民事檢察監督工作,一方面,需要保障相關當事人能有效行使訴權;另一方面,又需要保障法院依法行使審判權,使他們都在法律的框架內活動。
二是檢察機關的監督需要由實體型監督向程序型監督發展。隨著我國法治水平的不斷提高,程序正義的諸多價值被不斷挖掘,其有著實體正義無法比擬的優勢,因此,作為監督手段的民事檢察監督更是要保障程序的公正。[6]2012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對檢察監督的相關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程序型監督的特征,但程度遠遠不夠,需要在日后的修法中繼續加強。
三是檢察監督需要趨向協同型監督。在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獲得不斷發展之后,監督所具有的整體性日益凸顯,這就要求檢察機關適時調整監督理念,摒棄對立型監督,堅持協同型監督,以求實現法律的統一實施。[7]檢察機關所進行的監督,并不是為了破壞審判的獨立性,也不是為了制約當事人自由行使訴權,恰恰相反,其是為了審判活動的依法推進與當事人的權利得到有效救濟。
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立法對策。對于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在立法層面存在的現實困境,筆者在此處主要針對問題比較突出的民事檢察建議和民事調查核實權進行討論。
關于民事檢察建議,其雖然被寫入了立法,但由于立法規定比較簡陋,尤其是跟進監督措施的缺失,導致了該制度在實踐中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因此,重中之重是從立法上完善民事檢察建議跟進監督措施,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規定:第一,對跟進監督程序作進一步的規定。對于人民法院錯誤回復、逾期回復或拒不回復民事檢察建議的情況,僅僅規定檢察機關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交抗訴申請是不夠的,需要在此基礎上補充規定:即檢察機關可以將有關情況向上一級檢察機關反應,由上一級檢察機關向其同級的法院提出檢察建議。這樣規定可以讓上級檢察機關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最有利于實現監督效果的方式,同時也讓檢察建議應有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第二,強化對人監督的規定。民事檢察建議將監督對象擴大到了對人監督,改變了只是對事監督的情況,為了進一步發揮民事檢察建議應有的功能,有必要強化這方面的規定。[8]例如,針對法院錯誤回復、逾期回復或拒不回復檢察建議的情況,法律可以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向法院提出變更辦案人的檢察建議。第三,新增向媒體公布的規定。檢務公開已經是不可阻擋的一種趨勢,檢察機關向社會大眾公開終結性法律文書是檢務公開的題中之義。[9]檢察建議自然屬于檢務公開的范疇,對于法院多次不予回復、超期回復或者有錯不糾的同時,對社會造成嚴重影響的民事檢察建議案件,檢察機關需要向媒體公布具體的辦理情況與終結性法律文書。
關于民事調查核實權,立法同樣規定得較為粗疏,使得檢察機關在行使該權力時存在諸多困惑。為解決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調查核實權的啟用方式。我國現行立法并沒有對調查核實權的啟用方式進行明確規定,由此導致了檢察機關在實踐中依職權啟用還是依申請啟用比較混亂。在筆者看來,調查核實權是檢察機關職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檢察機關依職權啟用合乎情理,不需要以當事人提出申請作為前提條件。因為檢察機關對相關事實進行調查核實的根據是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存疑和法院可能存在違法行為,而并不必然與當事人的申請有關。當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可能引起檢察機關提起檢察建議或抗訴時,即使缺少當事人的申請,對于相關證據檢察機關也需要進行調查核實。而當證據與檢察機關提起檢察建議或抗訴無關時,即使有當事人的申請,檢察機關也不會進行調查核實。第二,調查核實權的適用范圍。調查核實權是檢察機關實現民事檢察監督的手段之一,其服務于檢察監督職能的履行,同時更是派生于檢察監督職能的權力,所以其適用范圍應與民事檢察監督的適用范圍相同,應對生效的民事裁判、調解書確定的事實和法官的違法行為進行調查核實。[10]具體來說,檢察機關應當重點對如下幾種可能影響案件公正處理的證據進行調查核實:一是可能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證據,以及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變更管轄等程序性的證據。二是判決、裁定、調解書可能存在錯誤和審判人員的訴訟行為可能違法的證據。三是在原審時當事人基于客觀原因無法有效收集的主要證據,或當事人以書面形式申請法院調取證據,或是法院應依職權調取證據,但法院不調取的這一類證據。四是被作為定案依據但涉嫌偽造的證據。五是在申訴階段,申訴人提出的足以引起檢察機關懷疑的新證據。第三,證據的效力問題。檢察機關調查核實后所得到的證據,是自動生效進而法院直接作為定案依據,還是必須經過法庭質證程序后才能生效?法律對此未明確規定,筆者更贊同后者。調查核實所得到的證據始終是檢察機關單方面取得的證據,這一點與其他主體提交的證據并無明顯區別,出于考慮證據的客觀性、真實性與合法性,有必要將證據放到法庭上公開質證。[11]另外,將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進行質證,有利于讓各方當事人接受證據,進而接受最終的判決,同時也有利于制約檢察機關,使其合法正當地行使調查核實權。
構建內外聯動的協調機制。需要明確的是,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具有其他制度所不具備的功能,而要確保該功能獲得充分發揮,構建內外聯動的協調機制必不可少,具體應當做到如下兩點:
第一,構建檢察機關內部辦案機制。“打鐵還需自身硬”,要使民事檢察監督順利進行,檢察機關首先必須從改善自身條件做起,完善內部辦案機制。具體來說需要做到如下兩點:其一,進一步推進隊伍專業化建設。檢察機關在合理配備好人員結構的前提下,需要將隊伍的準入條件適當提高。不管是民行干警的招錄工作,還是相關的工作調動,均應考慮專業對口的問題,優先招錄具有訴訟法、民商法專業背景的人,以提高隊伍的專業化水平,使民事檢察監督落到實處。與此同時,檢察機關有必要對相關干警推行定期培訓制度,針對新進隊伍的干警,可重點進行理論方面的定期培訓,針對老干警,可著重圍繞新出臺的司法解釋及疑難問題來定期培訓,以使干警們能更好地履行監督職責。其二,確保人員能夠相對穩定。此處的穩定并非要做到人員的永遠固定不變,而是在進行崗位輪換時應持慎重的態度,確保工作不受影響。
第二,構建檢察機關外部協調機制。完善外部協調機制,增強檢察院和法院之間的交流,促進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才能使民事檢察監督制度最終得到貫徹落實。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考慮:其一,加強溝通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統一性認識。“檢”“法”兩院可以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選擇舉辦講座、聯誼會或者其他形式進行交流,將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集中進行討論并達成共識。其二,推進“檢”“法”兩院聯合發文。由于法律具有滯后性,無法及時地應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此時司法解釋的頒布就顯得至關重要,尤其是“檢”“法”兩院聯合發布的司法解釋。針對立法中未作規定而實踐中亟需解決的問題,檢察院與法院可以通過聯合頒布司法解釋對其進行回應,這樣既能夠快速地解決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又能夠維護法律的穩定性。
注釋
[1]江偉、謝俊:《論民事檢察監督的方式和地位——基于憲法和民事訴訟法的分析》,《法治研究》,2009年第4期,第3~9頁。
[2]劉宏宇:《我國民事檢察制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7頁。
[3]高永剛:《論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第76~80頁。
[4]陶伯進、曹國華:《民事執行檢察監督的法理基礎與制度探索》,《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第37~42頁。
[5]湯維建:《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定位》,《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第32~47頁。
[6]康猛:《民事訴訟監督中調查核實權的行使與保障》,《遼寧警察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第14~20頁。
[7]張雪妲、李強、常海蓉:《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理論探析》,《人民檢察》,2017年第13期,第49~52頁。
[8]李潤生、史飚:《民事檢察建議制度新探——以新〈民事訴訟法〉為視角》,《湖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63~66頁。
[9]高一飛、吳鵬:《論檢察機關終結性法律文書向社會公開》,《中國刑事法雜志》,2014年第3期,第70~80頁。
[10]買文毅、陳鵬飛:《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思考》,《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16年第2期,第73~78頁。
[11]金石:《新修改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實施現狀、問題及完善》,《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151~158頁。
責 編/肖晗題
Abstract: Civil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legal sub-system, which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judicial justice. However,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in our country still faces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absence of legislation on civil procuratorial suggestions, the absence of application procedures of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rights,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mechanism for realizing the internal power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Therefore, we should start with changing the relevant guiding concepts so as to mak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ivil supervision system fare in a correct direction; find the corresponding legislative solu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people and disclose information to the media; and construct the internal case handling mechanism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so as to put the civil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system into practice.
Keywords: civil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guiding principle, legislative solutions, coordina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