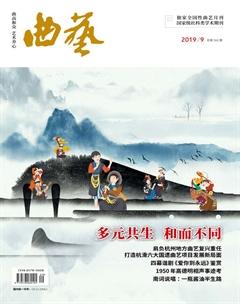新疆曲藝現狀與創新發展
周建國
新疆有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回、柯爾克孜、錫伯、塔吉克、烏孜別克、塔塔爾、達斡爾、滿、俄羅斯這13個世居民族,各自的民眾一百多年以前或者更早時候就在新疆定居。新疆各少數民族過去沒有“曲藝”的概念,編纂《中國曲藝志·新疆卷》時,各民族專家一同確定了37個曲種收入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開展以來,經過多次評定,截至2018年,列入國家級保護名錄的曲藝項目有:維吾爾族達斯坦(敘事長詩)、恰克恰克(說笑話),漢、回族新疆曲子,哈薩克族達斯坦(敘事長詩)、阿依特斯(對唱)、鐵爾麥、托勒傲,蒙古族《江格爾》《格薩(斯)爾》,柯爾克孜族《瑪納斯》。列入自治區級保護名錄的有:維吾爾族萊派爾,漢、回族新疆雜話,蒙古族圖兀勒(敘事長詩),柯爾克孜族達斯坦(敘事長詩)、阿依吐秀(對唱),錫伯族秧歌牡丹(曲子)、朱倫呼蘭比(念說)、更心比。其中,有的項目是以曲目入選,它們的表演形式又應屬于某個曲種。這樣算來,列入兩級保護名錄的曲種共有15個。還有22個曲種,大部分屬于人口較少民族的曲種,已經消亡或者瀕危。
新疆各民族曲藝歷史悠久,曲目豐富,形式多樣。同樣一個曲種在同一地區,不同藝人可能伴奏樂器不同、曲調不同、動作不同,甚至同一藝人,不同時間、場合表演也不盡相同。還有一個共同特點是,從來沒有或極少以某個曲種為謀生手段的、有固定演出時間和場所的職業曲藝演員。所以,新疆的民族曲藝是一直生成、成長于民間的,在民間自發傳承著。
列入兩級保護名錄的曲種,各級政府對其保護傳承非常重視。而保護傳承的內容和形式,則需要我們認真思索。如何才能達到“保護傳承”的目的呢,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一
“與時俱進”是藝術發展的共同規律,曲藝也不例外。目前,各個民族的傳統曲種、曲目,都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民族、群體的生產生活、社會歷史、文化變遷,是歷代民間藝人創作和流傳下來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民族文化持續發展的根脈。這種民間文化,依靠口耳相傳保留至今。每位民間藝人在承傳過程中,在與受眾的交流互動中,都融入了自己的智慧創造,而使曲目更加豐富完善,使表演更加引人入勝。農牧民們把它當作主要的娛樂方式,休閑時可以唱可以聽,回到氈房、住處,鄰居們坐在一起,也會聽藝人說唱、表演,樂而忘憂。那時候既有傳承者,也有聽眾,文化環境自然天成。現在這樣的環境正在消失。年輕人已經不安于傳統生活方式,而選擇走出草原、農村。許多農牧民科學種植、勤勞致富,也不想再過那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人們住進了定居點,娛樂方式日益多元,很少再有湊在一起彈唱的機會。現在幾乎找不到把主要精力放在背誦傳統曲目上的中青年表演者。
社會的進步、眼界的開闊、開放的心態和多元的追求所造成的文化環境改變是不可逆轉的,這也使得有些項目看起來學的人多,但傳承人能力和水平其實大為縮水。2007年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傳承人,多是新中國成立前后年富力強的一代,像《江格爾》國家級傳承人加·朱乃(已去世),在20世紀80年代普查時,提供了25章、24000余行唱詞。現在按照蒙古族專家賈木查的標準,能背唱七章就有評選傳承人的資格了。再如阿勒泰地區哈薩克達斯坦國家級傳承人哈孜木,80多歲,能演唱100多部達斯坦,都錄了音。而后繼者能唱五六部就是很難得的了。其他曲種,凡是曲目唱(說)詞有幾百行、上千行的,都有類似的問題。
這其中還有些實際的考量:學唱學背這些曲目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不足以使人們舍他趨此,反而會誤工費時耽誤發家致富。還有,背誦幾千行、幾萬行,說唱給誰聽?農牧區這樣的文化空間不存在了。官方組織的演出場次很多,但又不需要這樣的背誦。學唱背誦只能作為評定傳承人、享受傳承人待遇的依據,而評定的機會又甚渺茫。所以,盡管仍有人在背說背唱,但日益萎縮是肯定的。
史詩是只能豐富、不能再造的,達斯坦則可以由民間藝人創造并演唱、流傳。我在北疆阿勒泰地區福海縣采訪時,有位演唱藝人、詩人表達了要創作新時代哈薩克達斯坦的愿望,我是支持的,希望能夠創作成功并流傳下去。創新是一方面,同時也應當重視從傳統文本中發掘有益的人物、故事片段,經過改寫、移植,用影視、戲劇、畫書等形式演出、出版,擴大經典的知名度、影響力,現在已有這樣的嘗試。
二
新疆各民族曲藝是有著隨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傳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也反映在曲藝作品中,在謳歌共產黨、謳歌新時代、謳歌新生活的同時,曲藝本體也得到傳承發展。比如阿凡提的故事,他的機智、詼諧、抑惡揚善,已成為一個超越時空的符號。伊犁有位伊薩木·庫爾班被贊為“當代的阿凡提”,是恰克恰克的國家級傳承人,他講的笑話,就不是重復過去的故事,而具有了時代特點。比如“四人幫”橫行時,某編輯經常在報紙上發表一些極“左”文章,讀者很不滿意。在座談會上,這位編輯問伊薩木:“我們的報紙哪一版最受歡迎?”伊薩木回答:“登載您的文章的那一版呀。”那位編輯好奇地問:“為什么呀?”伊薩木說:“許多人說,那一版用來卷莫合煙,抽起來最有味道了。”這是很典型的阿凡提式的諷刺方式,幽默短小,耐人尋味,“包袱”抖得也很巧妙。
新疆雜話是流傳于民間用漢語講說的一種曲藝形式,它由一人表演,不用道具,無需化妝,全靠演員運用方言俚語,汲取生活中的典型事物,通過生動形象的表演,達到針砭時弊的目的。自治區級傳承人趙國柱在《堅決剎住吃喝風》里,諷刺檢查團以檢查之名下鄉,“坐著車子轉,隔著玻璃看”,“一杯酒一桶油,一頓飯一頭牛。”當問公牛為什么跑時,公牛答“鄉里來了檢查團,檢查完了要會餐。雞鴨魚肉全吃遍,現在興下的吃牛鞭。”當問母牛為什么跑時,母牛答“這幫人沒法提,臭味相投真可氣。他們不光吃牛鞭,吃了牛鞭還吹牛皮。”“牛們”的回答,讓我們欲笑不能,我們想到的只有一句話:中央“正風肅紀”何其必要!
現實題材的創作曲目里,還有一種是歌頌性質的曲目,反映了群眾對“一帶一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批判三股勢力等的正面歌頌,起到了凝聚人心、團結奮斗的作用。哈薩克族托勒敖《歌唱伊犁》,就以彈唱形式歌頌了伊犁的美麗風光和富裕生活。其實,這種歌頌題材作品,很多曲種都有。這些曲種有個共同特點,就是短小活潑,比如鐵爾麥、快板、恰克恰克等。它們是群眾集會中的常客,常有新作品呈現,傳承狀況也比較好。美中不足的是,對阿依特斯等即興演唱的曲種,限制表演時間,還沒有盡興、達到高潮,就得結束了。另外,因為這類展演都是政府組織的大型演出,有些作品難免出現套話雷同多,諷刺性、趣味性弱的不足,不似過去民間聚會演出那么熱烈、灑脫、娛樂性強。
三
民族民間曲藝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首先要加強學習,轉變觀念。民間藝人是民間曲藝創新的主力。所以應當組織民間藝人自覺學習黨的大政方針,學習必要的藝術理論,樹立開放的、發展的觀念。他們生活在基層,知道百姓最需要什么,曲藝最應關注的是什么。如果他們對黨的方針政策理解了,提高政治站位,作品針對性就更強,社會效益就更好。如果他們能改變一成不變的狹隘思想,廣收博采,銳意革新,自覺提升曲藝本體面貌,那么,創新發展也便容易多了。
其次,發揮曲藝有人有事、有情有趣、移風易俗、寓教于樂的特點。《文心雕龍》提出了“諧”“隱”的概念。“諧之言,皆也,詞淺會俗,皆悅笑也。”即是說,諧是一種語言淺顯、受眾廣大、可以引人發笑的表達方式。“隱者,遁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即以隱約的言辭來暗藏某種意思,用曲折的譬喻來暗指某種事物。老百姓的喜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多樣。語言應該是老百姓一聽就懂的村諺俚語,而且是有內涵有意味、百姓愛聽愛琢磨的。它的隱意,不是晦澀難懂的,而是稍加回味便可會意一笑的。相聲《五官爭功》《逗你玩》都是這樣的作品。
李漁在《閑情偶寄》里說:“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者,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這樣的機趣語言,往往帶有諷刺嘲笑的意味,在曲藝的唱詞、表演中時時體現出來。快板《王婆子罵雞》說的是王婆子養的蘆花雞被饞婆子偷吃了一只,她就扯開嗓子“罵呢罵呢實罵呢。”由于使用了回族方言,特別印象深刻:“鐵匠偷吃老娘的雞,火渣子蹦到個背心里,不過三天燒死去。石匠偷吃老娘的雞,石渣子別到個眼窩里,不到三天磨死去。木匠偷吃老娘的雞,錛子砍到個腳心里,不過三天疼死去。”王婆子罵得痛快,觀眾聽著好笑。
在蒙古族史詩《江格爾》里,有很多對江格爾及其他人物極具夸張的描繪,這樣的描繪超乎常人的想象,也會激起聽眾好奇的傾慕的心理。比如對阿蓋沙布德拉公主的描繪:“在她發出的輝光下,女人可以穿針引線。在她閃出的光芒下,男人可以打更放馬。即使黑夜里裁衣,也不會失手裁壞,即使袖子里納靴,也不會錯針納壞。”
還有在情節設計上的奇幻詭異,非同一般,展示了民間藝人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在《格斯爾》這部蒙古族史詩里,說格斯爾還是個拖著鼻涕的小孩子的時候,就娶了三個夫人。有一天他出去打獵,碰到一個女孩,射箭比賽他輸了,摔跤比賽摔了個平手,接著他們跳進水中較量。格斯爾判定她是龍王女兒莫爾根,便令神馬施展魔法刮起寒風,使河水瞬間結冰。格斯爾先跑上岸,躺在馬鞍墊上,蓋上了衣服。摩爾根耐不住寒冷,爬上岸來,衣服又被大風吹走了,只好鉆進格斯爾的衣服里,以身相許。這個情節的想象力真是非常大膽、非常有趣的。
哈薩克族阿依特斯,是男女即興對唱的曲藝形式。在對唱中,互相詰難,比賽聰明機智、應變能力,直到使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在過去有一場比爾江和薩拉的對唱,比爾江為了挽回敗局,采取了揭短的辦法:讓薩拉又老又丑、已有兩個老婆的丈夫當眾站起來,引起一陣哄笑。薩拉羞愧難當,唱道:“我可以和阿勒泰最好的阿肯對唱,但命中注定不如一條野狗。”唱完后,扔掉冬不拉,像駝羔般哭嚎著認輸了。這樣的揭短已不足取。但謔而不虐、以攻為守、絕地反擊,在阿依特斯中仍是屢見不鮮的。
這些例子,生動說明傳統曲藝為了博取聽眾的眼球而采取的一些手法,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曲藝當中的諧趣,類似戲曲中的插科打諢,時時都會抖露出來。李漁把它稱為善驅睡魔的“人參湯”。這種“人參湯”,曲藝也同樣需要。
再次,要創新發展民族民間曲藝形式。新疆各民族民間曲藝都是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已經相對固化了。因為始終沒有職業的創作者、表演者,沒有走向市場,缺少競爭,也就缺少發展。《瑪納斯》也好,《江格爾》也好,其他長詩的說唱、彈唱也好,都是在草地上、氈房里一坐就開始說說唱唱。因為坐在那里,雙手又拿著樂器,就束縛了手臂、腿腳的表演動作,聽眾只是聽他的唱詞、說詞而已。很自然地,這樣“重內容”的表演,吸引人的辦法就太單調了。漢族也有類似的形式,但演員的聲調、表情、動作,一招一式,一顰一笑,都是精心設計的“藝術”,而不是簡單的“背書”。
新疆曲子已經故去的盲藝人張生才,能彈唱324個曲子、秦腔劇目、道情曲目,是為數不多的職業藝人之一。這樣的彈唱者現在幾乎沒有了。一個原因是,他們唱的還是老腔老調,年輕人不喜歡。音樂怎么出新,老藝人沒有這種意識,也做不到。另外,彈唱形式單調,也沒有表演動作,不如連歌帶舞熱鬧,也不如靠情節吸引人的小戲更受青睞。其他短小活潑的曲種,都面臨表演上如何創新的問題,否則很難適應觀眾日益提高的審美需求。
現在我們看到的已經專業化的、流行的曲藝形式,無一不是在民間藝術中孕育出來的。近代相聲,據說是同治年間京劇丑角朱少文(藝名“窮不怕”)因國喪不能演戲,就改說“單春”(單口相聲),后收兩個徒弟,逐漸形成對口相聲;山東梨花大鼓是農民在田頭休息時說唱的,用破碎的犁鏵片伴奏,后來發展成有板式變化體結構的成套唱腔。所以,我們的專業曲藝工作者應當更加重視學習、研究民族民間曲藝,特別重視研究、解決民族民間曲藝面臨的困局。這既是傳統曲藝傳承所亟需的,也是民族曲藝事業發展所需要的。少數民族曲藝演員應當有更多機會觀摩學習交流,提高技能,創新觀念。各級曲協、專家也應把民族曲藝納入視野,給予關注,實現各族曲藝的共同繁榮。新的走紅全國的曲藝品種,可能就孕育在處于困境中的民間曲藝之中。
(作者:新疆藝術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