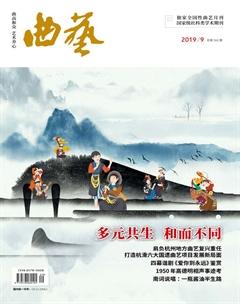中國少數民族說唱音樂本體特征與表達
崔玲玲
我國是由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構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這種多地區、多民族、多語言的環境,對我國各少數民族說唱音樂的形成與發展不僅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還對形成多種風格的說唱音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長期歷史的發展中,各民族說唱藝人根據本民族、本地區的音樂與文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說唱音樂形式。
中國少數民族的說唱音樂相當豐富,大多數的民族都擁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說唱音樂,如白族的大本曲,蒙古族的江格爾、好來寶與烏力格爾,朝鮮族的盤索里,傣族的贊哈,藏族的仲諧(或稱“格薩爾仲”,意譯是“‘格薩爾王傳說唱”)、折嘎與喇嘛瑪尼,維吾爾族的達斯坦,哈尼族的哈巴,壯族的末倫,滿族的太平鼓,赫哲族的依瑪堪等。
我國少數民族的民間說唱音樂大多都是在各民族民間音樂中的敘事性民歌、史詩祝贊詞、民間歌曲和民間器樂、民間歌舞音樂等形式的民間藝術相結合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形成一種獨立的、規模龐大的敘事音樂體裁的藝術表演形式。由于多方面的影響,我國各少數民族的說唱音樂發展并不均衡,有些民族的說唱音樂存在多種形式,且相當成熟,而有些民族的說唱音樂還處于敘事民歌和彈唱形式階段。
本文將從少數民族說唱表演形式、少數民族說唱音樂唱腔結構、少數民族說唱音樂與民歌三個維度互相關照的視角,對中國少數民族說唱音樂本體進行較為細致地解讀。
一、少數民族說唱表演形式
少數民族說唱音樂演唱的時間與場合較為靈活,在節日、禮儀活動、宴會或閑暇時,皆可邀請歌手蒞臨演唱助興,有時在較隆重的集會上演唱,有時在私人家庭中演唱。有些學者將我國漢族說唱音樂的表演形式歸納為:單口唱、對口唱、幫唱、拆唱、群唱、走唱六種。筆者通過梳理我國各少數民族說唱音樂的表演場所、表演主體、表演音聲、表演內容等方面,根據其是否使用伴奏和演唱人數等因素,總結出如下少數民族說唱表演形式:
(一)徒歌式說唱
就是一個人進行的說唱表演,沒有樂器進行伴奏。如蒙古族的說唱“江格爾”就有部分藝人進行徒歌式演唱;雙人以上的好來寶,一般也不使用伴奏;藏族的說唱中,很多種形式均無樂器伴奏,如“格薩爾”說唱中的演唱形式一般是單人表演,不用樂器伴奏。
赫哲族的依瑪堪也使用這類的說唱形式。其曲調變化隨意性較大,不受曲牌、句式長短和節奏限制;每一段開頭都拉長聲說個“阿郎——”。伊瑪堪在什么時候說什么時候唱,有一定的規律。在民間藝人表演到高潮的時候,聽眾常常要與藝人互動并發出助威或者感嘆的呼喊聲。
(二)自拉自唱式說唱
就是說唱藝人自己說唱自己伴奏,蒙古族說唱烏力格爾是由“胡爾奇”(四胡演奏者)手持低音四胡自拉自唱。演唱中有唱,有說,有念白,演唱的內容為民間故事和蒙古族長篇敘事詩《格斯爾傳》《青史演義》及漢族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其中《打仗曲》頗有特色,藝人們遇到熱烈緊張的場面時,會通過音樂的速度和節奏律動,密集的唱詞,加之用弓桿敲擊琴筒產生的擬聲,讓人聯想到刀光劍影的戰斗場面。蒙古族的一人好來寶也是由藝人用四胡自拉自唱。
哈薩克族的說唱月令中的“達斯坦”常由一人用冬不拉自彈自唱以英雄史詩或民間敘事長詩為內容,曲調簡短明快。善于演唱這種歌曲的被稱為“達斯坦奇”或“鐵爾滅奇”,他們是既具有彈唱技巧又具有即興填詞才能的歌手兼詩人。“達斯坦”音樂曲調平穩,近似說唱,音域較窄。維吾爾族的達斯坦也是由藝人們用彈撥爾或熱瓦普自彈自唱。
(三)一人演唱一人伴奏式說唱
即說唱藝人說唱時,另有樂師為演唱者進行伴奏,如朝鮮族說唱“盤索里”即由一人自說自唱,另一樂師用圓鼓或長鼓伴奏助興,兩人配合密切。白族的大本曲也是兩人表演,其傳統的表演形式是兩人分別坐于高臺上的桌子兩旁,一人說唱,另一人彈三弦伴奏,并同時用手帕、折扇和醒木為道具。
而傣族的“贊哈”演唱形式也是多為一人唱,另有樂手吹篳或拉西玎伴奏,如邀請了兩位或更多的歌手到場,則常出現賽歌的場面,有時可見到多位歌手輪流演唱的情況。說唱伴奏使用的樂器因地而異,西雙版納地區使用篳(簧管樂器,似巴烏)或西玎(弓弦樂器,似二胡),孟連等地使用玎列(彈撥樂器,似柳琴)。賽唱形式的贊哈演唱,帶有比賽性質,歌手需要廣博的知識和即興編曲的才能,經過針鋒相對的問答對唱,如果一方無法回答或答錯,則算失敗。
(四)多人演唱多人伴奏式說唱
是指在演唱說唱音樂時出現兩人或以上的藝人共同表演,一人或者數人進行伴奏的說唱形式。
土家族的“長陽南曲”表演特點除了有一人彈奏,另一人擊板演唱的形式以外,還有一人彈唱,二人對唱或多人齊唱等,偶有一人擊拍,數人奏三弦彈唱的形式。而伴奏中加進二胡、四胡、揚琴、月琴等樂器擔任間奏和幫腔,可以看出已受到高腔戲曲的影響。土家族的恩施揚琴屬于自娛自樂的演唱形式,最少也需要三人組合,分別使用揚琴、碗琴、鼓尺,輪番接唱,結尾處常有眾人和的“彩腔”。也有較大的表演形式,稱為“八音”,即揚琴、碗琴、三弦、月琴、二胡、京胡、鼓尺等八種樂器合奏。表演優雅而熱烈。
廣西壯族的民間說唱堂皇,是少則一兩人演唱,多則三五人演唱,以清唱為主,有時配木葉進行伴奏。流行于廣西西林、隆林等地一帶壯族說唱音樂萬播笛的演唱形式為女唱男伴,多人演唱多人伴奏的表演形式,伴奏樂器有月琴、二胡、嗩吶、小鑼、小鼓、簫、笛等,唱腔細膩,語言樸實,旋律優美。
從筆者整理的少數民族說唱音樂的表演形式上看,徒歌式的說唱和自彈自唱式的說唱音樂多流行于北方少數民族中,而一人唱一人伴奏式說唱音樂和多人演唱多人伴奏式說唱音樂多出現在南方的少數民族中。
二、少數民族說唱音樂唱腔結構
田聯韜的《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中將我國少數民族說唱音樂的唱腔結構分為單曲體和曲牌連套體兩種,筆者在借用這一分類時,又對其進行細致地劃分與解釋。
(一)單曲體
單曲體是以一個基本曲調反復演唱或者根據此曲調進行變化的唱腔結構。這種說唱結構從唐、五代時的變文開始到宋代的鼓子詞、陶真、貨郎兒,再到元明時期的寶卷、詞話,明清時期的彈詞、鼓詞等,其歷史發展過程較長。在我國少數民族說唱中采用此種結構形成的曲種相對較少,只有藏族的折嘎、喇嘛瑪尼,傣族的贊哈等。
“喇嘛瑪尼”,“喇嘛”意為“藏傳佛教的高僧”,“嘛尼”意為“佛教的六字箴言”,“喇嘛嘛尼”譯意是“藏傳佛教僧侶講唱的佛經故事”。它是流傳于西藏和四川省甘孜州的一種古老說唱藝術形式。“喇嘛嘛尼”的演唱者多是以說唱為職業的男女游方僧尼或民間藝人,藏語稱為“羅欽巴”,意為“善說者”,或稱“喇嘛嘛尼哇”,意為“說唱喇嘛嘛尼者”。演唱時,藝人掛出繪有佛經故事的唐卡,用木棒指向畫中的人物,說唱畫中的故事,唱者與聽眾常為感人的故事而落淚。
“喇嘛嘛尼”演唱的時間、場合均十分靈活,無論是村頭、路邊、田間、屋旁,處處皆可演藝。演唱方式是單人清唱,不用樂器伴奏。流傳于西藏各地的喇嘛嘛尼演唱內容、形式、音樂都大同小異。音樂較平穩,旋律線條起伏不大;音域較窄,僅在五、六度音程幅度之內;節拍、節奏較自由,音樂似說似唱。演唱的內容除了佛經故事以外,還有藏戲故事、民間傳說等。
利川小曲的特點是說唱并重,旋律與方言聲調密切結合,詼諧風趣,主要曲牌有“掛板頭”“三腳凳”“龍抬頭”等,利川小曲有坐唱、站唱、走唱等不同表演形式。表演者有男有女,伴奏有擊節的梆鼓、木魚、跳板和二胡、三弦、笛、嗩吶等旋律樂器。這類說唱音樂的基本曲牌通過結構的展衍和調式調性的改變產生出擔負不同表現功能的各種“變體曲牌”。
(二)曲牌聯套體
曲牌聯套體是以能表達多種不同感情的曲牌連綴演唱的唱腔結構。根據作品內容和情節的需要,選擇不同的曲牌連綴起來唱,這種演唱形式可以追溯到北宋時期的唱賺,在宋、金、元時期發展到高峰,如宋代說唱“小說”“合生”、元代的清曲、明清小曲等,這種唱腔對其他說唱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國少數民族說唱采用此種結構形式的曲種較多,如“大本曲”“仲諧”“好來寶”“烏力格爾”“盤索里”“哈巴”“達斯坦”等。其中白族“大本曲”南腔流派的唱腔包括平板、黑凈、螃蟹調、老麻雀調等九板十八調。
白族的“大本曲”是較為典型的曲牌聯套體說唱音樂。元、明以來,大量內地移民進入洱海地區與當地白族融合,也帶來部分可供彈唱歌舞的伴奏樂器,其中三弦以其制作簡易、彈奏方便、長于配唱等優點成為最受白族群眾喜愛的民間彈撥樂器之一。白族地區民間藝術和佛教文化基礎深厚,歷來有許多神話傳說和佛教故事長期在民間傳誦。其中部分動人篇目,在精通白族傳統民歌的傳誦者中受到“山花體”民歌格律的影響,逐漸格律化并成為敘事性較強的可供三弦彈唱的長篇歌謠。另加上民間原有部分相同格式的小調、謠曲,經三弦彈唱者加工改編,與長篇歌謠相輔相成,聯曲成套,遂構成一種長于表現故事情節的說唱藝術,民間稱為“大本曲”。
表演白族“大本曲”,兩人即可,傳統的表演形式是二人分坐于高臺上的桌子兩旁,一人說唱,另一人彈三弦伴奏,并有手帕、折扇和醒木為道具。白族大本曲的唱腔音樂結構作為一種聯曲體類型,至20世紀50年代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曲調,民間流傳的“三腔,九板,十八調”之說,即大體反映了這一事實。
一般認為:“三腔”就是在音樂風格上有所區別的南腔、北腔和海東腔三種流派;“九板”指的是各腔用以演唱各種曲本的九首基本的傳統曲調,如“南腔”的“九板”,即平板、黑凈板、路路板、大哭板、邊板、小哭板、趕板、提水板、陰陽板等九首。“十八調”指的是南腔常用的十八首輔助性傳統小調,即新麻雀調、老麻雀調、螃蟹調、花譜調、家譜調、琵琶調、花子調、道情調、放羊調、陰陽調、祭奠調、上墳調、思鄉調、大會調、神調、仙家樂、玉河池、蜂采蜜等十八首。北腔的輔助性傳統小調也有十三首,通常稱為“十三腔”。其曲名和音調,與“十八調”中的曲目大體相同。為適應現實題材曲本的需要,此時期藝人也常將一些流行的白族民歌小調,引入輔助唱腔之列,從而擴大了唱腔的表現力和容量。“大本曲”的音樂曲式結構多樣,有的以上、下兩個樂句為基本單位,也有三、四、五或六個樂句的結構。此外還有因曲牌連綴的運用而形成多段體曲式結構,曲牌采用的速度有中速或稍快兩種。音樂上都各有特點,功能各異,他們通過藝人聯套組合來演唱故事傳說,表現各種不同人物的形象和情感,具有較強的敘事性、抒情性和音樂表現力。
土家族的“長陽南曲”唱腔經搶救,今存曲牌三十余首,分南腔、北腔兩類。長陽南曲有三種曲式結構,即混合聯曲體、南曲聯曲體和單曲體。混合聯曲體以南曲板腔為主,兼用其他曲牌,是長陽南曲的主要曲式結構,多用于演唱帶故事情節的段子。南曲板腔體中屬板腔的曲牌有南曲頭、垛子、等板和南曲尾,稱“當家曲牌”。
南曲板腔體曲牌特點:(1)南曲頭,唱詞句式為四四七七,第二、三、四句押韻,曲調委婉抒情,字少腔長;(2)垛子,一般只兩句,亦有兩句以上和散文式的,兩句垛子每句四字。兩句以上的垛子較多;(3)等板,又稱“數板”,上下句,是南曲之主調,它在各類曲目唱腔中運用最多,有南曲“當家曲牌”之稱,唱詞句式為兩個七字句,上下句各為四小節,曲調流暢優美,曲牌適應性強,亦可唱七字句,十字句,可表現喜怒哀樂之情;(4)南曲尾,唱詞以七十十為基本格式。
少數民族說唱音樂的單曲體和曲牌聯套只是一個大的唱腔分類,這種分類中還包括了多種不同形式的下一級別的類別結構。
三、少數民族說唱音樂與本土民間音樂關系
我國少數民族說唱音樂非常重要的特點,即曲調多來源于本民族、本地區的民歌、宗教音樂、器樂音樂歌舞音樂或者戲曲音樂等。
源于土家族地區的說唱音樂形式都與本地民歌小調關系密切,如“利川小曲”就源于利川南坪茶興的民間小調。利川小曲中的曲牌“龍抬頭”,就以當地流行歌謠《鬧元宵》為基礎稍加變化而成。“銀紐絲”的原型則是《春季調》,而“爬山調”“太平年”“賀新年”“游春調”等曲牌,其母體均為當地民歌小調。
土家族的“漁鼓”音樂結構主要為聯曲體,民歌小調的隨機插入,增強了音樂的適應性和表現力。其歌詞句式工整,多為上下對稱的七字句或十字句,一韻到底。
滿族的“子弟書”的音樂就來源于“巫歌”“俗曲”。廣西壯族的說唱形式中的“末倫”來源于“巫調”,是從民間巫事曲調中脫胎而來的民間說唱。據史書記載,清末桂西諸縣早已盛行求雨巫事活動,參加巫事活動,愛唱“末倫”的一般是窮人,而且大多數是婦女,尤其是喪偶吃齋不嫁的婦女。這種巫事到了明清,更為盛行。由于當時人們不但對巫事活動感興趣,而且還應用巫調來嘆身世,訴衷情,敘說彈唱故事。
壯族說唱“末倫”中“北路末倫”是在當地山歌曲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起落音都是“la、do、mi”三個音。旋律發展基本采用伸展或壓縮手法,依字行腔,唱詞押韻規律獨具一格,它與壯族民歌的腰腳韻不同的是,七言句的上句末字專與下句的第五個字押韻,從頭至尾,句句關聯,環環相扣。
“南路末倫”是在當地高腔山歌基礎上發展而成;唱詞為七字句,由二、三、四句等組成一小段,句數不限,不分章節,一串到底,押尾韻,常以“哎啰哎”襯詞為段落尾聲。
“下甲末倫”是來源于巫調的曲藝形式;“下甲末倫”曲調是“嘆”出來的,所以每段開頭都有一個感嘆句“哎……”,末尾總以“即呀咄”結束,情意真切動人。“下甲末倫”歌詞多為五字句,句數不限。
“上甲末倫”由當地間歌曲發展變化而來。由當地民間歌曲發展變化而來,其音調、節奏和音樂風格仍保留當地民歌的特色,旋律敘述性強,委婉抒情,唱詞有五字句、七字句,或五字七字結合運用。
彝族說唱音樂中的旋律采取以敘事歌為主,再從該支系的其他歌種中選擇一些特色鮮明、旋律優美、可塑性大的民歌改造為唱腔曲牌予以充實,并逐步將常用曲牌加以固定,所以說唱音樂與當地的民歌有著緊密的聯系,如“甲蘇”的《舍赫》《甲赫》《依嗚》《索赫》等;“阿細說唱”的《阿哦》《嘎斯阿哦》《拉里》《先基》《嘎斯先基》等。后隨曲目情感表現的需要,又在這些曲牌的基礎上發展,從而產生了新曲。有《阿哦新曲》《嘎斯新曲》《先基新曲》《阿里新曲》等。唱詞以五言為主,韻白間有七言。有的曲目唱詞長達數千行以上,也有許多短小的寓言故事和即興之作。
壯族的“唱師”音樂是在當地民間歌曲(壯歡)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地腔調不同,少的只用一個腔調,多的則達十余種,有通用曲調,也有專用曲調,如《盤古腔》《功曹腔》《莫一行游腔》等,曲調宛轉悠揚,如訴如說,簡單淳樸,都有濃厚的鄉土氣息,音域不寬,易記易唱,唱詞韻律優美,常用壯族民歌的賦、比、興手法,多為五言四句,押腰韻、腳韻和內韻。
侗族曲藝音樂是侗族民歌的繼承與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侗族曲藝各個曲種的主腔,均與流行地區民歌關系密切,有的甚至與當地某種民歌使用同一唱腔,有的則在當地某一民歌的基礎上加以發展,使之適應說唱藝術的特點。如“榕江彈唱”是在河歌(亦稱“河邊歌”“流水歌”)的基礎上,加上琵琶伴奏發展而成;“果吉柆唱”和“六洞彈唱”是在敘事大歌唆君的基礎上,加上果吉或琵琶伴奏發展而成,“果吉柆唱”的屬腔更是直接借用民歌唱腔。從侗族曲藝使用的伴奏樂器琵琶和果吉來看,也是該區中流行地區民歌的伴奏樂器;從唱詞的結構與押韻規律看,也與民歌唱詞一樣;從音樂結構調式來看,也與當地民歌的音樂結構和調式基本相同。總之,侗族曲藝是在“壘”“暖”“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音樂源于侗族民歌。與此同時,當侗族說唱音樂產生和發展之后,它自身又為其后侗戲的產生奠定了基礎。白族的戲曲——白劇,也是由白族的民歌“吹吹腔”和說唱音樂“大本曲”相融合而形成的。
這些民歌、歌舞、巫歌等民間音樂形式給說唱音樂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土壤與養料,在說唱音樂成熟與完善的過程中,反哺其藝術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民間音樂向更高的藝術形式發展提供了啟發與堅實的基礎。
結語:
本文從少數民族說唱音樂的表演形式、唱腔結構、與民間音樂關系三方面進行了分析與探討,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少數民族的說唱音樂具有雙重歸屬性。首先,少數民族說唱屬于我國說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漢族說唱音樂在音樂本體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其次,由于不同的少數民族說唱音樂分屬不同的文化母體,而母體文化中固有的民族文化記憶和音樂特征,又促成不同民族說唱音樂藝術的不同發展狀態和不同特色風格與韻味,繼而形成各個少數民族說唱音樂文化的個性特征。所以筆者以為,在描述、分析、解析少數民族說唱音樂的特征,將其置入到本土文化中,是對其進行觀察、詮釋重要的手段與途徑。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