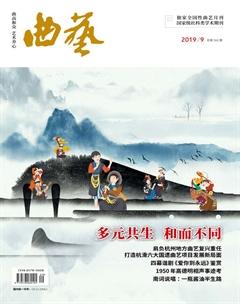歷久彌新竹板情
李宗義
我今年74歲了,不免有了些“神龜雖壽,猶有盡時”的念頭。雖然弟子們常用“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老話安慰我,可對著鏡子看看自己斑白的兩鬢,再想想走長路還氣喘的身體,就覺著稀罕可能沒有,再過兩年可能就真的“稀軟”了。也許人老了就愛琢磨些過去的事情,每每環顧四壁,就覺得家中最珍貴的物件就是快板了。而恩師王鳳山先生留給我的那一副,已經陪伴我走過60多年歲月,更是“貴中之貴”。
一、巧拜師樂生活
我1946年生在天津市一戶普通的工人家庭。要循著當時的家庭軌跡來說,我本來和藝術應該是沒什么交集的。可說來也巧,13歲那年,天津市曲藝團去我就讀的小學招收學員,當時還有些摸不著頭腦的我居然被學校推薦去應試,并最終和另外兩名同學一起入選,就此開啟了漫長的快板生涯。
當時天津市曲藝團少年訓練隊有22名學員,分別學習不同的曲種,都由著名演員擔任主教,我的授業恩師就是王鳳山先生。
在跟著師父學習的日子里,我對“師徒如父子”這句話有了很深的體會,師父的家成了我的第二個家。師父經常說,“吃、住都不用客氣”,聽起來輕松,實際上,20世紀60年代的國民經濟正面臨困難,一切物品都要憑票按人頭定量供應,多一張嘴就憑空多一份負擔。細糧更是難得,師父王鳳山、師娘任鴻智一直將為數不多的細糧分給我們這一幫正在長身體的半大小子。有人覺得面條、大餅在現在實在是太常見了,都吃膩了。那是他們沒經歷過細糧無比珍貴的日子,自然也不會明白我們這輩人對糧食的珍視。那個時候師娘總是親自下廚,她的廚藝和師父的藝術水平一樣精湛,做出的面條、大餅分外香。那種香味沉淀到了我的胃里和心里,留在我的記憶中和血液里,勝過所有的山珍海味。
天津的冬天可能不如東北的“凍人”,但時令不好的時候,一樣“風雪來得驟”,冷得人難受。師娘怕我們凍著,總是提前給我們趕制冬衣。她的針線靈活巧妙,做的棉衣、棉褲又合身又暖和。
而就在師父寬嚴相濟的督導和師娘無微不至的照顧下,我們這些曲藝雛鳥也逐漸成長。
二、勤學藝穩做人
在師父家住時,每天清早我都跟著師父到河邊練習基本功。師父功底深厚,但做基本練習的時候從來都是一絲不茍。在我印象里,除不可抗拒的天氣因素外,師父無一日不早起。“板不離手,詞不離口,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師父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但那時候畢竟還年輕,老是來回操練基本功,我也有不理解甚至不耐煩的時候。
快板書《繞口令》是最能體現王派特點的段子,也是師父用來啟蒙我的段子。我是天津人,有些方言上的障礙,但師父教我的時候從沒有絲毫的不耐煩。用了半年,我終于學會了《繞口令》,可師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還是讓我反復錘煉這個段子。“一個如此簡單的段子,幾天就會了,為啥不快點學大節目、新節目呢?”這是當時憋在心里疑問,但沒敢講出來。
師父大概是看出了我心里有事,所以每逢出差都盡量帶著我。那時候天津市曲藝團的演出任務是很多的,師父也很忙,但在演出間隙、行旅途中、茶余飯后,師父得空就給我講表演的技巧和做人的道理。師父一直認為,要學藝就要能沉下來,心不能“飄”。這心一旦開始“飄”了,根基扎不好,還容易迷失自己。
對這些話我一開始是半懂不懂地記了個囫圇圓。后來隨著表演經驗的豐富,對師父的這些話我才慢慢有了更立體的認識,因之也對師父有了更重的敬意。“沉重的字,丹田的勁,瀟灑的身段,巧妙的氣”,這是我在悉心學習后對師父藝術特點的總結,也是我表演的核心。
但師父教的是活生生的徒弟而不是只會照貓畫虎的木頭人,所以他常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長處,要根據自身情況來應對千變萬化的舞臺場景,學我但一定不要像我,像我就失敗了。”師父還常常教育我們,一個人會的再多也有限,“不要只學習我的東西,也多學學他人的藝術,李潤杰先生、高鳳山先生的活也要多聽、多懂,快板本沒有流派,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藝術而已。”
三、聽黨話跟黨走
師父愛黨愛國、愛藝術、愛家人、愛學生。他經常對我說,是黨讓他這樣一個舊社會的苦命人成為新社會的主人,跟著黨走才能有幸福。“‘人字兩筆,很好寫卻不好做,做藝先做人,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要跟著黨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王鳳山,我的一切是黨給的,所以我也要將我的一切獻給黨,獻給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 師父的這些話,我牢記到今天。也正是師父的教導,讓我對黨有了深厚的感情。在1989年,我正式入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黨員。
現在有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就罵娘,總覺得天生我材但沒用千金不來沒法兒散。這種情況下咱們干曲藝的不能隨波逐流,也不能站在干岸上沒動靜,咱們得“說書唱戲勸人方”,實實在在地用快板闡釋黨的政策,宣傳黨的思想!這是我一個老黨員的覺悟,也是師父的希望。
1963年,我正式出師,被分配到吉林省吉林市曲藝團工作。我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師父和師娘。臨行前,我帶上了師父為我做的竹板;師娘給竹子刮的青,這副板做得十分精致,師父還用海鳳師爺的綁板方式栓了個漂亮的線穗兒。就是這副竹板,伴隨著我學藝、演出、入黨、走進新時代。看著她,就像師父看著我一樣!
60年的光陰轉瞬即逝,這副竹板我一直珍藏著。演出是不會再用了,當徒弟們來到家中的時候,我總要拿出來給他們展示。雖然師父王鳳山先生已經離開我20余年了。看到這副竹板,師父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學藝的往事猶如一部歷久彌新的影片又開始在我腦海里回放。年過古稀的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像王鳳山先生那樣,為快板藝術再盡一份力量,也許這首小詩更能表達我的感慨:
先師授業舊話長,
青竹已舊恩難忘。
年過古稀跟黨走,
守業創新凱歌揚。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