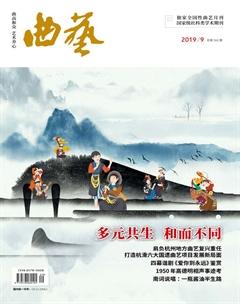上帝只賣一美元
醫院里跑出個孩子叫約翰,
手里拿著一美元。
見商店就進去,
忙問道:“你們這賣不賣上帝?”
老板娘把臉猛一板,
毫不留情往外攆。
(白)“滾,搗什么亂!”
“俺沒搗亂。”
“還沒搗亂,自從三皇開天地,
見過哪里賣上帝?
你以為上帝是顆娃娃菜,
推著車子沿街賣。
你以為上帝是5G電子狗,
你一遙控跟你走。
告訴你別犯渾,
上帝他不是玩意不是人,
他是神,阿門!”
小約翰一點不記恨,
沿街商店挨個問。
他走進第十九家小商店,
約翰累得直冒汗。
“請問老板,俺有錢是硬幣,
你這賣不賣上帝?”
這老板六十歲開外,
態度顯得很和藹。
一聽說孩子買上帝,
老板覺得很神秘。
遂問道:“孩子請你告訴我,
你買上帝干什么?”
老人一問不要緊,
小約翰淚如涌泉往下滾。
“俺叔叔,從腳手架上摔在地,
現在就剩一口氣……”
(白)“孩子別哭慢點說。”
卻原來約翰從小父母喪,
叔叔把他來撫養。
叔叔生命垂危送醫院,
大夫們馬上就診斷。
診斷完,大夫們搖頭又嘆氣,
他們說:“看來只有求上帝……”
小約翰一聽心里記,
才沿街商店買上帝。
老人聽罷約翰一席話,
感動得淚珠腮邊掛。
遂問道:“孩子你總共帶了多少錢?”
“俺這里只有一美元。”
老人說:“孩子,要說咱爺倆真有緣,
我這里有,上帝只賣一美元。”
老人家接過約翰一元是硬幣,
把一瓶“上帝”牌飲料遞過去。
“這瓶‘上帝牌飲料一喝掉,
叔叔的病情就會好。”
小約翰一下樂開懷,
進醫院就喊:“叔叔,我把上帝買回來!”
第二天,醫院里邊真熱鬧,
來了專家真不少。
這些醫療專家來會診,
叔叔的病情摸得準。
又動手術又吃藥,
藥到病除見成效。
臨出院,叔叔一看醫療賬單吃一驚:
“啊!這筆錢一輩子俺也還不清……”
醫院領導把話談:
“放心吧,醫療賬單不用還。”
(白)“啊!那為什么?”
領導說:“有位富甕叫邦迪,
家產超過幾個億。
退休后回到鎮上來閑住,
順便開了個小商鋪。
那一天約翰買上帝,
那老頭就是富翁叫邦迪。
小約翰哭訴淚漣漣,
一瓶‘上帝收了他一美元。
第二天邦迪請來醫學專家真不少,
把你的傷病給治好。
醫療費也是邦迪付的錢,
讓你們高高興興回家園。”
(白)“啊!真的?”
“真的!”
“沒錯?”
“沒錯!”
吔吔吔!哽哽哽!嘎嘎嘎!
嘭嘭嘭!嚓嚓嚓!
當滴格當滴格當滴格當!
嗚啪嗚啪嗚嗚啪!
嘻嘻嘻!哈哈哈!
餡餅落到窮人家!
咕咔咕咔咕咕咔!
叔侄二人沒過夜,
找邦迪當面去道謝。
誰知道邦迪去了北京,
臨走留下信一封。
信上說:年輕人健康出了院,
要感謝你侄子小約翰。
他拿著一美元是硬幣,
沿街給你買上帝。
他的愛心感動了天感動了地,
最后感動的是上帝。
上帝教咱有愛心,
全仗你侄子一片孝敬心。
故事到此并未完,
還得說說小約翰。
約翰人小勁頭足,
每天拼命在讀書。
勤奮學習十來年,
一舉考取醫學院。
在醫學領域展翅飛,
創新實踐有作為。
為減少建筑工人疼痛少流血,
一舉發明了創可貼。
為宣揚老板恩德和名譽,
創可貼起名叫邦迪。
這段快書講完畢,
為把愛心來傳遞。
賞析:
“上帝只賣一美元”是個挺有意思的題目,讓人一看之下就能不由自主地產生好奇:上帝也能賣?論個還是論斤?從這一點來說,李鴻民先生的這個作品開篇即先聲奪人,出手不凡。
文章也好,作品也罷,按照一般創作規律,大抵是要遵循“鳳頭、豬肚、豹尾”的流程——開頭燦爛華美,先聲奪人;中間內容充實,觀之有物;結尾呼應全篇,意思清新。但知者易而行者難,也有作者在鳳頭之后高開低走,言之乏物,最后把作品弄成鳳頭雞肚蛇尾巴的別扭樣子。而本作則在題目先聲奪人后,沒有循常例鋪展故事,而是繼續“劍走偏鋒”,刻畫出一個逢人就要“買上帝”的“奇怪”小孩。大人則毫無耐心,也不想細究這小孩究竟想干什么,只是用成人的身份“居高臨下”教育孩子,“上帝不是娃娃菜,也不是5G電子狗”,沒法子被“推著車子沿街賣”,被“一遙控跟你走”,末了還特別加一句,“告訴你別犯渾,上帝他不是玩意不是人,他是神,阿門!”這樣就通過有趣的語言,構建“無知”兒童和“懂事”大人之間的矛盾,讓人倍感有趣時又多了往下看的好奇心——“這‘熊孩子想干嘛呀?”
直到“熊孩子”碰到一個愿意傾聽他愿望的老人,受眾方才恍然大悟,孩子不熊,他的行為只是對叔叔“從腳手架上摔在地”后醫生可能一句戲言的直接反應,盡管有些幼稚,但充分表現出了孩子應該有的純真與善良,這打動了老人,所以才有了后來老人的幫助與孩子的感恩和醫學成就,進而展現出作者創作的最終目的,“為把愛心來傳遞”,如此結尾沒有斧鑿之痕跡,平滑爽利,觀之回甘無窮。
這個作品實際還展現出一種可能性,即曲藝作品與童謠兒歌的文學關聯和現實關聯。比如從童謠的歷史表現形式來說,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曲藝的原始展現形式,比如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民間文學》就把兒歌定義為“是在兒童中間長期流傳、廣泛傳唱的一種韻話體式的口頭短歌”,“短”“廣泛”和有一定的韻律,這在極大程度上也是一些曲藝形式的特點,如去年第八屆全國少兒曲藝展演上的蘇北琴書《小木盆》,說是曲藝節目自然可以,說是童謠也甚是貼合。從這一點來說,充分挖掘曲藝與童謠兒歌之間的關聯,對于曲藝受眾的拓展特別是在少年兒童中的拓展,是大有裨益的。李鴻民先生這個作品,無疑給曲藝工作者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稍有幾點建議,謹供李鴻民先生參考。愛能讓人有同情心,但科學能給人助人的能力。雖然作品中也說明了孩子勤學的作用,但落筆點還是在“愛心”上,建議李鴻民先生可以稍微強調下兩者的關系,讓作品的合理性更強些;再者,作品中某些字句可能還要再斟酌下,比如“上帝”“恩德”等西方化或者太過感情化的詞語,還是稍微處理一下為宜。
(賞析:本刊編輯部)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