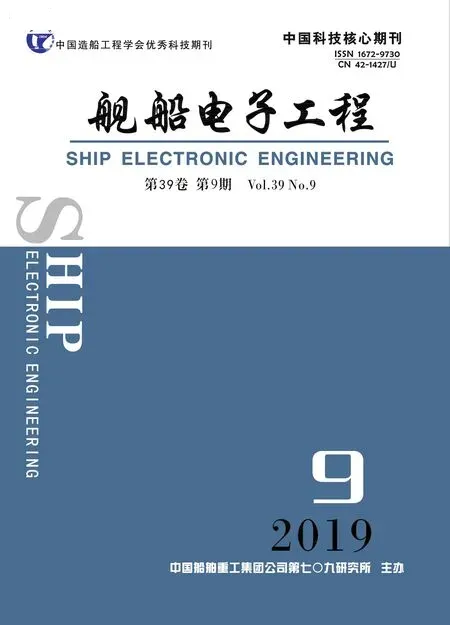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研究*
張繼春 李興順 王 會
(1.陸軍炮兵防空兵學院指揮信息系統教研室 合肥 230031)(2.陸軍炮兵防空兵學院研究生管理大隊 合肥 230031)
1 引言
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考核,目的在于通過全面系統的在役考核,客觀評估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驗證其能否滿足數字化條件下新的作戰要求,為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科學發展提供技術依據。評估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構建一個科學、完整的指標體系是準確客觀評估指揮控制能力的重要前提與保障[1]。
2 指標體系構建原則
針對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作戰效能高、信息化程度高以及具有作戰和保障雙重功能等特性,結合一般指標體系構建原則,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應遵循以下原則[2~5]。
2.1 一致性原則
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是根據評估目標分解得到的,每一條指標都應反映出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的某項特征,無論評估指標怎么分解,其子指標的選定總是圍繞目標的某一方面展開的,若干個子指標共同構成總的評估目標,即指標體系的建立與評估目標具有一致性。
2.2 完整性原則
指標體系的完整性是確保評估結果準確性的根本保證,在構建評估指標體系時,要充分考慮影響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的多種因素,從中抓住主要因素,即能反映評估的直接效果,又能反映評估的間接效果,使指標盡可能地涵蓋評估的全部內容。
2.3 客觀性原則
評估指標的確定應避免個人偏好影響,指標含義要明確,參與指標確定的人員要具有權威性、廣泛性和代表性,必要時還需要廣泛征集部隊裝備操作人員的意見,確保所選取的指標能客觀反映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的真實情況。
2.4 獨立性原則
評估指標的獨立性,要求所選的評估指標即能完整地反映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所覆蓋的范圍,又能確保每一個指標只反映評估目標的某一方面能力水平,各指標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不具有交叉性,這種獨立性不僅反映在同一指標內部,也反映在相鄰指標之間。
2.5 層次性原則
選擇的指標關系明確,相互之間具有層次結構,不能只是單純地羅列評估指標,這就要求在選取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評估指標時要合理地構建層次結構關系,既能夠很好地反映指標之間的邏輯關系,也便于應用綜合評估方法對指標數據進行集結。
2.6 可測性原則
可測性是指標的定量表示,即指標能夠通過測試儀器、試驗統計或數學公式等方法獲得。指標本身便于實際操作使用,能夠進行定量分析,度量的含義明確清晰,具備很強的操作性。
3 指標體系構建過程
指標體系構建是一個“具體-抽象-具體”的邏輯思維過程,是逐步深化、逐步完善、逐步系統化的迭代過程,構建過程如圖1所示。

圖1 指標體系的構建過程
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構建過程主要有以下四步:
1)明確評估的約束條件,即評估對象是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評估目標是所建立的指標體系能滿足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評估的需要,基本原則是上述的六個原則,指標體系構建采取基于“能力需求分析”思想[6],考核關注的要點分析主要依據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關注的主要內容。
2)進行指標分解。指標的分解以深入分析約束條件為基礎,充分參考借鑒專家意見,利用層次分析的思想從總目標開始,由上至下進行層層分解,得到初始指標集[7~8]。分解的指標要能夠覆蓋其準則的全部特性,并且每個評估指標能夠代表其準則不同的屬性。
3)進行初始指標集的篩選與優化。初步建立的指標體系還不能完全滿足評估要求,在應用于評估對象之前,還需對其進行篩選、調整和優化,并在評估過程中不斷完善和改進。
(1)重要度判斷。重要度判斷主要判斷評估指標是否具有代表性,能否真正反映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問題的本質。在初步構建的指標體系中難免存在一些重要程度不高的指標,應當對評估指標進行篩選,以分清主次,取舍恰當。指標權重是同層指標之間相對重要度的綜合度量,根據層次分析法原理,人們對不同事物在相同屬性上的差別分辨能力在5-9級之間,在某一準則下的指標數量不宜超過9個,最不重要與最重要指標的權重比值為0.11,通常取舍權重為0.1較為合適,當某一指標的權重小于0.1時,說明該指標影響較小,可以將其舍棄。
(2)完整性檢驗。完整性檢驗主要檢驗評估指標體系是否全面、完整地反映了評價目的和任務。一般通過定性分析進行判斷,采用過程分析的方法,依據相關領域專家的經驗進行確定。
(3)有效性檢驗。在構建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評估指標體系時,由于專家知識的完備程度不同,建立的指標體系可能存在差異,如果這種差異較大時,就說明該指標體系不能滿足客觀反映評估對象的要求,所以必須對指標體系本身進行有效性檢驗。
設根據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框架建立的某層指標表示為F={f1,f2,…,fn},參加評估的專家數為S,專家Sj對評估對象的評分集為Xj={x1j,x2j,…,xnj},定義指標fi的效度系數βi如下:

式中:M為指標fi的最大值為fi的平
從統計學含義上講,效度系數提供了衡量對某一指標評估時產生認識偏差的程度。效度系數的絕對值越小,說明各專家在采用該指標評估時,對該問題的認識越趨于一致,該評估指標體系的有效性就越高;反之則越低。
(4)體系結構優化。指標體系結構優化主要指從整個指標體系的角度進行完備性分析,主要分析評價目標的分解是否有遺漏,有無出現目標交叉而導致結構混亂的情況。重點檢查平行子目標之間是否存在相互交叉、重疊情況,若出現此類情況,須將交叉、重疊部分的子目標合并成一個共同的子目標,或將其進行分離單獨成為一個子目標。
4)判斷末級指標的細化和量化程度,決定是否再對指標進行分解。末級指標的細化程度需要綜合專家、部隊等方面的意見,并保證所有末級指標的細化程度相近。末級指標量化程度要求所有末級指標都具有可測性,并能保證數據采集的可操作性。若末級指標細化和量化程度沒有達到要求,則繼續指標的分解和優化,直到滿足要求為止。如果滿足要求則停止分解,從而獲得最終的指標體系。
4 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的特點,基于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構建思想和原則,構建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總體框架如圖2所示。

圖2 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框架
4.1 系統構建能力
系統構建能力的下一級指標有3個:系統開通能力、系統撤收能力和系統重組能力,如圖3所示。
系統開通能力是指數字化部隊指控系統將預案數據進行分發、加注和開通調試的能力。預案數據分發能力由預案分發時效性指標構成,參數加注能力由參數加注時效性指標構成,開通調試能力由指揮所開通調試時效性、各群隊開通調試時效性和指揮所到各群隊開通時效性3個指標構成。系統撤收能力是指撤收通信裝備和指控裝備的能力,由撤收通信裝備和指控裝備時效性2個指標構成。系統重組能力是指系統指揮節點遭敵破壞后和指揮所重新編成編組調整后的重組能力。系統指揮節點遭敵破壞后的重組能力由群隊指揮節點重組能力和下級指揮節點重組能力2個指標構成,指揮所重新編成編組調整后的重組能力由編成編組調整時效性、網絡規劃調整時效性、預案數據分發時效性、參數加注時效性和開通調試時效性等5個指標構成[9]。

圖3 系統構建能力指標體系框架
4.2 輔助決策能力
輔助決策的下一級指標有3個:情況研判能力、戰術計算能力和方案生成能力,如圖4所示。

圖4 輔助決策能力指標體系框架
情況研判能力是指對敵情、我情和戰場環境進行分析判斷的能力。敵情研判能力由敵情態勢研判能力和敵情基礎數據查詢能力2個指標構成,我情研判能力由我情基礎數據查詢能力、人裝物彈統計能力和作戰任務獲取能力3個指標構成,戰場環境研判能力由地形地貌分析能力、電磁環境分析能力、核生化環境分析能力、氣象水文分析能力和人文社會分析能力5個指標構成。戰術計算能力是指完成作戰計算任務的能力。通用計算能力由通用計算的完備性、準確性和便捷性3個指標構成,聯合作戰計算能力由聯合作戰計算的完備性、準確性和便捷性3個指標構成,專業計算能力由專業計算的完備性、準確性和便捷性3個指標構成。方案生成能力包括方案擬制和優選能力,方案擬制能力由方案擬制自動化程度、各模板內容要素齊全性、方案擬制智能化程度和擬制時效性4個指標構成,方案優選能力由方案評估能力和方案優化能力2個指標構成[10~11]。
4.3 精確控制能力
精確控制能力的下級指標有2個:控制信息流轉能力和任務監控能力,如圖5所示。

圖5 精確控制能力指標體系框架
精確控制能力是數字化部隊依托指控系統對所屬部隊進行精確指揮、控制和協調的能力,是將作戰決心和計劃付諸實踐的關鍵,包括控制信息流轉能力和任務監控能力。控制信息流轉能力是指揮控制系統在指揮所內部、對下級指揮所、越級、對上級指揮響應的控制信息流轉能力,四方面能力均由警報接收、簡令接收、文電接收和時統對時接收成功率4個指標構成。任務監控能力由定位導航能力和行動監控能力組成,定位導航能力由定位精度、導航線下方的一致性和糾偏響應時效性3個指標構成,行動監控能力由行動監控方式種類和監控自動化程度2個指標構成[12]。
5 結語
本文構建的數字化部隊裝備指揮控制能力指標體系是基于我軍最新提出的在役考核具體要求,在遵行指標體系構建原則的基礎上,應用層次分析方法建立起來的。該指標體系的建立,為實現數字化部隊裝備指揮控制能力評估量化、科學化和可操作化奠定了評估基礎。隨著我軍數字化部隊裝備體系的不斷發展進步,還將針對本指標體系中不合理之處進行補充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