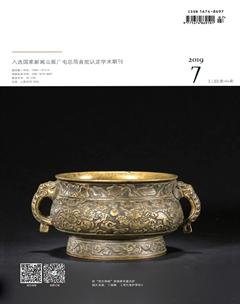北宋朝散大夫沈公墓志銘考釋
劉昱楓
摘 要:沈邈,北宋仁宗時期名臣,《宋史》有傳,僅百余字,但沈邈墓志志文有1200余字。墓志的出土,可以補充《宋史》等記載。墓志中對于志主的生卒年、歸葬地、世系、婚姻、仕宦經歷等信息記載詳實,可以補史之缺。墓志記載其為吳興沈氏的一支,亦可以豐富對其家族研究的資料。
關鍵詞:沈邈;墓志;仕宦
沈邈墓志在洛陽伊川出土,志蓋上書“宋故天章閣待制沈公墓志銘”。志文32行,滿行39字,隸書。志石長、寬均為83厘米。《宋代墓志輯釋》收錄其拓片及錄文[1]237-238。《宋史·沈邈傳》才百余字,但沈邈墓志有1200余字,墓志中對志主的生卒年、歸葬地、世系、婚姻、仕宦等信息記載詳實,可以補史之缺。
1 沈邈家族世系
沈邈,字子山,姓沈氏。“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春秋魯成公八年,為晉所滅。”[2]3146志載沈邈為“出周冉季,文王之子戎,為漢光祿勛,居吳興”。《元和姓纂》載:“漢光祿勛海昏侯沈戎,后居會稽烏程。吳興分烏程為吳郡。”[3]1129起源于東漢沈氏,后世代居于吳興。墓志記載沈氏一族在晉梁之時代有名人。在唐時,沈既濟、沈傳師父子以文學為后世所稱贊。既濟,“博通群籍,史筆尤工”[4]4037,在建中初年為宰相楊炎推薦,其才能卓著,“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4]4037,后撰《建中實錄》十卷。傳師,《舊唐書》有傳,“傳師,擢進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書郎……歷司勛兵部郎中,遷中書舍人”[4]4037。墓志記載沈傳師“即公十代祖也”。“朝宗生既濟、克濟。既濟,……生傳師、宏師、述師。傳師生樞、詢……”[3]1137故根據墓志以及《元和姓纂》的記載,沈邈先祖最早可以追溯至朝宗,為沈邈十二代祖。傳師之后,沈氏后人并未有大功勛者,故后代事跡史書未載。志載唐代后期季岳為兵部員外郎,從昭宗至洛陽,不肯隨眾入汴,后為李璟用為中大夫,出使兩浙。錢镠妻以子,生瞻,為錢氏步兵都尉,公之高祖也。沈言,為錢氏行軍參謀,公之曾祖也。沈言生沈師古,亦仕于錢氏。后隨錢氏歸宋,為大理寺丞,贈兵部尚書,即為沈邈祖父。生文□,初仕錢氏,后歸朝,為尚書虞部員外郎,贈吏部尚書,為沈邈之父。墓志記載,“曾祖妣錢氏、祖妣錢氏、妣錢氏,封仙源縣太君”,而沈邈妻亦為錢氏。沈氏四代妻皆為錢氏,故沈氏與吳越錢氏一族關系密切。正史中并無對其家世的詳細記載,《宋史·沈邈傳》僅記載沈邈為“信州弋陽人”[5]10030,即今江西上饒人,并無對其族人等記載,故墓志的出土可以豐富對沈邈家世及家庭成員的記載。沈邈的子女較多,有子四人,分別為群玉、嘉玉、伯玉、夷玉;女三人,長女出家為尼,次女適進士鄧子真,幼女適殿中丞吳安矩。墓志并未記載其四子的婚姻關系,為對沈邈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空白,有待更多的史料補充。
2 沈邈生平及仕宦經歷
墓志記載沈邈逝世時間為“慶歷七年(1047)也”,享年46歲,故可推斷沈邈出生約在真宗咸平四年(1001),歷經真宗、仁宗兩朝。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初九日,遷葬河南府洛陽縣鳳臺鄉陶牙里邙山之陽。
《宋史·沈邈傳》僅記載沈邈“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5]10030,而對于沈邈進士及第的時間則未記載。但其墓志記載沈邈“二十六登進士甲科”,可推斷其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舉進士第。《宋登科記考》中記載“寶元元年(1038)(一作慶歷間)登進士第”[6]166,故根據墓志記載則明確了沈邈進士及第的具體時間,補充正史記載之缺漏。吳建偉在《〈宋登科記考〉拾補——以碑刻文獻為中心》一文中對沈邈“及進士第的時間”[7]16也有探討。
正史中對于沈邈的仕宦記載較為粗略,結合墓志以及地方志的記載,可以詳細地梳理出沈邈的仕宦經歷。沈邈于天圣五年(1027)任大理評事,后遷丞,改殿中丞、太常博士。入尚書,為屯田都官員外郎。召拜侍御史,改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明道初年(1032—1033),改刑部郎中,知衢州江山、福州侯官縣,通判廣州、潭州。慶歷初年(1041),又拜侍御史,知雜事,賜緋衣銀魚,待制天章閣。慶歷三年(1043),沈邈任京東轉運使。五月戊寅,帝下詔令“轉運使皆領按察使”[8]194,十月丙午,命“張昷之、王素、沈邈皆領按察使”[8]194。慶歷四年(1044),逢保州兵亂,公知澶州,視事三日,授河北都轉運使。慶歷五年(1045)十一月自陜西都漕知延州。志載“賜三品服,充鄜延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積階至朝散大夫、上輕車都尉、開國吳興縣男、食邑三百戶,特贈諫議大夫。后因為沈邈長子沈群玉登朝為官,贈沈邈工部侍郎。沈邈英年早逝,仕宦僅二十余年,但卻任職多地,政績頗豐,為當地百姓所稱贊,仁宗也多次下詔褒獎,并賜金帶、開花鞔鞍轡馬、金銀花器等。
在沈邈的仕宦生涯中,為言官時敢于直言,任職地方時修邊備、繕營田、治水利,為政一方,愛民如子。較為重要的事件則有三件:其一是為人臣無功不應進官。慶歷三年(1043)三月辛卯,呂夷簡罷相,諸多輔臣皆進官,但當時還是侍御史的沈邈卻上奏仁宗,言:“爵祿……非功而受則為濫。……未聞廟堂之謀……而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9]3359這體現出沈邈不慕名利、一心為國的個人性格特點,仁宗也日益器重。其二便是夏竦罷樞密使一事。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三月,夏竦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時沈邈為侍御史,上章表明不可任用夏竦為樞密使。沈邈上奏仁宗,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內濟險譎。……人主之權去矣。”[9]3365仁宗聽從,罷竦樞密使。時夏竦權重,沈邈作為言官敢于直言,體現了他無謂權臣、正直忠義、膽氣過人的特點。其三便是改革紅鹽之法。福州“舊貢紅鹽、密煎二種”[10]257,但當時紅鹽的制作之法大多以“以鹽梅鹵,浸佛桑花為紅漿……暴干”[10]257,制作之法并不簡單,故沈邈在知福州時,便以道途遙遠、運輸不便令當地“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曬者”[10]257,還令漳、泉二郡亦均貢白鹽,體現了沈邈關心民生疾苦的愛民之心。
3 沈邈文學成就以及交游
沈邈不僅政績卓著,還有極高的文學成就,但后世留存的詩文不多,多數早已散佚,《全宋詞》中僅記載兩首,詞名均為《剔銀燈》。馮金伯《詞苑萃編》中記載張溫卿本是宿州營伎,名“張玉姐,字溫卿”[11]4024,在當地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11]4024,沈邈最為鐘愛,故在罷官次南京時,仍見之不忘,為其所作詞二首,詞中“須信道、情多是病”[11]4024等皆體現出沈邈對其思念之意。沈邈雖才能卓著,但也為情所累,后世多有貶低。《宋史》中稱沈邈雖“亦有美才,致位通顯”[5]10030,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5]10030,故此也影響了后世對其的評價。
沈邈交友廣泛,尤與歐陽修關系較為親密,二人情誼頗深,歐陽修也曾為沈邈作詩兩首,名為《寄子山待制二絕》[12]716,為慶歷五年(1045)所作。時歐陽修任河北轉運使,權知成德軍。《長編》記載“沈邈以慶歷四年九月為都漕”[12]717,此詩作于歐陽修“離開真定前夕”[12]717,當時“沈邈尚未赴任”[12]717。除歐陽修外,蔡襄也贈沈邈詩一首。沈邈文采風流,當時許多文人都愿與其相交彼此贈詩,這也為后人研究宋代文人雅士的交游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4 結語
墓志中對于志主的生卒年、歸葬地、世系、婚姻等信息記載詳細,而且對于沈邈的仕宦等也記載詳實,可以補充正史。吳興沈氏,興起于東漢,歷經南北朝而不衰,唐宋時亦有名人輩出。沈邈作為吳興望族沈氏的一支,對其志文的考釋,可以豐富對吳興沈氏的研究,填補學術界的空白。沈邈曾祖、祖父、父以及自身,四代皆娶吳越錢氏妻,也有利于豐富對吳越錢氏姻親的研究。
參考文獻
[1]郭茂育.宋代墓志輯釋[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2](北宋)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唐)林寶.元和姓纂[M].北京:中華書局,1994.
[4](后晉)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5](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
[6]傅璇琮,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7]吳建偉.《宋登科記考》拾補——以碑刻文獻為中心[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6):16-21.
[8]燕永成.皇宋十朝綱要校正[M].北京:中華書局,2013.
[9](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0]伊永文.東京夢華錄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7.
[11]葛渭君.詞話叢編補編[M].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12]劉德清.歐陽修詩編年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