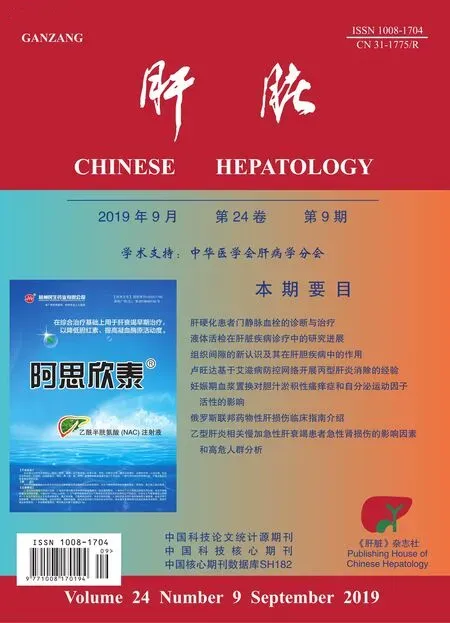13C-美沙西丁呼氣試驗在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中的臨床應用
張學秀 姚建寧 張延禎 李艷樂 王春峰 張連峰
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是一種隱匿的進行性膽汁淤積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發生于中年女性,特征性病理改變是非化膿性破壞性膽管炎,最終引起肝硬化。不同患者的自然病程差異極大,部分患者無癥狀時間可長達20年,而部分患者可早期出現黃疸,并迅速發展為肝硬化、肝衰竭等[1-2]:這些與肝臟儲備功能密切相關。目前判斷肝臟儲備功能最常用的指標是白蛋白和凝血酶原時間,但在早期PBC患者,這兩項指標通常正常,而堿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高低與膽管破壞程度無明顯相關性;判斷PBC嚴重程度的金標準是肝臟活檢,但因具有創傷性,影響其在臨床動態監測的應用。
13C-美沙西丁呼氣試驗(13C-methacetin breath test,13C-MBT)是近來應用于臨床進行評價肝臟儲備功能的一種新方法。因13C-MBT與Child-Pugh評分有良好一致性,已被用于評價病毒或者酒精性肝硬化的嚴重程度[3],但關于13C-MBT在慢性膽汁淤積性疾病中的應用較少報道。本研究擬探討13C-MBT在PBC患者肝臟功能和臨床病理分期中的評估作用。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收集2010年8月至2015年9月在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確診的PBC患者63例,其中男性4例,女性59例,年齡(52.2±13.6)歲。PBC診斷標準:ALP升高大于1.5倍,抗線粒體抗體陽性,肝臟病理符合PBC病理特征。健康對照組22例,男性1例,女性21例,平均年齡(49.3±14.2)歲。PBC組與對照組在性別年齡上無統計學差異。排除標準:(1)肝外原因引起的膽汁淤積;(2)有病毒或酒精原因引起的慢性肝病;(3)嚴重的心肺疾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4)服用可影響CYP1A2酶活性的藥物;(5)腫瘤;(6)伴有發熱或甲狀腺疾病;(7)任何可以導致吸收不良的胃腸道疾患。所有研究對象均簽署知情同意書,且本研究通過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二、方法
(一)臨床資料 收集所有患者的臨床檢查數據,包括肝、腎功能、凝血全套等,腹部B超檢查,患者病史情況等;并計算肝硬化患者的Child-Pugh評分。
(二)病理資料 PBC患者的肝臟病理評分參考Ludwig’s標準(Ludwig’s stage,LSS):Ⅰ期為膽管炎期;Ⅱ期為門靜脈周圍炎伴膽管增生;Ⅲ期可見纖維間隔和橋接壞死形成;Ⅳ期為肝硬化期[4]。
(三)13C- MBT13C-美沙西丁和IRIS紅外線同位素能譜分析儀由德國WAGNER公司生產。晨起空腹收集呼出氣體100 mL作為0時氣體;服用溶有50 mg13C-美沙西丁的溫水150 mL。口服后開始計時,于安靜狀態下分別收集10、20、30、40、50、60、80、100和120 min時間點呼出氣體各100 mL。通過IRIS檢測,繪制出豐度(delta over baseline,DOB)曲線和代謝速率(metabolisation velocity,MV)曲線,并記錄3個主要呼氣參數,即前40 min代謝速率峰值與正常值的比值(MVmax40)、40 min13CO2累積呼出豐度與正常值的比值(CUM40)、前120 min13CO2累積呼出豐度與正常值的比值(CUMl20)。MVmax40和CUM40代表肝臟儲備功能,CUM120代表肝臟代償能力,以(MVmax40+CUM40)/2的值作為量化值將肝功能進行量化分級。參照如下標準判斷13C-MBT分級:≥1.20為肝功能誘導狀態;0.8~1.2為肝功能正常;0.5~0.8為病理性肝損傷;0.25~0.5為13C-MBT-A級;0.15~0.25為13C-MBT-B級;<0.15為13C-MBT-C級。
三、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計量資料以均值±標準差表示,并采用t檢驗或方差分析;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應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OC曲線)下面積來評價指標對預后的預測準確性,ROC曲線下面積在0.8~0.9的模型被認為有很好的預測和判斷準確性,ROC曲線下面積≥0.7的有臨床應用價值。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以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13C-MBT代謝曲線的比較
(一)DOB曲線比較 結果顯示,LSS Ⅰ組至LSS Ⅳ組的DOB峰值依次降低,見圖1。其中LSS Ⅳ組曲線始終低平,峰值不突出,峰值出現較晚,較其他各組明顯降低(P<0.01),見表1。

圖1 各組DOB曲線
(二)MV曲線比較 LSS Ⅰ組至LSS Ⅳ組較對照組峰值逐漸下降,LSS Ⅰ組至LSS Ⅲ組峰值出現早且峰形尖銳,而LSS Ⅳ則相對平緩,見圖2。LSS Ⅳ組較其他各組峰值出現時間延長,且峰值不明顯,見表1。

圖2 各組代謝速率曲線
二、13C-MBT的主要參數比較
PBC LSS Ⅳ患者MVmax40、CUM40、CUM120和量化值均較其他各組明顯降低(P<0.01或P<0.05)。LSS Ⅲ組與健康對照組相比,CUM120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MVmax40、CUM4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13C-MBT的代謝曲線峰值及主要參數值(±s)
注:與對照組比較,aP<0.01,bP<0.05;與LSS Ⅰ組比較,cP<0.01;與LSS Ⅱ組比較,dP<0.01;與LSS Ⅲ組比較,eP<0.01,fP<0.05
三、13C-MBT量化值與肝硬化的關系
以有無肝硬化對PBC患者進行分組,并將是否存在肝硬化作為狀態變量對PBC患者13C-MBT量化值進行ROC分析,ROC曲線下面積為0.95,標準誤為0.5(95%CI為0.903~0.997,P<0.001),當量化值=0.63,約登指數達最大值0.75,此時敏感度為86.2%,特異度為89.2%。

圖3 各組PBC患者13C-MBT量化值的ROC曲線分析
四、PBC肝硬化患者13C-MBT分級與臨床Child-Pugh分級一致性分析.
將PBC肝硬化患者按照Child-Pugh分級分為A、B、C三級,該分級與13C-MBT分級一致率為82.3%(kappa=0.72,P<0.01),見表2

表2 13C-MBT分級與臨床Child-Pugh分級一致性比較(例)
討 論
13C-MBT是近年來出現的評價肝臟儲備功能的一種方法,13C-美沙西丁口服后可被腸道吸收轉運至肝臟,在肝細胞微粒體內代謝后生成13CO2經肺部呼氣排出,可通過質譜儀分析得出結果。肝臟微粒體內混合功能氧化酶系的活性及儲備能力直接關系到美沙西丁分解代謝生成13CO2的速率以及最終生成13CO2的量,故13CO2的呼出量能特異地反映肝臟細胞損害情況和儲備功能。13C-MBT和傳統肝功能檢測方法相比,具有準確、可重復、無創、方便等特點;但目前13C-MBT使用存在較多局限性,一方面是由于技術問題,另一方面13C-MBT較依賴于肝臟氧供應,并易于受已知或未知可影響P450酶的因素的干擾[5]。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嚴格規定了納入研究人群,以排除心肺疾病或藥物對13C-MBT各項參數的影響。
目前關于13C-MBT在慢性病毒性或酒精性肝臟疾病中應用的研究越來越多,但關于在PBC中的應用罕見報道。PBC病理發展過程與病毒或酒精性肝病不同,主要源于小膽管的病理改變,最終發展成肝硬化,因此13C-MBT在PBC患者疾病進展過程中的作用有待于研究。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隨著PBC患者肝臟病理分級的進展,13C-MBT主要參數如DOB峰值、MV峰值、MVmax40、CUM40、CUM120和量化值等逐漸下降,但早期PBC各組患者(LSS Ⅰ組、LSS Ⅱ組、LSS Ⅲ組)和健康對照組對比,其在統計學上無明顯差異(LSS Ⅲ組CUM120除外),而在肝硬化組(LSS Ⅳ組)有明顯統計學差異。因此13C-MBT在早期PBC患者的肝功能評估方面無明顯敏感性,無法與健康對照者區分。但對于進展為肝硬化的PBC患者肝功能評估有明顯的臨床意義。
既往研究顯示慢性丙型病毒型肝炎炎癥及纖維化程度可影響13C-MBT結果[6]。13C-MBT可用于檢測肝纖維和肝硬化,并監測肝臟功能[7]。而Braden[8]等研究發現,13C-MBT在丙肝引起的慢性肝病中鑒別肝硬化與非肝硬化方面的靈敏度為95%,特異性為96.2%。這與本研究中通過13C-MBT量化值鑒別PBC患者是否存在肝硬化,結果較為一致。在本研究中,ROC曲線分析得出,當PBC患者13C-MBT量化值<0.63時,診斷為肝硬化的敏感度為86.2%,特異度為89.2%,患者亟待于臨床密切觀察,以贏得治療時間,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考慮進行早期肝移植治療。
在PBC肝硬化患者中,從Child-Pugh A級發展至C級過程中,殘存肝細胞數量逐漸減少,肝臟儲備功能逐步下降。Child-Pugh分級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評估肝臟功能的方法,但是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難以具體量化患者肝功能的受損情況。既往報到中顯示,13C-MBT重要參數可隨著Child-Pugh分級的嚴重程度加重而降低[9,10]。而在本研究中我們采用量化值將肝硬化患者分為A、B、C三個等級,結果發現13C-MBT分級與Child-Pugh肝功能分級一致性達到82.3%。但呼氣試驗不依賴于肝性腦病、腹水等主觀指標,結果相對客觀,能夠以定量的形式直接反映肝細胞的儲備功能。因此13C-MBT可以方便、有效地對PBC肝硬化患者進行肝功能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