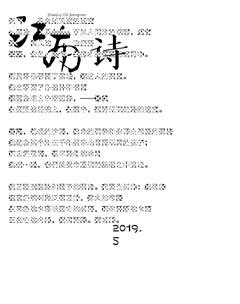唐祈,一九三八
唐祈,一九三八(三首)
室 友
早起晚歸的永遠是他。有時,
晚夢中有圣賢用金鑰匙開門救我的
情景,想必是他后半夜回來時的
惠贈。周末的三清君也會蒙頭[1]
睡他個整日,鼾聲沉雄而悲涼,
像戰畢的魔獸。十余平米的小寢室,
兩個人因為緣分而共棲,互磨習性,
共同愛護君子之交的好室風。
這空間的左翼由我據占,耽喜
清潔的西北氣質總讓我將周身世界
調置成有序和明亮。而那對面的
右翼地區,則雜亂,幾近于墮落。
且看那床墊一角不堪高蹈,發動
“脫離床板”運動,垂落在塵地。
被與褥,暗沉失寵,扭抱于一團,
仿佛蓄藏著一脈動人心魄的靜電。
在它們上面,間或有一兩處時間的
斑跡,古老而醒目,是苦悶的象征。
攤放的托福詞匯書,似乎在努力
證明它的主人并非進京乞討的人。
不修邊幅的南方驕子,并不貪戀
霓虹的招引,在這世俗時代活成
苦行的圣徒。他手握材料力學魔棒,
創造未來的新風景。最動情的詞語
也被他輸入航空器的心臟,使
燃氣渦輪發動機運轉出天使的嬌美。
被他研讀過的科學論著,此刻,
正山巒般堆疊在書桌,矗立于
零食、硬幣、車票、空瓶、快遞袋、
過期藥丸、會議手冊、胸卡、灰塵
和兩盒未拆封岡本的海面上,
搭成一道驚艷卻批判的后現代景觀。
冬季,學期末尾的午夜十二點,
朋友仍在實驗室內練習馭龍術。
在這狹小的陋室內,他那一側
寂寥的雪聲,是我每日必修的功課。
不是嗎?生活里的你我都是苦修者,
渺小而隱忍,如同龐大中國的每一個。
第一綠
一
我坐在開往郊區的公共汽車上,
以綠之名,擅長把沿路每一個人
都細膩地看過。塵土覆蓋著祖國,
并且支撐著我,一個殘忍的浪子。
五環外,遠省務工者的臉疲憊如霧,
亦如五道口咖啡館里精致的青年。
整個世界都是疲憊,金銀璀璨的
疲憊。在單向度的世紀,精神之鴿
在泥溝里流著血。誰才是勝者?
不管多混亂,我也能聽到你的心,
在一座龐大機器中被破損的聲音。
二
越往外走,世界越是衰老。我滿眼
都是傳奇者的白發。這世界燃燒已久。
高鐵從頭頂飛過,去往魔燈之城。
而我所乘坐的汽車,正穿過這道
漆黑的隧道,迎面就是萬仞的山峰。
我認出堅固如愛人。巖石與野梨花,
共同塑造成對方的風景。我喜愛事物
一切的交織,就像既愛又恨的我們。
山谷中刮來語言的春風,吹醒永世
只作為腹稿的我。何時才能完成終生的
真命題?何時才能親吻美人的手臂?
三
于是,事件的我,終于也在今天
被你閱讀。然后遺忘,徹底如野火。
汽車駛出群山,抵達平坦的田野,
農地里的母親和父親,在土壤上
高貴地衰老。也許,我的詞語
只應獻給一切貧窮的牙齒和手掌。
于是,綠,救命的綠,在我黎明
上空飛蕩著,與太陽一同重塑我。
在這沒有終點的汽車上,你,
一個不免顛簸的靈魂,練習過痛苦,
終會以綠的形式復活在每一次海邊。
唐祈,一九三八
這是抗戰的第二年,中國上空
飄飛著東瀛的灰罐子,專門帶走
美的魂靈。這一年,少年的詩人
與弟弟跟隨母親從南昌來到西北。
這一路,新奇的世界正在他面前
一頁一頁被打開,遼闊土地上的
風物和族群,成為他身體新的部分。
多么神奇,觀看不停地賦予我意義。
不僅蒙古族的女人,倉央嘉措,
也是人生的詩化與成熟的心智。
在地理遷徙中,他榮獲兩份禮物:
寬闊與深邃。是的,如他所說,
這是“一生的珍藏”,比寶鏡更美。
那不同于他的,不僅不是敵意,
卻是精神的泉水,汩汩引灌著我。
怎么說呢,在差異種種的今天,
詩人仍是我們要學習的好榜樣。
作者簡介:馬驥文,1990年出生于寧夏,詩作見載于《詩刊》《十月》《飛地》《上海文學》等刊,出版有詩集《唯一與感知者》(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曾獲首屆草堂詩歌獎·年度青年詩人獎、第十一屆未名詩歌獎、第六屆光華詩歌獎等獎項,曾參加《詩刊》社第33屆“青春詩會”,現負笈北京。
[1]清華園里一般把本、碩、博都在清華讀的人稱為“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