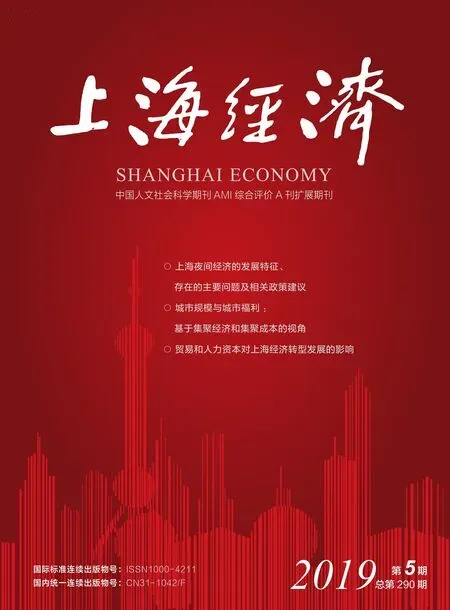長三角城市群生態環境-科技創新-經濟增長耦合協調時空分異研究
馬雙 張翼鷗
(1.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上海 200235 2.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 上海 200062)
一、引言
當今,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和飛速發展的科技創新引發了人們對于科學發展模式的思考,可持續發展理念成為世界各國積極推崇的發展方式(李虹、張希源,2016)。區域經濟的增長離不開科技創新的推動,同樣也離不開生態環境的保障。一般認為,科技創新對區域經濟的貢獻呈幾何系數增長(雷曙光,2017;胡曙紅等,2016),生態環境保護的高門檻則會阻礙區域經濟總量的增長,但卻有利于經濟結構的改善和優化。隨著中國經濟逐漸平穩步入新常態,人們開始日益關注生態、創新和經濟之間的有機結合與共生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努力踐行生態與創新的融合共生,推動綠色創新發展成為新時代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作為國內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和創新能級高地的長三角城市群,各地也不斷積極探索和實踐生態環境、科技創新與經濟增長的融合發展。上海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理念,爭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科學發展的先行者;蕪湖在安徽省內率先出臺《綠色發展行動計劃實施方案》,培育發展綠色經濟,提高生態文明軟實力,當好皖江崛起排頭兵、綠色發展領跑者;杭州圍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目標,引領都市圈產業轉型升級,倡導信息經濟與科技創新的新引擎作用。
在經濟地理學者日益從空間視角(Bathelt、Gluckler, 2003)關注人地關系和諧(陸大道,2002;程鈺等,2015)、區域間協調發展(沈玉芳等,2000;曾剛、王豐龍,2016)、區域內城鄉一體化(張永岳,2011;汪宇明等,2012)等問題時,我們也應從要素領域思考如何發揮各要素系統的耦合協調能力以期更好地發展。基于此,本文從生態環境、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關系入手,通過文獻梳理嘗試闡述三者間的內在聯系和作用機理,構建指標體系測度長三角城市群26個城市的耦合協調度,同時對區域類型和時空格局進行劃分和可視化表達,據此提出優化路徑以期為各地深入開展生態、創新和經濟三系統融合共生發展提供科學指導和政策借鑒。
二、相關文獻回顧
而生態環境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則較為復雜。Valadez和Hu(2016)研究了生態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發現中國對環境保護和綠色產業的投資并未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這可能與中國投資政策導向有關。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指出環境污染物與經濟發展并非線性關系,而是倒U型曲線關系,即雖然經濟的發展會伴隨著環境的惡化,但當經濟發展突破某拐點時,環境污染狀況將得到改善。范慧平等(2015)對河南省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進行了動態計量分析,結果表明在短期內兩者互為負向關系,但長期來看則變成正相關,這證實了Grossman和Krueger(1995)的觀點。Uddin等(2016)基于庫茲涅茨曲線對22個國家的碳足跡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表明了環境與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效應。工業時代,經濟快速增長導致生態環境惡化,但隨著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文明時代,經濟增長逐漸開始正向反饋生態環境(Kahuthu, 2006)。Galli等(2012)評估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對全球環境的影響,結果表明在過去的45年里中國和印度的生態足跡增加顯著影響了全球人均生態承載力,而Senbel等(2003)對北美地區的研究表明經濟活動和消費的增加對區域內生態生產力和消費平衡產生赤字,并可能降低生態可持續性,但長期來看則會出現方向效果。
高水平的環境管制和生態質量有利于科技創新的提升(Jaffe, 1997; Smith、Crotty,2010; Masaru, 2004)。著名的波特假說將生態環境及其管制納入修正的競爭力模型之中,該理論反對“高水平的區域生態環境將會增加企業費用,對生產率和競爭力的提升產生消極影響”這一觀點。認為適當的環境規制可以促使企業進行更多的創新活動,而這些創新將提高企業的生產力,從而抵消由環境保護帶來的成本并且提升企業在市場上的盈利能力,提高產品質量從而獲得競爭優勢(Porter, 1991)。生態環境的提升有利于科研成效和產業生產率的提高,良好的生態環境預示著高水平的區域能級、文化氛圍和政策環境(譚文華,2014;曹霞、于娟,2015),科研人員在舒適環境下能更好地發揮出聰明才智和潛能(Saxenian,1994)。而政府強力的環境治理倒逼本地產業升級,使得區域產業發展不得不訴諸于創新能力強的產業(Goldkuhl, 2009),現實中上海漕河涇高科技園區的科技綠洲品牌項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Kemp等(2000)從系統論的視角構建了環境管制與科技創新的理論框架,他們認為復雜制度、社會聯系和網絡等構成的規范和政策在生態環境和科技創新中扮演重要角色。錢麗與肖仁橋(2012)將生態環境效應納入農業創新系統效率評價框架之中,發現有效的生態災害防護有助于安徽省農業創新效率的提升。反過來,科技創新特別是環境保護和生態技術領域的創新突破,將提高傳統產業工藝水平,大大減少污染事件,改善生態環境。
三、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TOPSIS熵權法是有限方案多目標決策的綜合評價方法之一,它對原始數據進行同趨勢和歸一化的處理后,消除了不同指標量綱的影響,并能充分利用原始數據的信息,所以能充分反映各方案之間的差距、客觀真實的反映實際情況,具有真實、直觀、可靠的優點,而且其對樣本資料無特殊要求。其解決方案通常經過以下步驟:
①對m個研究區域n項指標構建初始矩陣A=(Xij)m×n,并進行歸一化處理,得到歸一化判斷矩陣B=(Yij)m×n,其中Xij為第i個區域的第j項指標值;
②確定各指標的熵值Hi并計算熵權Wi:

③確定理想解Z+和負理想解Z-,計算各方案與Z+、Z-的距離D+、D-:

④得出評價得分Ci:

Ci介于0到1之間,值越大,優劣次序越靠前。
建構主義是學習理論中行為主義發展到認知主義以后的進一步發展,最早的提出者可追溯到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杰(J.Piaget)和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Seymour Bruner)。70年代末,以布魯納為首的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將蘇聯教育心理學家維果斯基的思想介紹到美國,極大地推動了建構主義思想的發展。建構主義目前還未形成穩定的、統一的體系,其分類存在不同的方法。國內學者陳琦等歸納了六種不同傾向的建構主義:激進建構主義、社會性建構主義、社會文化認知的觀點、信息加工的建構主義、社會建構論和控制論系統。
耦合協調模型通常用來表示兩個或兩個以上系統相互作用和協調程度。根據之前TOPSIS法算出三大子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借助耦合協調模型得到生態環境-科技創新-經濟增長耦合協調模型如下:

其中,D為耦合協調度,T為三大子系統綜合評價值,f(x)、g(y)、h(z)分別為生態環境-科技創新-經濟增長子系統評價值,α、β、δ為待定系數,本文取值1/3。
(二)研究對象和數據來源
根據2016年5月國務院通過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本文選取長三角26個地級市作為研究對象。遵循科學性、全面性和數據可得性原則,本文構建了一個由18個指標組成的耦合測度指標體系(表1)。所需數據來源于2005-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統計年鑒、各城市年度統計公報等。

表1 生態環境-科技創新-經濟增長耦合測度指標體系
四、長三角城市群實證分析結果
(一)三維子系統評價指數時空分異
首先,對生態環境、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三系統的指標進行了信度和效度檢驗,結果表明指標間相關性顯著。接著,利用TOPSIS熵權法對三個子系統各年份綜合評價指數進行計算,結果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2005-2015年間,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經濟增長與科技創新均大體呈上升趨勢,且基本保持同步,經濟增長指數從0.47上升至0.53,科技創新指數從0.44上升至0.49。其中,在2009年出現較大幅度下降,這可能與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有關。而在2012年之后,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增長指數出現小幅下降并開始保持穩定,這與中國經濟下行并進入新常態有關。相反,生態環境指數出現先下降后上升的態勢,從2005年的0.30下降至2011年的谷底0.25,之后又微幅上升至0.28左右的穩定水平,這與之前的研究判斷基本吻合:區域經濟的增長伴隨著生態環境的破壞。黨的十八大以來越發重視和強調生態文明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更是把生態保護、綠色發展放在首要位置。作為幾大國家戰略的交匯地,長三角城市群生態環境、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發展態勢成為中國近10來發展的縮影。

圖1 2005-2015年生態環境、科技創新與經濟增長指數變動情況
在整體發展演變分析的基礎上,選取2005和2015年兩個時間節點對長三角城市群內26個城市三個子系統進行了綜合評價(表2)。2005-2015年,長三角城市群的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指數格局總體相對穩定,且兩者呈現一定程度的相關。高值區域主要分布在上海、蘇南、浙北三地,其中上海在兩項指標上的首位度優勢明顯,且與第二位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分別從2005年高出0.11和0.14提高到2015年高出0.13和0.16。低值區域幾乎都在安徽境內南部城市,滁州、宣城、池州、安慶末位次序未發生變化,但經過十年發展差距在不斷縮小,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水平有所改善。合肥、嘉興、南通等地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均有顯著提升,臺州、泰州、揚州則有較大幅度的衰減,這表明上海作為長三角龍頭城市的輻射帶動能力在不斷增強,地理鄰近城市受益匪淺。
與創新和經濟相反,生態環境指數變化劇烈,整體上呈下降趨勢,在空間上表現出明顯的“紅增綠減”態勢。2005年,上海、蘇南蘇中、浙西北、安徽南部和東部均呈現良好的生態環境格局,而一些沿海城市生態環境指數反而較差。到了2015年,安徽省大部分城市(除了銅陵、池州、滁州)、江蘇南京和揚州、浙江嘉興都有大幅下降,湖州、滁州、泰州等有大幅度上升,而舟山、杭州、蘇州、寧波等則有小幅增加,其中杭州從2005年的第二位上升到第一位,超越上海成為長三角城市群生態環境指數最好的城市。通過計算生態環境指數的標準差,我們發現長三角城市群的生態環境指數差異擴大了接近1倍。在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指數均呈穩定上升態勢的情況下,生態環境系統發生嚴重倒退現象,空間格局和地區分異也出現劇烈變動和陡然增大,這與人們預期和以往實證研究存在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張榮天、焦華富,2015;彭迪云等,2016)。

表2 2005年和2015年長三角城市群子系統綜合評價得分
(二)耦合協調度評價和類型劃分
借助耦合協調評價模型,計算2005-2015年長三角26個城市歷年的耦合度及均值,并將耦合類型劃分為5個層級:嚴重失調(小于0.20)、輕度失調(0.20-0.40)、一般協調(0.40-0.60)、中度協調(0.60-0.80)、高度協調(大于0.80),計算結果、各城市耦合類型和主要制約因素見表3。
上海是長三角城市群內唯一高度協調的城市,其主要制約因素是生態環境。杭州、南京、蘇州、寧波、無錫、紹興、常州是中度協調城市,鎮江、合肥、嘉興、湖州、臺州、金華、南通、馬鞍山、揚州、泰州是一般協調城市,其中大部分城市的制約因素為生態環境。屬于輕度失調類型的城市有鹽城、舟山、蕪湖、銅陵、宣城,其制約因素主要是科技創新和生態環境,而屬于嚴重失調城市的安慶、滁州、池州則主要受限于經濟增長。總體而言,處于失調狀態的城市不足三分之一(8個),耦合協調受制于生態環境的城市超過一半(14個),長三角26個城市是一個總體協調、生態環境系統相對落后的城市群。
從空間格局來看,長三角城市群耦合類型呈現滬寧杭Z字形高水平發展軸,輔以合肥-馬鞍山、金華-臺州、揚鎮泰-南通較高水平發展帶,以及安徽大部、蘇北低水平發展區的空間結構特點。其中,上海的極化輻射效應明顯,離上海越近的城市其耦合協調度也越高,南京、杭州作為兩個副中心高地也呈現出較好的帶動效應,而合肥的帶動效應則不明顯。

表3 2005-2015年長三角城市群耦合度計算結果及耦合類型
五、結論與建議
如何更好發揮區域內各要素系統間的協調發展潛力、探索科學有效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已成為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日益關注的問題之一。本文以長三角城市群為案例,借助TOPSIS熵權法計算了2005-2015年26個城市生態環境、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三個要素系統的評價指數,接著利用耦合協調評價模型計算各城市耦合度并進行類型劃分,最終刻畫出長三角城市群耦合協調發展水平的時空分異格局。
本文通過研究發現,長三角城市群三個子系統的時空動態變化過程中,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呈現較高程度的一致性且相對穩定,而生態環境的變動性較大。從時間演化來看,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均呈現穩定上升趨勢,而生態環境則出現波動下降的情況,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并未帶動生態環境指數的提升;從空間分布格局來看,經濟增長水平高的城市,科技創新水平也相對較高,但生態環境指數的相關性不明顯。擁有低生態環境指數的城市既有鹽城、南通、寧波、臺州等沿海較發達地區,也有合肥、蕪湖、馬鞍山等內陸發展較快城市。
通過進一步的耦合協調指數分析,我們發現長三角城市群總體協調,但發展受制于落后的生態環境系統。上海、蘇南、浙北等綜合發展水平高的城市其耦合協調度越高,相對低水平的安徽大部分城市的耦合協調度則較低,整體格局大體呈現滬寧杭Z字形高水平發展軸,蘇中、浙南、徽中較高水平發展帶,以及安徽大部、蘇北低水平發展區的空間結構。其中,滬寧杭三座城市的帶動效應顯著,而合肥則不太明顯。
本文的研究結果為長三角城市群提升核心競爭力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和政策指引。在日益強調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城市群中各城市內部的各要素系統間應保持較好的協調性,而且不同的城市因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制度環境、文化差異、區域特性的差異會遇到不同的發展瓶頸,因此要根據各自的制約因素著重補發展短板。上海、杭州、南京等綜合發展水平較高、耦合協調度較好的城市應進一步發揮龍頭帶動作用,擴大輻射范圍向內陸縱深影響;合肥應充分把握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的高度耦合關系,提升經濟科技創新水平,同時充分發揮兩者對生態環境的拉動作用;江浙兩地的沿海沿江發達城市在保證經濟增長、科技創新高水平的前提下,應更多關注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安徽省其他城市要以《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為契機,結合自身優勢,立足區域實際,加快轉型步伐,推動區域發展方式向生態環境、科技創新、經濟增長耦合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方式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