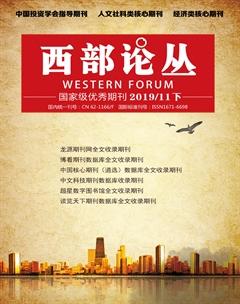淺析古代中西方刑罰制度之比較
衛曉青
摘 要:刑罰制度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斷變化,不同時期和地區的刑罰有不同時期的特點。本文通過了解中西方刑罰制度的起源,從刑罰體系、刑罰手段、刑法適用范圍三個方面對中西方刑罰制度進行對比,做簡單的分析,為促進當代法制建設提供參考。
關鍵詞:刑罰制度;起源;制度比較
一、古代中西方刑罰制度的起源
刑罰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與變化,實質上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濃縮。
關于刑罰的起源,古人有多種主張,主要有:刑出于天、刑源于苗、刑始于兵、以及刑罰是由象刑演變而來。最早出現類似刑罰的概念,是《尚書·舜典》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所以我認為中國古代刑罰的起源是由象形演變而來的。但不論是“刑始于兵”,還是刑罰是由象刑演變而來,我們都可以看出,當時刑罰的出現是來約束萬民,形成有序的統治。
西方出現“刑罰”這一類似概念,應是在《烏爾納姆法典》中的罰金形式[1]。《烏爾納姆法典》是至今為止已經發現的最古老的成文律法,其中沒有以牙還牙的刑罰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罰金形式。在后來的古代奴隸制國家,國王和貴族們的權威至高無上,他們對犯罪行為的懲罰極其簡單,大約只有兩種:要么是處死,要么是奴役。早期西方刑罰處于以復仇為主要目的的階段,到中世紀演變為威懾,集權威懾成了中世紀的主要刑罰思想,進入十七世紀以后,受文藝復興等影響,刑罰進入到博愛階段。
二 、古代中西方刑罰制度的比較
(一)從刑罰體系方面比較。中國古代的刑罰體系是以五刑為核心內容的法律體系。根據史料、古籍的證明,自夏朝時起,各代統治者便將刑法統稱為“五刑”。那時的“五刑”指墨、劓、刖、宮、大辟,被稱為奴隸制五刑[2]。從奴隸制的五刑我們可以看出,存在大量野蠻殘酷的色彩。《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夏有亂政,而坐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可見奴隸制時期的刑罰體系,均是以肉刑為基礎的刑罰制度。后進入封建社會,刑罰體系由肉刑為主向以勞役刑為主的方向過渡。文景時期鑒于肉刑使罪犯肢體損壞,失去勞動能力,為了增加勞動力、促進生產、發展經濟,于是開始廢除肉刑的改革,后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廢除肉刑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用“笞、杖、徒、流、死”逐步代替了“墨、劓、刖、宮、大辟”,這是刑罰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因此我國古代的刑罰體系在總的趨勢上是逐步完備,朝著不斷文明寬緩的方向發展的。
西方的刑罰體系和我國古代刑罰體系額的趨勢是相同的,均逐漸完備,都經歷了一個有濫用到慎用、嚴苛到輕緩的過程。西方法律文化受到神學自然法化的影響,刑罰體系也日趨人道[3]。從教會法方面看,刑罰種類包括:補贖類刑罰、監禁刑、死刑。其中補贖類刑罰最輕,包含財產刑、羞恥刑等;監禁類分為普通監禁和嚴格監禁;死刑則通常以絞刑和火刑為主。而之前的羅馬法,則是以肉刑為主,刑罰殘酷,而由后發展,特別是啟蒙運動以后,伴隨著近代刑法思想的傳播,刑罰的形式隨著時代的經濟與政治的發展逐漸發生著改變。從對他人產生人身傷害到侵害他人隱私與財產經濟,這種現象的出現進一步刺激了西方法律的完善以及刑罰體系的建設。
(二)從刑罰手段方面比較。古代中國和西方刑罰手段前期都被認定為“殘酷、野蠻”,均通過刑罰的輕重來體現。但仔細分析,二者判定刑罰輕重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肉刑是最殘酷的。肉刑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一是在臉上刺字、烙印等毀人肌膚,例如墨刑等;二是破壞人的身體器官和技能,使人散失勞動能力,例如刖刑、宮刑、劓刑、車裂等;三是擊打人的身體,產生肉體疼痛的效果,且多者都會喪命,屬于變相死刑,例如笞刑、杖刑等。而凌遲超越了上述刑罰,凌遲是最殘忍的肉刑。西方的古羅馬,身體刑的執行方式包括笞刑、鞭打、棒打等。拜占庭帝國刑法規定的斷肢刑,有砍手、割舌、割鼻、挖眼、去勢、鞭打、絞刑等。
基于此,中西方刑罰輕重的標準是不同的。例如斬刑與絞刑,在古代中國認為斬刑更重,而西方卻認為絞刑是極刑,原因在于二者的思想文化不同。在西方國家看來,絞刑的死亡過程漫長而痛苦,絞刑的時長多于斬刑,因此是最嚴厲的刑罰。而在中國人看來,絞刑比斬刑輕。中國自古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孝在傳統文化中處于核心地位,中華傳統文化認為身體是父母賜予的,不能隨意毀壞。尸首分離為古人所不恥,因此,刑罰的輕重具有相對性,其雖然刑罰手段均殘忍野蠻,但中西方認定刑罰輕重的標椎是不一樣的。
(三)從刑罰適用范圍方面比較。刑罰適用范圍,指的是刑罰適用在什么地方、什么時間、和什么人。中國古代刑罰在適用范圍上,有其特有的特權性和階級性。從奴隸社會“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開始,幾乎每個階級都把維護本階級等級制度和特權制度放在重要位置,這在刑罰制度的設定上也有體現[4]。在中國古代的刑法中,罪名與刑名是緊密聯系的,一般來說貫徹了同罪同罰的原則,借以維護統治階級的法制,但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刑法也表現出等級特權性,貴族高官可以根據議、請等規定,而獲得同罪異罰的法定優待。隋代確立的“八議”制度,規定對八種人犯罪必須交由皇帝裁決或依法減輕處罰的特權制度。唐朝的“議、請、減、贖、當”是唐律疏議的貴族官員減免原則,這也體現了中國古代專制主義集權下,階級社會刑罰下的階級本質。
西方的古羅馬時期,一是對于罪犯要考慮原因、地點、行為、時間及后果,才決定刑罰適用;例如區分白天盜竊還是夜盜、父母老師出于糾正目的則不予責罰、二是身份高貴減輕處罰原則;身份性體現了兩個方面,一是社會身份不同處罰不同,其實類似于我國的貴族官員減免原則;二是血緣關系不同處罰不同,如殺親罪的處罰與一般殺人罪的處罰則不同。除了如此,古羅馬也存在類似我國古代的上請制度,地方議員不能被處以死刑或者礦場勞役。
三、結語
上述種種,從三個方面厘清了中西方刑罰制度的異同,可見刑罰制度在不同地區有其相似性,從中理解了差異性和相似性,才能有助于二者的制度研究,了解中國的本土性刑罰色彩,從而對現代社會如何選擇制度和進行制度設計提供借鑒。
注 釋
[1] 張偉辰:《小異中西古代刑罰制度之差異》,西北:法制博覽2014,10,第271頁.
[2] 陳佳維:《論述中國古代的五刑制度》,河北:社會科學論壇,2014.07.第242頁.
[3] 耿健翔:《論基督教神學自然法對西方刑法學的影響》.海南:海南大學,2015 ,05,第10頁.
[4] 韓文政、李坤輝:《中國古代刑罰制度的演變及特點》.黑龍江:學術交流.2012.06. 第58頁
參考文獻
[1] 大木雅夫,東西方法文化比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 楊一凡,新編中國法制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3] 王永寬,扭曲的人性—中國古代酷刑[M],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
[4] 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略[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
[5] 張楠,清末以來刑罰”中重西輕”之爭現象研究[D],寧夏:寧夏大學,2017.
[6] 張偉辰.小議中西古代刑罰制度之差異[J].山西:法制博覽,2014.
[7] 耿健翔.論基督教神學思想自然法化對西方刑法學的影響[J].海南:海南大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