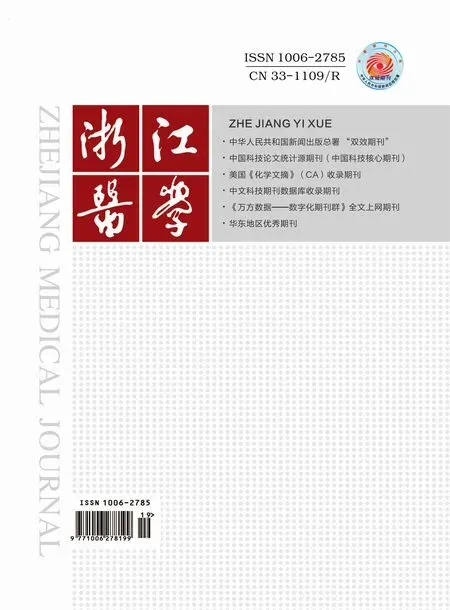應激性心肌病的臨床特點分析
侯良磊
應激性心肌病(Takotsubo cardiomyopathy,TTS)最早于1990年由日本學者報道,一度被認為只發病于亞裔人群;隨著歐美病例被報道,逐漸引起西方醫學界重視。TTS的特點是短期內左心室壁運動異常,并有與急性冠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相似的臨床特征,如胸悶、胸痛、呼吸費力等癥狀,心電圖檢查異常、心臟生物標志物水平升高等。目前國際上對該病更一致的稱呼為Takotsubo綜合征(Takotsubo syndrome,TTS),因中文應用習慣,部分場合仍沿用“應激性心肌病”這一傳統稱呼,本文以TTS稱呼。近年來臨床醫務工作者對TTS認識加深,診斷病例數較早年有所增加,漏診、誤診情況明顯減少。筆者收集本院診斷的9例TTS患者,結合其臨床表現、輔助檢查結果、預后等情況,分析該病的臨床特點,探討其診斷要點和治療方法,現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收集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本院急診-心血管內科收住或診斷的TTS患者,入院診斷中“應激性心肌病”或“Takotsubo syndrome”為主要診斷或次要診斷之一的患者共12例,排除僅臨床診斷或僅會診時考慮的3例患者,最終納入9例患者,男2例,女7例,平均年齡 68.44 歲,平均住院日(14.22±8.38)d。初步診斷方法采用Mayo2014標準[1]。9例患者中6例存在明確誘因,其中親人去世1例,極度激動或爭吵3例,軀體應激(高度勞累)2例,癥狀以胸悶為主者3例,胸痛3例,一過性神志不清2例,因其他原因發現心電圖改變 1例。入院患者血壓 142(129,157)/74(70,84)mmHg,心率 86(69,104)次/min。
1.2 方法 回顧納入患者的病例資料,包括就診后首次收縮壓、舒張壓、心率、入院時肌鈣蛋白、氨基末端腦鈉尿肽前體(N terminal pro B type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D-二聚體以及心電圖、心臟超聲、冠狀動脈、左心室造影等檢查結果。
心臟超聲采用飛利浦EPIQ7C超聲診斷系統、西門子ACUSON SC2000多普勒心超儀,測量左心房內徑、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冠脈造影最少由2位心內科醫師操作并診斷,左冠狀動脈至少掃描3個體位,右冠狀動脈至少掃描2個體位。從醫學影像系統內提取完整圖像并截取所需左心室造影圖像。冠狀動脈病情依據美國心臟病學會診斷標準,計算狹窄程度。
InterTAK診斷評分由國際Takotsubo注冊中心制定,旨在為臨床醫生提供評估TTS診斷可能性的模型,也可一定程度上鑒別TTS和 ACS。InterTAK診斷參數及分值為女性25分,情緒觸發24分,身體觸發13分,無ST段壓低(aVR除外)12分,精神疾病11分,神經系統疾病9分,QT間期延長6分[2]。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進行K-S正態性檢驗,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P25,P75)表示,治療前后比較采用秩和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檢驗結果 平均NT-ProBNP為(3 311.89±3 561.65)pg/ml,其中3例NT-ProBNP較高患者在治療后有復查NT-ProBNP,中位數7 530pg/ml下降至1 853pg/ml,治療前后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入院肌鈣蛋白 I為(6.74±7.44)μg/L,D-二聚體為(1 265.75±1 289.12)mg/ml,LDL-C 為(2.90±1.25)mmol/L。
2.2 心電圖表現 9例患者心電圖均表現異常,ST段抬高、T波改變患者4例,伴明顯Q波1例,ST段壓低伴T波改變患者2例,ST段無明顯改變,T波倒置、伴QT延長為主患者1例,房室傳導阻滯者2例,表現以下壁導聯(Ⅱ、Ⅲ、aVF)改變為主者3例,以前壁導聯(V1~V6)改變為主者4例,其中廣泛前壁1例,其他導聯改變為主者1例(Ⅰ、AVL)。見圖1。

圖1 3例TTS患者入院時心電圖檢查(左側為入院心電圖,右側為其住院觀察或治療一段時間后的心電圖改變;a:表現為ST段抬高、T波倒置的“急性心肌梗死演變期”表現,但4d后改善,一般在臨床中會理解為冠心病動態演變,但該患者為骨科患者,無心肌梗死、心功能不全;b:表現為前壁ST段抬高,廣泛Q波的“心肌梗死”樣表現,右側為住院3d后,仍存有一定的Q波、ST段基本回歸基線;c:表現為廣泛前壁的T波倒置,在院3d后復查提示T波倒置幅度明顯改善,在平素臨床工作中此亦常理解為“心電圖ST-T動態變化”的急性冠脈綜合征改變,但該患者冠脈造影同樣提示冠脈無嚴重狹窄)
2.3 心超檢查結果 9例患者中見心室壁節段性運動減弱4例,其余5例僅提示“左心室運動減弱”或“左心室收縮(舒張)功能減退”。因本中心急診床旁超聲檢查無書面報告或住院多日后才行正式心超檢查,資料中正式報告未提示左心室運動減弱,與左心室造影結果不符,EF值也多正常。9例患者EF值為(64.44±10.46)%,左心房 31.5(26,35.25)mm,左心室42.5(39.25,43)mm。
2.4 冠脈造影結果 9患者均行冠脈造影,其中6例未見任何冠脈狹窄,右冠狀動脈50%狹窄1例,右冠狀動脈60%狹窄1例,前降支70%狹窄1例。9例患者均行左心室造影,結果均提示心尖部收縮運動減弱,其中心尖部氣球樣改變1例,心尖活動幾乎消失1例,左心室前壁、心尖部活動減弱1例,基底部活動增強4例,左心室中段活動增強1例。見圖2。

圖2 84歲女性患者典型TTS左心室造影檢查(表現為左心室心尖部氣球樣,幾乎沒有收縮運動,而基底部收縮增強,呈現經典的“章魚簍”樣運動)
2.5 InterTAK評分 9例患者InterTAK評分為34~67(46.77±12.34)分。
2.6 預后及隨訪情況 所有患者均好轉出院,門診隨訪3個月~2年未再發TTS。
出院后電話隨訪,未留有效電話1例,失訪2例(其中1例電話失效),最終隨訪6例,其中1例患者因非相關因素去世,4例患者目前一般情況可,1例患者拒絕提供詳情。
3 討論
TTS的發病機制最常見的幾個學說包括:(1)軀體、精神損傷等各種因素,交感神經系統過度激活,兒茶酚胺大量釋放,心肌損傷;(2)心肌缺血后恢復血供,未死亡的心肌恢復正常功能需要一段時間,也稱心肌頓抑;(3)雌激素減少,對兒茶酚胺的對抗作用不足;(4)冠狀動脈血管或微血管結構功能異常;(5)斑塊劈裂;(6)多支心外膜血管痙攣;(7)基因突變、遺傳相關[3]。以上幾個學說,很多情況下不是單一機制作用,而是多種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
與既往國際登記的TTS研究相似,本研究中大部分病例都出現了心臟標志物改變,NT-proBNP升高和TTS高度相關,與以下元素有聯系:交感神經過度激活的程度(去甲腎上腺素濃度)、C反應蛋白濃度峰值(提示BNP釋放可能是炎癥起源的一部分),以及左心室功能不全情況[4]。本研究中部分患者NT-ProBNP數值住院治療后從中位數7 530pg/ml下降至1 853pg/ml,但因樣本量較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本研究中幾乎每例患者都出現肌鈣蛋白升高,但與經典ACS相比,平均峰值明顯較低。本研究發現,入院肌鈣蛋白水平高低和預后有一定關系,這與既往的研究結果一致[5],也有研究提示該病左心室局部室壁運動受損程度常大大超過相關心肌壞死標志物上升程度,可能反映了心肌損傷可逆(頓抑)[5]。另外也有基礎研究發現一些其它生物標志物和該病有關,如微小RNA等,但此類觀點缺乏在臨床應用的經驗[6]。
對于心電圖改變,TTS和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均有ST段抬高的表現,也常常伴有T波改變,T波的改變可能和心肌水腫、頓抑等相關。根據2018年TTS臨床專家共識的,可以認為TTS的ST段抬高集中在胸前導聯 V2~V5和肢體導聯Ⅱ和aVR,而在前壁 STEMI的患者中,ST段抬高集中在胸前導聯V1~V4和肢體導聯Ⅰ和aVL,這可作為初步鑒別依據,但是在本研究中未應用到該結論[7]。2018年TTS臨床專家共識提出了2種具有高靈敏度和特異度的心電圖標準來區分TTS和前壁STEMI。首先是關注胸前導聯ST段抬高,特別是V1導聯,因為該導聯ST段抬高在TTS中不明顯,在 STEMI中常見;另外ST段抬高局限于下壁導聯(Ⅱ、Ⅲ、aVF)在 TTS中少見[7]。另QT延長、T波倒置可能是另外常見的因素,這些不典型表現也需引起重視,QT間期延長常有時會引起尖端扭轉性室速,造成預后不良[8]。
盡管心肌標志物和心電圖非常重要,但與ACS的最終鑒別診斷還需冠狀動脈造影,尤其是在ST段抬高患者中,非侵入性檢查無法排除心肌梗死。在本研究入選的9例患者中,均在冠脈造影排除STEMI后行左心室造影完成初步診斷,顯然在部分冠脈造影陰性的患者中必然存在漏診。增強臨床醫生對該病的認識后,左心室造影的例數較前增加,漏診率則減少。
超聲心動圖是評估左心室功能改變最常用的影像學工具。在既往的TTS專家共識中,將諸多文獻的超聲心動圖改變歸納為 4種不同的變異型,包括:(1)心尖部氣球樣變,心尖中部心肌節段運動減退;(2)心室中部運動弱為主;(3)累及心室基底段為主;(4)以前外側段為主[7]。在本研究收集的病例中,超聲中4例可見心室壁運動減弱,但因早年醫師可能無足夠資料系統學習TTS超聲改變,僅報道心室節段性運動減弱,另外5例僅報道“左心室運動稍減弱”或因住院多日后才行正式心超檢查,正式報道未提示左心室運動減弱,與左心室造影結果不符。有研究總結在可疑患者中,AWMSI(室壁運動得分)≥1.75且有4個以上功能異常節段,對該病的診斷有較高的特異度[9]。
此外,心血管磁共振成像可以評價節段性室壁運動異常、心室功能,對判斷及評估TTS心肌組織的特征(如水腫、炎癥、壞死纖維化)有非常重要的價值[10]。但對急性新發的TTS,臨床醫生大多忙于進行談話及確定是否要行急診冠脈造影,本研究入選的所有患者均沒有行心臟磁共振,是研究不足之處。
InterTAK診斷評分由國際Takotsubo syndrome注冊中心制定,來自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診斷takotsubo綜合征的預測因素[2]。旨在為臨床醫生提供評估 TTS診斷“可能性”的評分模型,也預測存在 TTS的概率并鑒別TTS和 ACS。評分項包括性別、情緒、QT間期延長等7個因素,評分值>50分的患者患TTS的概率為18%,評分值>70分的患者患 TTS的概率為90%。本研究中>50分患者較多,但無患者>70分,這可能和患者精神、神經系統疾病史追問記錄不詳有關,普及該評分,需醫師在接診患者時增加對患者病史的關注。
對于TTS的治療,由于缺乏前瞻性隨機對照的臨床試驗,目前治療策略是基于臨床經驗和專家共識。在急性期用藥上,對于β受體阻滯劑普遍觀點不支持有益,而左西孟旦可能對該病有益,對于ACEI/ARB類藥物則有不通的看法,部分觀點認為有用,部分反之[7]。對于TTS合并心力衰竭的治療,除了常規治療外,應避免應用一些正性肌力藥物,如多巴酚丁胺、腎上腺素等[7]。出院后,可以考慮應用ACEI/ARB類藥物、精神藥物,部分患者可以雌激素替代治療[7]。
本研究回顧了9例本院診斷的TTS患者,從入院癥狀、輔助檢查等歸納統計了該病的一些臨床特點,臨床資料較為充分,但本研究屬于回顧性研究,也為單中心研究,因病例較少,研究總樣本量較小,難以得出有指導性意義的結論;另外,早年對該病認識有限,沒有跟進心臟核磁共振成像等輔助檢查,也沒在出院后足夠重視病歷而獲得足夠詳細的院后隨訪資料,此外,因該病起病急,對急診不少患者存在漏診可能,都是本研究遺憾。
目前在國際上已有較大TTS數據庫,雖然此病因發病率低而缺乏臨床指南,但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研究指導臨床工作者更好地作出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