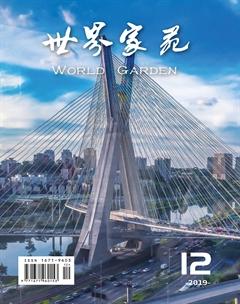風險社會下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規制
亢奕嘉

摘要: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食品種類的日益豐富,人們對食品的要求已從吃飽變為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守護舌尖上的安全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但是食品安全的問題依舊頻頻發生,如“染色饅頭”、“三聚氰胺”、等一系列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使我們必須重視完善我國的食品安全的有關法律、法規。目前我國關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立法還存在著體系不完善、刑罰設置不完善等問題,針對我國立法的不足之處應增強刑法與行政法的協調性,在刑罰體系完善罰金刑以及增設資格刑。
關鍵詞:風險社會;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規制
1 風險視角下的食品安全犯罪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面對的風險也越來越多,包括自然帶來的風險也包括人類自身帶來的風險,風險刑法由此而生,風險刑法的優勢表現為以下兩點:第一,實現法益保護的抽象化,風險刑法無需結合危害結果來進行判斷,如果行為本身具有風險性,就可以予以打擊。第二,實現法益保護的早起化。風險社會的突出特點是風險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對于出現危害結果時才啟動刑法已經不能實現對社會的保護了,風險刑法并不要求危害結果出現才啟動刑法,對于實施了足以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危險行為,能夠及時的制止。
風險刑法對食品安全的要求,是指在整個生產食品的過程中,不能實施可能對人體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危險的行為,一旦在生產過程中存在這種對人體生命健康的風險,就需要擔刑事責任。食品安全犯罪的“風險”,并不取決于是否有特定的危險結果產生,比如我國刑法關于生產、銷售假藥罪所描述的具體危險,而是一種可能對他人法益造成潛在危險的風險,無需結合危害結果判斷,行為人應對這種行為本身的風險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2 我國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規制中的問題
2.1 刑法體系不協調
我國《刑法》和《食品安全法》對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規定,構成了我國關于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體系,保持兩者在規制食品安全犯罪上的一致性,能夠避免出現適用法律混亂的情形。然而就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來看,從兩者的之間還存在著主體、對象規定等方面的不協調。
關于食品安全犯罪主體方面的規定,根據我國《刑法》關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規定可知,刑法對其的打擊范圍僅限于生產、銷售環節以及監管環節,而對運輸、貯藏等環節并未規定。而反觀《食品安全法》關于違法主體的規定,其涵蓋面明顯大于刑法分則的規定,它包括了從食品原料的初級生產到最后成品銷售過程中整個流程中涉及的相關人員,種植者、運輸者和貯藏者都在其涵蓋范圍內,這樣就容易造成對于食品原料的生產者、貯存者和運輸者等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人無明確法律依據追究其刑事責任,造成司法適用上的混亂。我國《刑法》規定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對象較為單一,從《刑法》第 143、144 條的規定來看,對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對象僅限于食品,并且此處的食品并未有相關司法解釋對其進行擴大解釋,而《食品安全法》第二條規定的食品添加劑、食品的包裝材料、消毒劑、洗滌劑以及與食品相關的產品,則無法按照《刑法》第143、144條的規定來定罪處罰,僅能對其實施行政處罰,這樣無疑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
從理論上來說,刑法具有二次違法性,即某種觸犯刑法的行為首先一定經過了相關行政處罰的評價,進而因為社會危害性較大,從而進入刑法的評價視野,這也是刑法作為社會最后一道防線的應有之義。對于食品安全犯罪來說,刑法必須發揮堅強后盾的作用,尤其是在風險社會中,我國刑法必須有所作為,我國刑法行當做到與《食品安全法》的有效統一。
2.2 刑罰設置不完善
從我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屬的章節,可知其性質是屬于經濟犯罪犯罪范疇,基于經濟犯罪大都具有貪利性目的,我國刑法對食品安全犯罪中不僅設置自由刑,而且設置了相應的財產刑,采取“并處罰金”的方式,但是,在罰金刑使用過程中還存在著罰金刑數額不夠明確、標準也不統一的問題。這種不確定的規定不僅不能為司法實踐提供指引作用,反而容易造成適用上的混亂。
我國對于食品的生產者、銷售者都實行相應的市場準入制度,即必須經過法定程序取得相應的職業資格才能進行相應的食品活動。作為食品安全犯罪的主體,必會利用其職業資格作為犯罪的根本,我國現行的刑罰體系中規定的資格刑僅僅是指限于剝奪政治權利這一項,沒有明確的規定職業資格刑就意味著,行為人即使被判處資格刑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但并未剝奪其進入食品行業的權利,其仍然有可能從事食品犯罪活動,這樣不利于對食品安全犯罪的遏制。
3 我國食品安全刑法規制的完善
3.1 協調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體系
在我國,《刑法》和《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犯罪的規制,構成了我國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體系,要想更進一步加強對食品安全犯罪的規制,必須要保持兩者在規制食品安全犯罪上的一致性,增強兩者之間的協調性。首先,應擴大刑法中關于食品安全犯罪的主體范圍,我國刑法分則僅僅對食品在生產、銷售環節的參與者進行規制,如果要保持與《食品安全法》的協調,加大對食品安全犯罪的打擊力度,必須將其他犯罪主體囊入其中,將犯罪主體擴大至加工者、運輸者、儲存者。其次,擴大刑法關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規制對象,隨著社會的發展,“食物”的含義已不能僅僅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食品,同時還包括食品添加劑以及食品相關產品,為保持《刑法》與《食品安全法》的一致性,刑法也要將食品添加劑以及食品相關產品納入保護的范圍。
3.2 完善財產刑適用標準
我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雖幾經修改,但在刑法分則體系所屬章節一直未發生變動,這在性質上表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仍屬于經濟犯罪范疇。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罰金刑可以作以下修改:一方面是明確罰金刑的數額。明確其最低罰金限額,同時也要兼顧與《食品安全法》中關于行政罰款的設置相協調,其最低限額可與《食品安全法》中規定的數額相一致,關于最高限額可以根據案件不同而自由裁量但不能超過一個限度;另一方面是關于不同的犯罪主體設置不同的罰金刑,對于從事食品行業的單位其規模往往比個人的規模大,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其對公共的飲食健康安全帶來的惡劣影響更大,若對兩者實行相同的罰金刑有失公平也不能達到有效預防的目標。因此,對于單位犯罪的罰金額要明顯有梯度的高于自然人犯罪的罰金額。
3.3 引入職業資格刑
刑罰是一種事后制裁,它的功能主要是指個別預防功能和一般預防功能。資格刑是附加刑的一種,它通過剝奪犯罪人法律上賦予公民享有的一定權利為內容,作為刑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著久遠的立法淵源。針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我國可以針對個人和單位設定不同的資格刑:針對自然人,資格刑可以根據其犯罪情況設置為剝奪或限制一定年限甚至終身從事食品生產經營活動。而對于單位而言,對其職業資格刑的設置不能僅僅限于禁止其在一定時間內從事食品生產,還應包括對其榮譽稱號剝奪的附加資格刑,單位的榮譽稱號往往與商業利益掛鉤,榮譽稱號的剝奪意味著商業利益受損,使之得不償失,無利可圖,從而達到其預防再犯的刑罰效果。
食品安全問題關乎民生,一旦發生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就會對整個社會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所以,我國積極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予以規制,《食品安全法》是關于食品安全方面覆蓋面最廣,懲罰力度最大的法律,《刑法》對于食品安全犯罪也有規定,但是其對食品安全犯罪的規制還不夠完善,健全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體系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應加強行政法規與刑法的有機統一。在本文中,通過分析我國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規制方面的問題,提出相關完善意見,以便能用更科學、更有效的法律法規,來減少甚至避免食品安全犯罪的發生。
參考文獻:
[1] 陳燁.刑法中的“食品”概念辨析[J].時代法學,2013(01).
[2] 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J].中國社會科學,2007(03).
[3] 李森,陳燁.中國食品安全犯罪的罰金刑修訂與評析——基于與國外刑法典中相關規制的比較[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02).
[4] 劉仁文.中國食品安全的刑法規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04).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