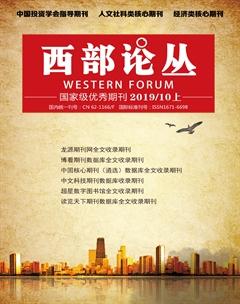弘揚焦裕祿精神紅色主題繪畫創作研究

一、概念的解析
紅色主題繪畫是以弘揚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人們大眾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堅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為題材的繪畫。對于我們而言,在新時期里對于歷史的銘記和反思,對于紅色文化故事的學習,既是我們不忘初心,努力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食糧,也是我們勇往直前,克服萬難,實現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強大精神動力。
二、焦裕祿精神簡析
焦裕祿是山東淄博博山縣人氏,曾任蘭考縣縣委書記一職,就職之前,蘭考是一個災民遍野,民不聊生的地方,由于當地的風沙、鹽堿、洪澇等自然災害,導致當地的農產品畝產才三四十斤,因此當地多有餓死的災民。當時很多人都不愿意到蘭考任職,但是焦裕祿得知情況后自告奮勇的到蘭考縣任職,幫助村民們改變現狀。在他的領導下,蘭考的受災情況一步步有了好轉,可是還沒等蘭考的狀況徹底改變,焦裕祿就因勞累過度而病倒了。1964年5月14日,年僅42歲的焦裕祿在蘭考病逝了。雖然焦裕祿人走了,但是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勤儉節約、艱苦創業“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奮斗精神;牢記宗旨、心系群眾的人民公仆精神;不怕風險、不懼困難的大無畏精神;廉潔奉公、廉政為民的奉獻精神永遠被人們所銘記和學習,永遠是鞭策我們勇往直前的強大精神動力。因此鄭州大學人物畫工作室便以此為題材開展了一系列的創作研究,并在多地舉辦了展覽。展覽中的作品總數達70余幅,其中,以張寬武的人物畫作品《情系災民》比較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篇文章便以此作為研究的主要內容。
三、藝術語言的表達
1、構圖
對于繪畫這種視覺藝術而言,繪畫主題內容的表達固然重要,但是好的表達方式更重要,因此構圖的好壞與否,是直接關系到繪畫主題內容的呈現的重要因素。從構圖的角度來講,《情系災民》這副作品以傳統的散點透視的方法、通過長卷式的構圖向我們展示了焦豫祿初到蘭考時,蘭考車站饑民遍野的宏偉場景。這副作品全卷長共8.5米高3.8米,人物數量多達49人,站在畫前仿佛置身于畫面所描繪的整個場景之中一般。在人物位置的安排上,作者通過人物站姿、坐姿等不同動態的組合使畫中的人被自然的劃分成了八個小組,從而形成了畫面布局的疏密、聚散的組合關系。根據畫面構圖形式美的要求,作者還對部分人物的結構做了虛化處理,這樣不僅使畫面達到了虛實結合的藝術效果,也增加了畫面的形式美。其次在構圖上,作者對畫面頂部空間和底部空間進行黑色墨塊的渲染,使畫面的中間部位異常明亮,從而使畫面中間的人物成為了觀者視覺中心的主體,因此,這樣的構圖手法不僅烘托了畫面的氣氛,而且很好的表達了畫面的主題。
2氣韻的表達
“氣韻”在中國傳統美學中被用來說明美的本源,用來描述和表現宇宙天地萬物生生不息,元氣流動的韻律與和諧,它一方面指藝術家主觀的“氣”是對藝術家心理素質與創造能力的總的概括,另一方面指客觀物象的生命性和精神性。在謝赫六法中,“氣韻”亦是作為第一法而出現,因此“氣韻”的傳達是人們品評人物畫成敗的關鍵因素。在張寬武的《情系災民》這幅作品中,氣韻生動不僅表現在每個人物的形象刻畫上,更是表現在作者對于黑白空間的處理上。關于人物形象的氣韻表達,《六朝畫論研究》的表述有:“強調氣韻,就是傳神,是傳神的更全面、更精密、更具體的說法,傳神的重點在眼睛,氣韻則包括眼睛、面容、四肢、身軀,既整個人體的精神姿態”,以此為基礎,我們來研究畫面中的人物形象,
觀察畫中人物,我們會發現畫面中的人物大多眉頭緊鎖,不知道是因風沙和寒冷還是因為饑餓,大家眼睛都睜的比較小,有的甚至閉上眼睛,好像睜眼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一般,在動態的刻畫上,有的人迷茫無助蜷縮在大衣之中、有的人背著行李痛苦的前行,還有一個老人形象刻畫的十分的生動,他拄著拐杖、餓的張著嘴巴、弓著后背艱難的前行。每個人的神態和動作都淋漓盡致的表達了當時人們的貧苦、無奈以及饑餓的狀態。在空間的處理上,作者亦是十分的講究。賈又福先生曾說:“中國畫很講究留白,并非空白,白仍是畫,白具有和黑一樣的價值”。在《情系災民》這副作品中,作者對于畫面留白所賦予的意義和價值甚至多于畫面的黑。這是因為在這幅畫中,白是有著現實意義的,白既指人與人之間“氣”的流轉,也可理解為遠山、河流、空氣,具有多重含義和抽象性,具體是什么需要觀眾借助自己的想象力去理解,因此給人留下無盡的想象空間,使畫面韻味無窮。并且,作者對于畫面中這種黑白空間的低沉氣氛的營造,亦是作者對于畫面內容所產生的壓抑情感的一種表達。
3.筆墨表達
一幅優秀的作品必然是“遠觀有氣勢,近看有硬功”的,因此,除了構圖和氣韻之外,我們要考慮筆墨的問題。好的筆墨往往更能抒發作者的情感,引起觀眾的共鳴。在《情系災民》這幅作品中更是如此。從宏觀來看,這副作品最據沖擊力的筆墨呈現當屬畫面中對于畫面上、下兩部分的墨色渲染了,因為作者的渲染,使畫面的中間部位十分明亮,很好的突出了主題,將觀眾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了畫面中央的人物形象刻畫上,另一方面,在《情系災民》這幅作品中,畫面頂部的墨色表達是具有多重含義的一種半抽象性的藝術語言,它們既像遠山,又像漂浮在空中的云彩,十分具有想象性,齊白石曾經講過“作畫妙在似與不似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因此這些墨塊表達與中國畫的寫意性精神十分相符。而畫面右上角的兩塊長短不一的墨塊和畫面最頂部的墨塊所形成的十分具有延申性的“S”形的白色空間,使畫面所表達的畫境變得十分的深遠。從微觀來看,畫面中筆墨表達的最精彩的是對人物的面部的刻畫中。在對面部刻畫時,作者一般都要經過五到六遍的調整,第一遍是淡墨勾勒及簡單皴擦,第二遍調好淺淡的顏色進行面部的初次上色,第三次趁著面部顏色將干未干繼續進行面部的進一步詳細的勾勒和皴擦,第四次對畫面的整體調整及個別結構的強化處理,第五次,最后的綜合調整。有時候一個人物的面部可能還會進行更多次數的刻畫,因此,在仔細觀察人物面部的墨色處理時,我們會發現不僅筆法多變,而且墨色的層次變化也十分豐富。從作者的繪畫做品中,我們不僅能夠體會到人物形象的生動,更能體會到作者對于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的態度。
總 結
紅色文化對我們民族而言,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永不退色的先進文化,對紅色文化的弘揚和學習也是我們民族在各個發展階段永恒的課題,因此弘揚焦裕祿精神的主體性創作,不僅是個人藝術水平的展現,更是對社會精神的傳達。而張寬武在《情系災民》創作中對于藝術形象的生動刻畫,以及對藝術的不懈追求正是其藝術水平的體現和其“艱苦奮斗”的焦裕祿精神的傳達。
作者簡介:孟亞然(1992.04.01)女,鄭州大學美術學院,人物畫創作研究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