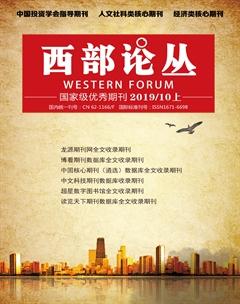驚恐障礙的病因?qū)W特征
徐展
摘 要:驚恐障礙是一種常見的急性焦慮障礙,是通常伴有生理癥狀的精神疾患。本文從病因、癥狀和診斷三個(gè)方面介紹了驚恐障礙的基本特征,并進(jìn)行了簡(jiǎn)要總結(jié)。
關(guān)鍵詞:驚恐障礙;心理治療
1 引言
驚恐障礙作為一種常見的焦慮性精神障礙,嚴(yán)重影響了患者的生理感受、認(rèn)知思維模式等各方面功能。驚恐障礙具有及其復(fù)雜的病因和表現(xiàn)方式,雖已有較為明確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卻往往因?yàn)獒t(yī)者和患者雙方的原因造成誤診
2 驚恐障礙
驚恐障礙(Panic disorder,PD)簡(jiǎn)稱驚恐癥,是近代研究最活躍的急性焦慮障礙之一。PD的終生患病率約為3%發(fā)病年齡一般在20歲左右(Kessler, Petukhova, Sampson,Zaslavsky, & Wittchen,2012)。PD患者的各項(xiàng)功能明顯低于患有糖尿病,心臟病或關(guān)節(jié)炎的患者(Sherbourne, Wells, & Judd,1996),生活質(zhì)量顯著降低(安婷, 王丹, 陳琛, & 謝祥遠(yuǎn),2015)。
2.1.2 生化因素。首先,研究證明去甲腎上腺素能、γ-氨基丁酸能等神經(jīng)遞質(zhì)在 PD 的發(fā)生發(fā)展和治療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Stork在對(duì)老鼠的實(shí)驗(yàn)中發(fā)現(xiàn),γ-氨基丁酸合成酶的缺失或減少,增加了害怕和恐慌的行為(Storketal.,2000), 說明γ-氨基丁酸對(duì) PD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還有研究者發(fā)現(xiàn),PD患者存在腦去甲腎上腺素功能的亢進(jìn)的現(xiàn)象(JDetal.,1992)。其次,研究表明跟 PD 有關(guān)的受體包括苯二氮受體和β-腎上腺素能受體等。人腦中苯二氮?受體與γ-氨基丁酸受體連接緊密,苯二氮?受體的激活可使γ-氨基丁酸的功能增強(qiáng),從而有效抑制PD的發(fā)生。去甲腎上腺素能神經(jīng)元主要位于中腦的藍(lán)斑核,其過度的活動(dòng)可能是導(dǎo)致驚恐障礙發(fā)作的原因之一,而位于藍(lán)斑核神經(jīng)元的胞體及突觸前部位的2α自體受體對(duì)藍(lán)斑核起主要調(diào)節(jié)作用(安婷, 王丹, 陳琛, & 謝祥遠(yuǎn),2015)。
神經(jīng)結(jié)構(gòu)方面,Dresler等(2011)提出了“恐懼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主要包括前額葉皮層、島葉、杏仁核,它們?cè)隗@恐發(fā)作 中扮演著不同的重要角色。另外,研究表明, 驚恐障礙患者的交感神經(jīng)平衡會(huì)受到影響,并且在一定的精神壓力下表現(xiàn)出交感神經(jīng)反應(yīng)性的增加(Kotianovaetal.,2018)。
2.1.3 社會(huì)—心理因素。研究證明,認(rèn)知功能缺陷是 PD 發(fā)病機(jī)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安獻(xiàn)麗等(2018)提出PD患者在注意、解釋、記憶三方面的認(rèn)知偏向,即優(yōu)先加工威脅性刺激激發(fā)焦慮體驗(yàn)、將模糊刺激解釋為威脅性刺激增加焦慮水平、優(yōu)先提取先前經(jīng)歷過的威脅性信息,這 3 種認(rèn)知偏向是驚恐障礙形成和保持的關(guān)鍵因素。災(zāi)難化認(rèn)知理論提醒我們PD患者對(duì)身體感覺和外界信息的災(zāi)難化解釋容易使 PD 發(fā)作,外部刺激和內(nèi)部的感覺、想法、想象等,都可誘發(fā)PD。
研究顯示,環(huán)境因素也可導(dǎo)致PD發(fā)作。精神分析動(dòng)力學(xué)理論認(rèn)為早年創(chuàng)傷經(jīng)歷可能在日后誘發(fā)驚恐發(fā)作(肖融, 吳薇莉, & 張偉,2005)。有研究發(fā)現(xiàn),相比正常對(duì)照組,PD患者會(huì)更多地報(bào)告父母早逝、與父母分離、童年患病史、家庭暴力等各種童年創(chuàng)傷性經(jīng)歷,但未來還需更科學(xué)的設(shè)計(jì)來探索PD和早年創(chuàng)傷經(jīng)歷之間更明確的關(guān)系(Bandelow et al.,2002)。
另外,目前普遍認(rèn)為PD患者存在一定的人格基礎(chǔ)。盧樂萍等(2004)通過艾森克個(gè)性問卷和 SCL-90 量表對(duì)PD患者進(jìn)行了人格特征和心理健康狀況的評(píng)估,結(jié)果表明PD患者有明顯的神經(jīng)質(zhì)傾向,其中焦慮、抑郁、恐怖、軀 體化、強(qiáng)迫等維度的得分明顯高于對(duì)照組。
2.2 癥狀表現(xiàn)。PD是一種常見的心理疾病,發(fā)作時(shí)出現(xiàn)顯著的心悸、出汗、震顫等自主神經(jīng)癥狀,伴以強(qiáng)烈的瀕死感或失控感。PD患者往往對(duì)自己的軀體癥狀作出災(zāi)難性的解釋,并通常伴有回避行為(Svenaeus,2013)。PD具有很高的緩解率和復(fù)發(fā)率,其患者對(duì)不可預(yù)測(cè)的厭惡事件過度敏感(Grillon etal.,2008),對(duì)失去掌控和不可預(yù)知的事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恐懼和擔(dān)憂( Starcevic, Kellner, Uhlenhuth, & Pathak,1993),即預(yù)期焦慮。
2.3 診斷。目 前 采 用 國 際 疾 病 分 類 第 十 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th Revision, ICD-10)作為 PD 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 《DSM-5 鑒別診斷手冊(cè)》在第四版的基礎(chǔ)上, 將 PD與廣場(chǎng)恐懼癥(Agoraphobia)分為獨(dú)立的兩類精神疾病,并且允許共病(安婷, 王 丹, 陳琛,& 謝祥遠(yuǎn),2015)。
PD通常伴有生理癥狀的表現(xiàn),因此患者往往優(yōu)先就診于非精神科室。PD 存在不小的誤診率,有報(bào)道顯示國內(nèi)誤診率可能高達(dá) 77.5%。誤診原因主要來自醫(yī)者和患者兩方面。 前者由于接診醫(yī)生對(duì) PD 的了解不夠,以及非精神科醫(yī)生的專業(yè)慣性導(dǎo)致;后者則來自患 者對(duì)軀體癥狀的關(guān)注和對(duì)心理情況的忽視,以及不可抗拒的污名意識(shí),導(dǎo)致患者選擇綜合性醫(yī)院而非治療精神疾患的專科醫(yī)院(費(fèi)春華等人,2013)。
3 總結(jié)
近年來,PD 已經(jīng)成為臨床上常見的精神障礙,涉及到生理、心理和社會(huì)等多方面因素,現(xiàn)有大量研究探索其發(fā)病機(jī)制,但仍未完全明確。診斷方面,雖然已有較為明確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但仍然存在較高的誤診率。
參考文獻(xiàn)
[1] Bandelow, B., Sp?th, C., Tichauer, G. ?., Broocks, A., Hajak, G.,... Rüther, E. (2002). Early traumatic life events, parental attitudes, family history, and birth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43(4), 269-278. doi: 10.1053/comp.2002.33492
[2] Dresler, T., Hahn, T., Plichta, M. M., Ernst, L. H., Tupak, S. V., Ehlis, A.,... Fallgatter, A. J. (2011). Neural correlates of spontaneous panic attacks. Journal of Neural Transmission, 118(2), 263-269. doi:10.1007/s00702-010-0540-2
[3] Grillon, C., Lissek, S., Rabin, S., McDowell, D., Dvir, S.,... Pine, D. S. (2008).IncreasedAnxiety During Anticipation ofUnpredictable ButNot Predictable Aversive Stimuli as a Psychophysiologic Marker of Panic Disord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 JD,C., MR,L.,JM, G.,AJ,F(xiàn).,DJ,D., RB, C.,...DF,K. (1992). Noradrenergic function in panic disorder. Effects of intravenous clonidine pretreatment on lactateinducedpanic. Biological Psychiatry
[5] Kessler, R. C., Petukhova, M., Sampson, N. A., Zaslavsky, A. M., & Wittchen, H. (2012). Twelve-month and lifetime prevalence and lifetime morbid risk of anxiety and mood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ofMethodsin Psychiatric Research,21(3), 169-184.doi:10.1002/mpr.1359
[6] Sherbourne, C. D., Wells, K. B., & Judd, L. L. (1996). Functioning and well-being of patients with panicdisord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7] Starcevic, V., Kellner, R., Uhlenhuth, E. H., & Pathak, D.(1993).Thephenomenology ofpanicattacks in panic disorder with and without agoraphobia.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34(1), 36-41. doi: https://doi.org/10.1016/0010-440X(93)90033-Z
[8] Stork, O., Ji, F., Kaneko, K., Stork, S., Yoshinobu, Y.,Moriya, T.,... Obata, K. (2000). Postnatal development of a GABA deficit and disturbance ofneural functionsin mice lacking GAD65.Brain Research, 865(1), 45-58. doi: https://doi.org/10.1016/S0006-8993(00)02206-X
[9] Svenaeus, F. (2013). Diagnosing mental disorders and saving the normal.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10] 安婷, 王丹, 陳琛, & 謝祥遠(yuǎn). (2015). 驚恐障礙病 因及診治研究進(jìn)展. 國際精神病學(xué)雜志(05), 68-73
[11] 安獻(xiàn)麗, & 鄭希耕. (2008). 驚恐障礙的認(rèn)知偏向研究. 心理科學(xué)進(jìn)展(02),255-259
[12] 費(fèi)春華, 卞慧蓮, 張平, 李穎, 周德云, 張敏,... 杜 昊.(2013). 驚恐障礙誤診 62 例分析. 臨床誤診 誤治(12),37-39
[13] 盧樂萍, 劉雪虹, & 王力娥. (2004). 驚恐障礙患者 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個(gè)性特征. 中國臨床康復(fù) (03),410-411
[14] 肖融, 吳薇莉, & 張偉. (2005). 驚恐障礙的病因?qū)W 特征. 中國臨床康復(fù)(48),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