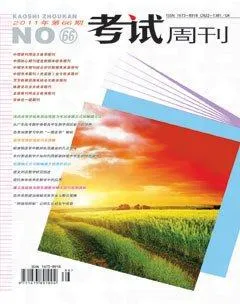對中職英語活動單導學模式的思考
摘 要: 如皋大地上正在強勢推行的活動單導學法,不但已經成為許多學校的常規教學法,而且正在普教領域開花結果。同時,這股教改的春風也刮到了職教領域:施行新的教改方法以來,固然有了很多的收獲和成果,但是在實施英語活動單導學的過程中,不斷發現所存在的一些問題,這引起了作者的思考。
關鍵詞: 中職英語 活動單導學模式 思考 總結
自活動單導學法實施以來,我們的課堂活躍了,老師上課的心情也輕松多了。老師們也都愿意嘗試新的更為有效的教學模式,對活動單導學模式大都欣然接受。所以,我們英語組也對成功地實施這樣的教學法很有信心。事實證明,我們的推廣和實施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讓中職學生真正成為課堂上學習的主人,是我從教12年來所看到的最讓我激動和認可的課堂現象,這也是前期我對中職英語教學所困惑的問題,也是我在不斷進行思考并且想方設法要解決的問題。活動單導學模式的推廣,解決了我對中職英語教學很大的困惑,并對此更加充滿信心,以爭取在新的教改形勢下,取得中職英語教學更多的更大的成績。
在一段時間的實踐中,我發現中職英語導學模式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一些一時難以解決和糾正的問題。通過這一段時間的思考,特總結如下。
一、課前花費時間過多
為了順利在課堂上實施中職英語活動單導學模式,許多老師不得不在課前印發大量的材料給學生預習,這就明顯耽擱了學生的學習時間。剛開始施行新的活動單導學模式時,一節課需要的復習時間竟達兩個課時。這固然與中職學生英語基礎較為薄弱和知識儲備很有限的有關,更與采用活動單導學模式需要較多的信息量和較高的個人能力有關。這無疑影響了學生對當天所學知識吸收和鞏固。那么,怎么解決這樣的矛盾呢?我認為,減少學習的任務量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目前正在進行的江蘇省中等職業學校新課程的創建與新教材的編寫,無疑給實施中職英語活動單導學模式提供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契機和可靠保障。
二、課堂參與率有待提高
我們的學生已經大都習慣了老師講、學生聽和記的傳統的教學模式。這并不是說老師們非要采用這種“填鴨式”教學法,而是教學的任務量和教學成果的評價體系決定了老師們必須采用這種直接的、多次重復的教學模式,才更有教學成果。在單位時間內識記一個知識點的次數越多,所掌握的效果就越好,這就是“填鴨式”教學法最大的特點。顯然,這使得學生在過去的課堂里的參與度不高,因為學生的大腦只是單純地成了被動接受知識的容器。然而,改成新的教學模式后,一部分學生卻無所適從,不知道怎樣去積極配合整個課堂學習的環境,還沉浸在過去難以開口的課堂氛圍中。最后還是那些基礎較好、能說會道的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率高。在多次聽課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部分學生存在消極應對的情況:答案反正有成績好的小組成員提供,最多我只要抄一下答案;課堂展示,反正有基礎好的同學去做;非要去展示我無法確認是否正確的答案,那就只有抄寫他人的答案了。在中等職業學校中有這樣的想法和認識的學生不在少數。那么,怎樣切實解決這樣的問題呢?這就要求教師正確配置組員。在我們班,每6人一組,其中配置了文化課程與專業課程的小組長,由他們負責幫助和輔導在某一課程上有所欠缺的組員。并且長期保持小組成員的相對穩定。這樣一方面能夠幫助組員進行較為順利的學習,另一方面又會讓基礎薄弱的學生逐步建立起學習的信心,那么要求參與課堂小組活動的積極性就肯定會被調動起來,學生整體的課堂參與率也就必然提高了。
三、課堂評價體系建設滯后
采用了新的教學模式,相應的它的評價體系也要是新的。但現實是我們的教學評價體系不但沒有任何改變,而且還大行其道。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中職英語教學領域并沒有創建新的教學評價體系。傳統的評價體系,只會讓我們回到傳統的最有利于它的教學方法上去,所以,現在出現了部分學校反復的現象:有的學校、有的班級又回到老路上去,個別的甚至要上級主管部門勒令整改,并恢復英語活動單導學的模式。這一現象說明了什么?單一的英語教學模式的改革是不全面的,需要整個教學體系甚至是教育體系的轉變,才有可能為新的教學模式的施行提供可靠的強有力的保障。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門強烈要求不把學生考試成績和升學率作為對學校和老師的考核依據就是為了給創建和推廣新的教學模式與進行新的課程改革提供一個更為廣闊、寬松的外部環境。
四、系統革新難以看到
我在實施英語活動單導學模式的過程中對教學工作體會最深的是難以完成學期教學任務和目標。要完全實施這樣的教學模式,真的很難完成正常的教學任務,這也是像我這樣的許多一線老師的深刻體會。為什么呢?用傳統的教學模式能夠較好地完成各項教學任務;用了新的教學方法后,所需的時間多了,同時,教學的任務卻沒有變少,這樣要及時完成教學任務就難以實現了。所以,施行新的教學模式,絕不是僅僅改變了教學的方法。對于教材、教法甚至教學理念與理論都要進行一次革新。最后,我認為,如果要采用新的教學模式,那么教育主管部門就要重新制定新的教學大綱。因此說,這是一個系統的工程,絕不是局部的改造。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看到在這方面的改變與革新。新的教學理念與理論的模糊不清,教學與評價體系的滯后,系統工程的缺失,這些都預示著這樣的教改可能還需要不斷地完善和提高。目前,少部分學校的反復現象,無不說明這樣的革新與創造是多么的艱難和復雜。
限于學識與眼光,我只能從以上幾個方面來思考中職英語活動單導學模式的前景,也難以對此下比較直觀的結論。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中職英語活動單導學模式無疑是優于舊有的傳統的中職英語教學模式。當然,我們在施行的過程還要不斷地總結、不斷地完善、不斷地提高,以使中職英語導學模式得以更完美地、更廣泛地普及開來。我也相信這樣先進的教學改革模式一定會在未來不短的時期內得以實現。
參考文獻:
[1]熊川武.反思性教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5.
[2]丁非編著.“活動單導學”模式下的課堂籌劃與設計.新蕾出版社,2009.11.
[3]馮衛東.今天怎樣做教科研:寫給中小學教師.教育科學出版社,2011.6.